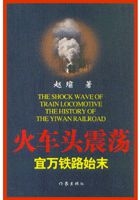那时,柏林正响应世界革命的号召。前一天,柏林工人置共产党之命令于不顾,全部出动至市中心,进行示威游行。在“红色水兵联盟”和其他激进军事集团的参与下,他们占领了当地30个警察局;水兵们包围了位于亚历山大广场的警察总署,该署由“自由兵团”的几个步兵连守护。次日,“工人委员会”的1500名代表,以压倒多数的票数,赞成总罢工的号召。首都动弹不得;无电,无交通运输。
革命者全集结于东城。他们在主要的关卡架起机枪。为了进行反扑,国防大臣诺斯克使用了新近才赐给他的专制权力,于3月5日从“自由兵团”调遣了3万名军队进城。叛乱者被挨座楼房驱走;柏林的酒吧间、舞厅和酒馆等,则仍正常开业。
柏林在进行激烈的巷战。一方用的是大炮、机枪和飞机扫射;另一方用的是步枪和手榴弹。经4天激战后,诺斯克宣布,“凡持武器反抗政府军者就地枪决。”于是,数以百计的工人依墙而立,未受审判便被处决。有1500多名革命者被打死,至少有1万人受伤。然而,叛乱精神继续在全德国蔓延。在萨克森,政权由激进派掌握;鲁尔盆地处于被包围状态。芝加哥《每日新闻》代办处的记者本·赫希特发电称:“德国正患神经病,没有精神健全的东西可报。”
慕尼黑也处在另一次革命的边缘。这次革命是在布达佩斯一次政变的鼓舞下发生的。3月22日,有消息传来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人民阵线,以工农兵委员会的名义,已夺取了匈牙利的政权,成立了以不知名人士贝拉·昆为首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贝拉·昆本人是犹太人,在32名委员中,有25名也是犹太人。因此,伦敦的《泰晤士报》便将这个政权称为“犹太黑手党”。贝拉·昆的胜利,使慕尼黑左翼分子的胆子壮起来了。4月4日傍晚,委员会的代表们踏着厚达20英寸的大雪,艰难地行走在街道上。他们的目的地是离希特勒战前住所仅两座房子开外的罗文布劳大厦——在这里,人们大声宣读决议:“消灭党派,团结全无产阶级,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与俄国和匈牙利的无产阶级结成兄弟关系。这样,世界上便没有任何力量可阻止我们全面实行社会化。”
这是个咖啡室革命,是血腥现实的幼稚的翻版。革命的领导人是诗人恩斯特·托勒。他的主张包括要求改革戏剧、绘画以及建筑的艺术形式,使人类精神得以自由。内阁由一群怪人组成。例如住房委员下令,此后各家的起居室,须一律建在厨房和卧室上方。然而,这群怪人皇冠上的珍珠还要算是弗朗斯·里普——他被挑选为外交委员,理由是,他胡子修剪齐整,又穿一件灰色大衣,是外交家的形象。里普给莫斯科发了一份措辞激愤的电报,攻击埃斯纳的继承人偷了部里的厕所钥匙;并向伍尔登堡和瑞士宣战,“因为这些猪狗未立即租给我60辆机车”。
4月13日,棕榈主日,当原总理大臣,即那位社会主义教师霍夫曼试图用武力夺取慕尼黑时,革命也就到此告终。即使拥有像希特勒等那样战功卓著的军人,他却从未有机会起事。其中一原因是,为了阻止第二团士兵赤化,他曾站在椅子上大声疾呼:“说我们应保持中立这话的人是对的!毕竟,我们不是为一伙漂泊不定的犹太人站岗的革命卫士!”虽然希特勒等人曾使慕尼黑卫戍部队保持中立。到黄昏,“霍夫曼起义”仍被粉碎,政权落入了赤色职业分子手中——由欧仁·莱维内领导,他是圣彼得兹堡人,父亲是犹太商人。他们是共产党派往慕尼黑去组织革命的。在逮捕了诗人托勒后,他们立刻将政权变为真正的苏维埃。然而,他们违反了“即使能在局部或暂时取得胜利”的情况下都要避免动武的严格的党令,以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名义,派出相当一部分力量去与霍夫曼为重新夺取慕尼黑而仓促纠集起来的8000名士兵对垒。那时,霍夫曼的部队正向离城只有10英里的达豪集结。
红军的总司令恰好是刚被共产党逮捕的诗人恩斯特·托勒。他从狱中一出来,便跃上一匹借来的马,赶赴战场,像旧时的武士一样,决心“为革命而战斗”。4月18日,这位红色的骑士指挥部队向霍夫曼发动进攻。但由于他是个人道主义者,又是个个人主义者,坚持置慕尼黑的命令于不顾。首先,他拒绝炮击达豪,企图通过谈判避免冲突。其次,当战斗打响时,他率领士卒进行战斗,几乎未流血便取得了胜利。霍夫曼的部队慌忙后撤。苏维埃领导人下令枪毙他所俘获的军官。不用说,他又把他们放掉了,而他自己也再次入狱。
达豪一役失利后,霍夫曼被迫接受国防大臣诺斯克之“自由兵团”的援助。他们以出奇的速度草就了一份征服慕尼黑的计划,并执行得卓有成效。到4月27日,慕尼黑已被完全包围。为报仇雪恨,被围困的红军把苏维埃共和国在全慕尼黑的敌人都抓了来。水兵们抓了反犹的“图里会”的7名成员,包括一名漂亮的女秘书。共约100名人质被监禁在留波尔德中学。
4月29日,慕尼黑的包围圈不断紧缩,城内的革命者惊慌失措。有人谎报说,白军已占领了主要的火车站,顿时间,红军指挥部的人员便走散一空——除托勒和红军的指挥官外。红军的指挥官决定对白军进行最后的报复。因为不久前,“自由兵团”曾在一石场里处决52名俄国战俘和枪杀10多名手无寸铁的工人。他下令将关在学校里的人质全部处决。托勒吓得魂飞魄散,慌忙前去阻止这次屠杀。但,待他赶到时,最少有20人已被杀害。
有个学生从红军残存的阵线溜了出去,将这一暴行情况向“自由兵团”的指挥官作了报告。于是,他们便下令拂晓进城。5月1日、晴朗而温暖。“自由兵团”从几个方向朝城内倾泻而来。除在霍普班诺夫和施霍宾地区遭到一些抵抗外,他们没费多大功夫便把零星的革命力量解决了。“自由兵团”的部队到处都受到被解救出来的市民们的欢呼。在马里恩广场还举行了群众集会。红旗降落了,换上的是巴伐利亚的蓝白国旗。
正当列宁在红场上向大型的“五一”节群众集会宣布共产主义的胜利时。“自由兵团”正在慕尼黑消灭抗拒分子的老巢和逮捕红色领导人。慕尼黑的大街小巷已属于“自由兵团”。很快,他们便在路德维希大街大踏步前进,在经过弗尔德赫仑大厅时,还操起正步。埃尔哈特旅的士兵,头戴*字钢盔,高唱着“头戴*字盔,黑白红袖章”……
到5月3日,慕尼黑已全被夺取,“自由兵团”所付出的代价是68条生命。当然,此仇也得报。属圣约瑟夫会的30名信仰天主教的工人在一酒店内商讨演出话剧的事情时被捕。他们被押进惠特尔巴赫宫的地下室,其中21人被当作危险的赤色分子枪杀或被刺刀挑死。数以百计的人被在类似的情况下杀死,数以千计的人被押赴“自由兵团”所属各部示众“以示警戒”。另外,还颁布一系列苛刻的告示,继续进行镇压。有些告示是根本无法执行的,例如,有告示规定,必须立即交出武器,否则枪毙。在法律和秩序的名义下,市民们被逐出家门,或受侮辱,或挨鞭打,或被杀害。“自由兵团”把慕尼黑从苏维埃共和国的铁蹄下解救出来,共和国做得虽然过分,但若与解救的方法相比,却又相形见绌了。
“要叙述白军的暴行,非有厚厚的一本书不行,”法国驻慕尼黑武官报告说,“……肆无忌惮而又有组织的野蛮行为……野蛮的屠杀,无法形容的胡闹……”英国的官员们要不是没有看见这些暴行,要不就是视而不见,批准这些暴行“从目前所掌握情况看,慕尼黑苏维埃插曲之结果,”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局报告说,“是在全德加强了法律与秩序,使斯巴达克斯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在群众中名声扫地。”共约1000多名所谓的“赤色分子”被“自由兵团”处决。在慕尼黑,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堆起如此多的尸体,使人们的健康受到了威胁。对那些无法辨认的尸体,只好抛入堑沟。
以理想为目标的万德沃格尔的青年,曾把他们的崇高理想带进战壕;现在,作为“自由兵团”的士兵的他们,又把这些理想带上了德国街头。“这是一代新人,是突击队战士,是中欧的精华,”他们的桂冠诗人恩斯特·荣格写道,“这是一崭新的种族,坚强、有智慧,又满怀目标。”他们将是为拯救德国而战斗的军人。“我们必须用鲜血铸造新的形式,用铁拳夺取政权。”
荣格这一席话,可说是代表希特勒讲的。慕尼黑之赤色政权使积在希特勒心头的憎恨苏醒了。在慕尼黑获得解放后不久,便发生了一件将改变希特勒的生活、扭转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1919年6月28日,获胜的盟国签署了凡尔赛条约,德国政府没怎么拖延便批准了条约的条款。条件很苛刻。德国被迫独自承担引起战争的责任,并赔偿战争造成的所有损失。大片大片的帝国领土被夺走:阿尔萨斯一洛林地区落入法国之手,马尔梅蒂地区割给了比利时,波森之大部以及西普鲁士割给了波兰。德国还丢失了她的殖民地。丹吉克成为一个自由邦;萨尔、施莱维希和东普鲁士将拥有公民投票权。更有甚者,盟国将占领莱茵河最少达15年之久,莱茵河右岸30英里宽地带将被划为非军事区。条约还规定,德国不得拥有潜艇或军用飞机,军队数目仅限10万。这样,德国蒙受之耻辱便达到了顶点。
这支新的力量,即德国国防军,几乎立即开始行使比其本身力量大得多的权力。为使部队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影响,他们成立了一个局,专门在部队中调查以颠覆为目的的政治活动,还向工人组织渗透。在负责这个单位的卡尔·梅尔上尉所挑选的人员中就有希特勒其人。希特勒原是最适合干这一行当的,但梅尔之所以挑选他,是因为他在战时有过“模范”记录,也可能是出于怜悯。“我第一次碰见他时,他像是一条寻找主人的、疲倦的丧家犬。”梅尔所得之印象是,希特勒“随时将命运投入他人之手,只要此人对他表示友善”。他“对德国人民和他们的命运漠不关心”。
实际上,由于革命这个传染病,希特勒正处在酝酿和混乱的状态中,他从未像现在那样对他所投奔的国家之命运表示关切。不久前,他曾得到一本宣传种族主义的小册子——或许是埃卡特编写的。这立刻使他想起他在维也纳读过的类似小册子。“这样,我不自觉地发现,我自己的发展又重新展现在眼前。”他在慕尼黑街头之所见所闻,使压抑在他心头的对犹太人的仇恨活跃起来了。犹太人处处都在掌权:先是埃斯纳,继而是像托勒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者,末了是像莱维纳那样的俄国赤色分子。在柏林是罗莎·卢森堡;在布达佩斯是贝拉·昆;在莫斯科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希特勒原先怀疑是阴谋的,现正被变为现实。
在就职前,希特勒及其他政治奸细被送往慕尼黑大学受专门训练。政治教导员中有像卡尔·亚历山大、冯·米勒教授那样满肚子是激进右派学问的保守派。“对我,”希特勒写道,“这件事的价值就在于,我现在有机会见到思想与我相似的同志,可与他们详尽地讨论目前的形势。我们都多少坚信,犯下了11月罪恶的各党派,各中心也好,社会民主党也好,均无法将德国从未来的崩溃中拯救出来。而那些所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组织’尽管愿望良好,但也无法对已发生的事件进行弥补。”
在战争期间,希特勒曾对维斯登基尔希纳说过,在和平时期,他将成为画家或步入政界;他的同志问他喜欢加入哪个政党时,他回答说:“哪个都不。”受训者中其他圈里人的结论也是,只有一种崭新的运动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决定将这个组织称为“社会革命党”,“因为这个新组织的社会观点确实要进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