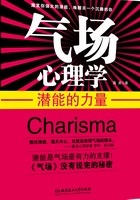可是俩孩子才迈过门槛,大的回身就关闭糟烂的破门,锁上了。
屋里顿时黑了下来,要没有墙壁透过的点点亮光,走路就会撞到墙上。
雨春心里一惊:自己已经失去了自由?
俩小子对她看不出恶意,为何锁起她来?
难道他们另有企图?
叫她妹妹,肯定是一家人。
适才听他们议论,不让人打搅她,还说没人护着,娘会打死她。
难道,这具身体办了大逆不道的事,还是干了辱没门楣的错事,让亲娘忍无可忍,要打死亲生女儿?
自己看过许多古代女卑的小说,女子因为做了失足让家人丢脸的事,家人会置她于死地。
她伸伸手,竞能动了,喝过粥,有了点儿力气了吧?原来这主是饿得不会动。
刚才漱口照水瓢,只看到不像老太太,究竟多大年龄没有看清,因为脸上脏兮兮的,看不到真容,只看到小姑娘的丫髻头。
屋里别说没镜子,这黑暗的屋里照镜子哪能看到脸,墙缝的亮光已隐没,天黑下来了。
无奈手伸向头顶,以拃做尺,量起了自己的身高。
这一量,她“扑咚”的心顿时稳住,这个身体还小,哪里会勾引男人做什么龌龊事,顶多是个七八岁的孩子,又小又瘦,就这体质,就是再高上半头,也达不到勾引男人的雌激素水平。
这个判断否决了。
亲娘为什么要打死女儿?
她想了几种可能,突然全身的鸡皮疙瘩爆起,冰凉的小身板儿战栗起来,就像得了重感冒,浑身冷的堕入冰窟一般:此女是遭色魔强*暴?她娘嫌丢人?就处死了她?
明摆着此女已经死了,自己才撞上这倒霉大运,肯定是被她娘打死的。
自己借了这个身板儿,会不会旧戏重演,再次被弄死。
附了这体就够倒霉的,再被打死岂不更冤枉。
女儿受害,不替女儿做主讨回公道,反杀女遮羞,这个社会女人一定不值钱。
是惹不起罪犯?用女儿的血涂脂抹粉?还是有别的缘故呢?
雨春想不明白,浑身困乏,头晕目眩,没精神继续下去,晕晕沉沉便失去了知觉。
轻轻的“哗铃”一响,门外的亮光随着进人照亮了门内那一块儿,是昨天那个大小子,一手端个碗,一手端着盆,走近床边把盆放在地上,碗放在床沿儿。
“哥给你擦擦脸。”捞起盆里的一块破布,拧了一下,轻柔地动作,温和的话语,真诚的眼神,让雨春冰冷的身子瞬间如吹过了一股春风。
这样纯洁的男孩,要说他有坏心算计她,她现在是不信的。
雨春只想用眼不用口,在自己达到能逃跑的体力之前,不想惊动任何有害物质。
男孩为她擦脸之际,摸了她几次脑门儿,大概是试她的体温。
雨春一点儿声色不动。
“三春,头还那么疼不?”男孩端起碗,喂了雨春一勺粥,口里温和地问着。
雨春虽然很感动,可还是没有说话,也没有摇头点头。
她心里合计好了,装傻试试,毕竟打她的女人是这个身体的亲妈,看到女儿被她打死再复活了,能不能良心发现,可伶可怜这个傻女儿,给她一条生路。
男孩面现愁苦之色,眼神比进门时暗淡了许多,强忍愁苦,心中默叹:妹妹许是被娘亲打傻了,一棒槌削到后脑,花花脑子没流出就是万幸,能有不傻的?
妹妹的一生让娘给毁了,她这一生怎么办?
娘可真狠,这么一点儿的孩子就要卖给个老头儿做小,好像三春不是她的亲生。
没有一点儿疼惜,没有一点儿留恋,她的行为说明,女孩生来就是留着卖的。
林雨春肯定了她借的这个身体名叫三春,她也只有默认了。
这男孩就是三春的三哥陶永明,那个小的是她四哥陶永辉。
此时陶永辉急匆匆跨进门槛,急切叫了声:“妹妹!”慌忙从怀里掏出半拉白花花的馒头,馒头中间夹了块肥肉,急急地递给三春:“春儿!快吃,干喝稀粥没有盐味,多饿得慌,楚大哥说,没有补品,受伤的人不易好起来。”
永辉眨动大大的星眸,满眼的真诚与疼惜。
见三春没接,掰了块馒头,揪了小块儿肉片,捏着送到三春嘴里。
三春早就饿得慌慌,馒头要是在她手里,一定两口就会吞下肚。
她猜想这个孩子准是把自己该吃的偷偷留下,给她拿来,她怎么好意思去接。
再次感动……
眸子水雾迷蒙,强忍下流泪的冲动,下力的闭起双睛,哽咽的咽下嘴里的食物。
永明看三春不知道接永辉手里的馒头,眸光更加暗淡,叹息声脱口而出。
直到永辉喂完了三春馒头,朝阳升起了老高。
“我们扶三春到院子透透风,屋里阴暗潮湿,再生了病就更遭罪了。”永明一提,永辉立即赞成,双双扶出三春。
从黑屋出来,院里的明媚阳光晃得三春睁不开眼,在二人的扶持下,走了好多步,才适应过来。
屋里屋外两个天下,院子是天堂,小黑屋就是地狱,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儿,她终于活过来了。
溜了一会儿,腿就能站稳了。
哥俩交换了一下眼色,好像心有灵犀,永辉鬼机灵,看三春不言不语,明白哥哥的暗示,晶亮的眼眸黯了又黯。
心里明白,嘴上怎能说出来。
当着妹妹的面儿,万一她听得明白,使她的精神受挫,或是受到打击,做了傻事,后悔药是没处买的。
三人正在各有所思,一声脆厉的怒吼惊得三人呆愣当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