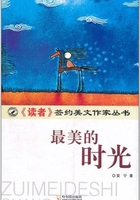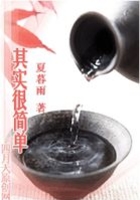倚势欺民太不良,偶遇玉川问短长。
群奴仗主逞凶恶,打伤劣少逃过江。
四句闲言叙过。话讲大明天子万历皇爷登极以来,各国进贡,四方安靖。一日,皇爷朝驾登九五,只见黄门官跪拜,口尊:“万岁,臣启吾主,昨日乃系元宵佳节。灯烛无光,京都地震山摇。”皇爷闻奏,遂宣钦天监上殿相问。监正官姜瑞鸿奏曰:“月烛无光,地震山摇,当主两处反乱。”皇爷闻奏曰:“以待后验。”遂即朝散。
且言山西太原府有一位田云山,文才甚佳,胸藏锦秀,身中黄榜进士,官居江夏县知县。夫人曾氏所生一子名田车,字玉川,相貌文秀,自幼聪慧,习就文武兼全。自十七岁身入黉门,随父到任,仍读诗书。时逢夏令,天气炎热,公子心中闷倦,闲暇无事,心欲往龟山避暑玩景,怀揣蝴蝶杯走出县衙,望龟山而来。一路行来,不一时来至龟山。只见青山叠翠,绿柳成阴,百鸟喧鸣,翠柏苍松,密密森森。江中鱼船来往撒网,红男绿女皆奔龟山前来乘凉。真是幽雅避暑之处。
且言江中有一鱼船,渔翁姓胡名宴,不幸其妻早已亡故,膝下只有一女,名唤凤莲,年方一十六岁,生得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聪明伶俐过人,每日随父在船中打鱼度日。此日天气清朗,江中无风。父女二人把鱼网撒在江中。不一刻,胡翁见网内沉重,必有大鱼,忙唤女儿把船拢岸。凤莲忙把船拢岸,抬头一看,见网内打着一鱼,是人头鱼身,心中一惊,忙呼:“爹爹快撕手,放他去罢!”胡翁问:“好容易打上此鱼,为甚么把他放了?”胡凤莲口呼:“爹爹,此是怪鱼,乃是不祥之兆,恐与咱父女有不吉之处,放了为妙。女儿夜间偶得一梦,未敢向父亲言说。所梦者就是此怪鱼蹦上船来,把父亲推在江中。
不祥之兆莫非应在此鱼身上?还是放了好。”胡翁闻言笑说:“你是不认得此鱼,此鱼名是娃娃鱼,就是众鱼船上人最难打着此鱼。若讲梦兆,我又不是读书之家,那来的这些之乎者也?我等打鱼之家,盼望打着大鱼才有度用。好容易打着大鱼就要放了,动不动的就讲梦。我是一福压百祸,你休讲那春梦!”凤莲姐说:“此系异怪鱼,恐无人敢买。”胡翁说:“若遇富豪之家见此鱼,买了去放在池中,闷时赏玩。我无非多卖几串钱。”遂把鱼放在筐中,携着鱼筐登岸。凤莲姐口呼:“爹爹早些回来,免女儿挂心。”胡翁说:“不早回来,难道就死在外边?真乃少调失教!”言罢徉徜而去。凤莲见父已去,不由眼中落泪,心中暗想:“父亲不听谏言,反被其辱,令人羞愧煞也!”
不言胡翁父女之事。且言万历皇爷临早朝,驾升九五,龙门闪放阖朝文武大臣朝参已毕,文东武西,各归班中。只见太师张居正出班,俯伏金阙,口呼:“万岁,臣有本奏上。”皇爷问:“有本奏来。”张居正奏曰:“现有朵思叛贼董狐狸,侵犯吾主北界雁门关一带地方。”皇爷问:“此贼搅扰朕当边界,以何人前去征讨?”太师奏曰:“戚广基久守蓟州,广得人心。若带兵前去平贼,必大获全胜。”皇爷曰:“依卿所奏,朕即传旨。”一言未了,只见右都御史冯保、左都御史海瑞二人跪伏金阙,口呼:“万岁,现有南溪洞苗蛮造反,侵占数处地方,官兵屡战不胜。
”遂把告急文书呈上。皇爷览表沉吟暗想:“正应地震山摇之兆。”遂问:“海爱卿久守南界,必晓苗蛮之虚实。当饬何人去征伐?”海瑞奏曰:“苗蛮不种田苗,广积金银财宝;山路崎岖险峻,官兵实难除之。若前去征伐,除非令湖北武昌府两湖总督卢林,幼年习就文武全才,兵书战策,可任平蛮之命。”皇爷准奏,降下旨意,宣召两湖总督卢林挂印为帅,右营司马唐让为前部先锋,武昌府管理押运粮草,旨到即刻起程。又降旨:“戚爱卿:封卿为雁门关总帅。现有朵思王、董狐狸扰害百姓,侵占疆土,令卿速赴教军场挑选兵马,前去征伐。破虏之后,加级封赏。”戚广基谢恩,众臣皆退朝散去。
慢表戚帅挑选兵马前去征伐北虏。且言武昌府总督卢林,文武双全,英勇无比。现年五十余岁,膝下一子一女:一子名士宽,年一十八岁,女名凤英,年方一十六岁,美貌无比,贤惠无双。士宽生来不习诗文,专好浪荡胡行,生性骄傲,或游逛妓院,就是驾鹰弄犬。这日闲暇无事,呼唤“小子们快来。”只见有二十名家将,闻唤忙忙来至近前,单腿打千,口呼:“大爷,唤我小子们那边使用?”士宽说:“带着赛虎犬,你们随大爷我到龟山游玩避暑。”众家将问:“大爷可是坐轿,可是乘马?吩咐下去好预备。”卢士宽闻言说:“不用轿马,多带酒肴,步行龟山乘凉。”众多家将遵命,各各洋洋得意,抬着酒肴食盒,有架着鹰的,牵着犬的,一齐出离府门,竟奔龟山而来。
且言老渔翁胡宴,手提鱼筐走在龟山,吆喝买大鱼。只见一伙人近前问:“你这老汉卖的是什么鱼?拿来我家大爷要看看。”胡翁遂把鱼递与家将,便道:“拿过去请看,比不得寻常之鱼。”家将说:“你往后些站。”胡翁笑说:“只要大爷爱惜此鱼,何论价值高低?”家将闻言骂道:“你这瞎眼的老狗,大爷爱要竟敢要钱!你就当奉送与大爷才对!”胡翁说:“若把鱼送与你家大爷,我一家就该喝风不成?”家丁喝道:“你这老东西,我家大爷不难为你,赏你二百文铜钱,到帅府去领。”胡翁说:“我打鱼为业,无闲工夫,不能赊帐。价钱不敷我是不卖。”家丁说:“你当真不赊帐吗?”胡翁说:“实在不能赊帐。”家丁骂道:“你这老狗,不识好歹、不知进退的东西!”卢士宽说:“令他拿了去!”遂把鱼往地上一摔,被大犬一口咬死。胡翁一见,连忙跑近前抢鱼,被大犬将手咬坏,鲜血淋漓,疼痛不止。胡翁哭喊说:“你就是大爷就不讲理吗?快赔我的鱼罢!”卢士宽闻言大怒,喝道:“好一老狗,你在这武昌府访问访问,谁敢逆言冲撞。你竟敢冲撞你家少爷!”遂吩咐家丁:“拉他下去,打他四十皮鞭!”众家丁遵命,闯上来按倒胡翁,用皮鞭乱抽。只抽的胡翁叫喊连天,竟打的皮破肉绽,血水崩流。
且言田玉川正在龟山闲游,看的明白,心中暗想:“世上竟有这不讲理之事!”遂上前分开众多恶奴说:“列位停手,不必打了!”众家丁见是一少年前来讲情,说:“打他不打他与你何干?难道你替他挨打吗?”田玉川无暇答言,忙走至卢士宽面前,口呼:“少爷请了。”卢士宽问:“你是甚么人,敢来答话。”田玉川说:“这老者若大年纪,不赔他的鱼到也罢了,况且又打他一身伤。倘若将他性命损伤,反为不美,岂不是倚势欺人吗?”士宽怒问:“你是那里来的?敢来多言多事。就是打死他,有你少爷作主!”田玉川说:“我乃江夏县知县之公子田玉川是也。”卢士宽闻言说:“好一小小知县之犬子,竟敢前来放肆!尔如飞蛾投火,你莫非替他挨打,自寻其死?尔如粪堆之草,怎比俺丹桂。
”田玉川说:“你休要出口伤人!凡事理同天下,岂以势力压人?王子犯法与民同罪!”士宽问:“你家少爷有何罪?”田玉川说:“你仗势抢夺民鱼,纵犬伤人,反喝令恶奴毒打老翁,岂不是罪?”士宽怒说:“我父乃是两湖总督,难道不如你父七品知县?我纵犬伤人也是有的。喝令打此老狗,只当取笑。把他打死,你不过看着我!”田玉川怒道:“恐老天不容你这劣货!”众恶奴见此光景,不由怒气冲冲,齐声说:“打!打!打!”各各卷袖攒掌,怒目瞪眼,咬牙切齿。田玉川见他主仆等不讲理,横行霸道,不由一阵心头火起,大骂:“你这群狗娘养的贼子!倚仗势力欺虐百姓,人人得而诛之!我田某有何惧哉!”卢士宽一闻田玉川之言,不由怒气攻心,遂把恶犬撒出。
恶犬照着田玉川扑来,田玉川见犬临近,不慌不忙,使了个泰山压顶式,一拳打去,正中犬的顶门,只打的恶犬栽了两栽、晃了两晃,“噗嗵”一声,四足朝天,死于非命。众家丁一见把犬打死,齐说:“不好了!把犬打死了!”卢士宽闻言大怒,喝道:“还不一齐下手,等待何时?”众恶奴闻言一齐闯上来,抡拳就打。田玉川微微冷笑,近前迎抵。不一刻工夫,打倒七八个恶奴。卢士宽见众家人不是田玉川抵手,自己乃是将门之子,略通武艺,不由气往上撞,遂即赶奔近前,向田玉川动手撕斗。未及三合,被田玉川一拳打倒在地,复又以脚踏在项上,又打了数拳。众家丁一见,心中大吓,近前抢护,招招架架,一溜歪斜,一阵乱跑逃去。田玉川见豪奴等逃跑,并不追赶,回头见渔翁口内“哼咳”不止,卧地不起,近前问渔翁曰:“你这老汉还不回去吗?”胡翁曰:“小老儿被他们打的站不起来了。”玉川闻言,忙把胡翁扶起。胡翁含泪曰:“多蒙相公救我不死。活命之恩,日后小老儿必然报答。”言罢蹒跚回船去了。
且言众恶奴搀扶卢士宽走至江边,一声吩咐:“船户们听真,今有县衙知县之子将总督公子打伤,千万不可渡他过江!那个渡他过江,查访出来拿到帅府,按违命问罪!”吩咐已毕,过江回衙去了。
再言田玉川走至江边,一声呼唤:“船家渡我过江。”那些船户说道:“今有总督公子吩咐我等,不准渡公子过江,若渡公子过江,治我等之罪。公子再设法去罢。”玉川再问,各船户皆不答言。自思:“船家不渡我过江,必是这恶豪们回到他帅府领军兵前来拿我。不如且到龟山上再作道理。”
且言胡凤莲独自一人在鱼船上,心神不安,坐卧不宁。自清晨直到午后,不见父亲回船,心中纳闷,站在船上向远处眺望。猛见父亲踉踉跄跄踱了来。即临且近,见父亲眼含痛泪,“哼咳”不止,声声呼唤:“女儿呀女儿,快快搀扶为父上船。”凤莲见父浑身是血,满面青肿,不由的心中大惊。
不知后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