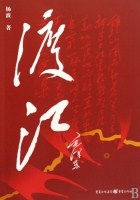黄天骥
广州久未下雨,连日郁热。从昨天起,雨丝风片,渐渐飘进了校园,榕叶轻摇,凉意渐生。我平生怕热,正在浑身感到不自在的时候,打开电脑,看到郭启宏学兄寄来的《燕云居诗稿》和《燕云居长短句》。读着读着,心潮洞。这时暮云四合,电闪雷鸣,忽又大雨倾盆,竟似江河倒泻。而我,则越读越感到淋漓痛快,两腋风生。
记得二十年前,启宏曾寄给我一批唐宋诗集句。当时,我便知道他熟读大量诗词,但并未知道他也经常写诗填词。这次,细读了他的作品,才晓得他深谙其中三昧。有些诗篇,即使放在当今的诗坛中,也可以称得上是上乘之作。
近几十年,人们对古体诗词的创作,越来越感兴趣,许多骚人墨客,“勒马回缰作旧诗”(闻一多语)。尽管报章上很少刊载这类作品,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写作诗词的兴致。因为,从语言的音乐性而言,从注意平仄音韵的运用,使诗作更符合汉藏语系的特点而言,格律体的诗、词、曲,比新诗有更大的优点。不错,有人认为诗词格律会约束作者的自由发挥,说写格律诗像是“戴着镣铐跳舞”。其实,这些说法,只是出于对格律和对创作形式的误解。我认为,无论采取任何体裁进行创作,其形式,必然会对作者有所帮助,也有所约束。而一旦作者熟练掌握了形式,例如说,掌握了古体诗词格律的规矩,那么,所谓“镣铐”,反可以为作者所运用,让它有助于传达感情,表现内容,更好地展示“舞蹈”的曼妙。像启宏的诗词,格律是严谨的,但这没有影响他奔腾跳踯的思绪,倒能更微妙地表现出他在特定情境中的特定意绪。所谓“镣铐”,在他手中,成了具有表现力的“道具”,成了诗词作品的花环。
近现代格律诗词的创作,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走向。一是以聂绀弩为代表,即在熟练地掌握格律的基础上,又颠覆并突破了传统诗词审美观念,以嬉笑冷诮的笔触,揭露嘲讽不合理的生活现实。无疑,以黑色幽默构建格律体诗词,乃是中国诗词史上的新创造。另一种,则以郁达夫为代表,即在继承传统审美意象的基础上,融入自己具有时代色彩的思想感情,像他那“曾因酒醉输名马,只怕情多误美人”的名句,便在传统审美机趣中透露出新的意趣,这也属于新的创造。当然,这两种写作趋向,和作者不同的性格以及不同遭遇有关。而无论是突破还是继承,凡属成功的诗作,都离不开感情的“真”和意象的“新”。换言之,现代格律诗词的写作,如果能使“真”和“新”浑成一体,那么,便可以在诗坛上留下宝贵的一页,做出触目的贡献。
启宏的诗风,接近于郁达夫一路,却又有自己的个性。我认为,婉约中见奇崛,典雅中有含蓄;清丽其表,风骨其里,是他诗词创作最为明显的特色。试看他的《咏萤》、《供草》、《茶余偶成》诸诗,淡淡写来而中含机锋,才华横溢而隐露激越。这些诗作,笔法的纯熟和旨趣的奇兀,在现代诗坛中并不多见。从他常写到对生活的爱和恨,写到创作生涯的甘和苦,我认为,这一独特诗风的形成,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启宏的诗词创作,已经达到颇高的境界,所以,实不必对他的作品逐一分析,只宜让读者从总体上把握其机趣。可以说,《燕云居诗》和《燕云居长短句》,无论是古体、绝、律、词、曲,俱臻妙境。其中像《顾梁汾歌》、《改编下场诗》、《有感》、《金缕曲二首》、散套的《归去来书怀》,尤属各种体裁中的精品。这些诗作,在风流蕴藉中贯注着磊落不平之气,真情丽句,感人至深。
在这里,我又想起了启宏多年前给我看过的“集句”。说实在话,“集句”虽属游戏文字,但若非对古人诗作读得精熟,融会贯通,也无法“集”得起来。显然,启宏胸有诗书,烂熟于心,便能顺手拈来,集腋成裘,别饶佳趣。在《燕云居诗》里,他用典恰当,疏密有度,有雅驯之妙,无“掉书”之嫌。而在古体诗《古意》一篇中,他甚至敢于把汉乐府、古诗十九首、陶诗、唐诗、宋词、元曲中许多句子,撮其佳韵,熔于一炉,含英咀华,以“古意”表达自己对现实的新感受。这一切,说明了他根基深厚,所以既能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又能继承我国诗词的传统,蕴涵深远的意境。
启宏是我国着名的剧作家,他写了多部被人传诵的剧本,像《南唐遗事》、《李白》、《沈园梦》、《知己》等等。这些剧作,取材于历史人物,但和别的历史剧不同的是,他的剧本,全都流注着诗意。它们是戏,却又是诗。“戏中有诗”,这一点,正是启宏剧作鲜明的特色。在演出中,观众分明可以感受到在戏剧矛盾冲突中包孕着诗心,分明可以感受到剧作家的诗人气质。而现在,我细读了《燕云居诗》,发现有些诗章,在抒情中突现作者内心的矛盾冲突,这又近于戏剧性的写法了。像《茶余偶成》:“少小乖张老大狂,人间百味半亲尝;追思谈笑成佳趣,一入毫端便断肠。”其间诗人的心路历程,进展何等曲折;喜怒哀乐,对比何等强烈!当然,这里没有戏剧的场景,但作者内心戏剧性的变化,又使我感受到启宏的许多诗作,具有“诗中有戏”的韵味。
我和启宏都毕业于中山大学中文系,同受业于王季思教授门下。我比他痴长几岁。当时,我作为青年“教师”,曾和同学们一起到虎门公社,参加劳动锻炼,一起摸爬滚打;也曾在讲台上,向同学们胡诌些自己对古代戏曲的学习心得。启宏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劳燕分飞,我们联系的机会就不多了。由于我长期在季思师身边工作学习,知道他老人家一直惦念和器重从事戏剧作的郭启宏同学,以及从事戏剧文物研究的黄竹三同学。他常向研究生们提起,要好好向这两位在戏剧领域上作出贡献的校友学习,学习他们落地生根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后来,季思师仙逝,启宏回校奔丧,在追悼会上,他和我相拥而泣,我为他对老师那份感恩之心和真挚之情,深深感动。前几年,竹三同学七十大寿,我们得以在临汾欢聚一堂。执手相看,彼此均已两鬓添霜了。回首前尘,感触良多,我们也都记起了季思师的教导,彼此相互勖勉。那几天,我们一起游览,一路啸吟,师兄弟之间,享受着校友情谊的温馨。
以前,我虽知道启宏能诗,但只有读了《燕云居诗》及其长短句,才真正了解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造诣,也理解了他能在戏剧创作方面,取得如此卓越成就的原因。母校师友,每为启宏的成就感到自豪。最近听竹三说,启宏创作了《知己》一剧,剧坛反响强烈,但他似也累倒了。我一面为他高兴,一面也有点担心。我深知,戏剧创作,需要对角色全程投入,极易兴奋乃至亢奋。以他的诗人气质,感情精神的损耗,脑力劳动的艰辛,实在可想而知。
读罢《燕云居诗》及长短句,夜已深,我不禁走到阳台上,遥望北方,意往神驰,启宏的身影和我们几次短促相聚的情景,宛然在目。临毫之际,深深祝愿他佳作迭出,更希望他注意健康,为中国剧坛珍重,为母校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