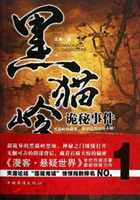秋天尚没过完,一股强烈的西北风裹挟着寒流吹进吕梁山区。树叶子打着旋儿在风中飘飞、碰撞,落的满世界都是。走在县城窄窄的石头街道上的人们,一个个屈颈缩脑像进入冬天一般。国民党离石县党部特务塌鼻子猫着腰揣着手踏着树叶子走着,一双鼠眼却不安分地瞟来瞟去,像绺贼寻觅偷窃的目标。他猛然发现迎面走来一个戴呢子礼帽的男人是兀的面熟,就是一下子想不起是谁。第六神经告诉他这个人不能放过!等那男人与他错过身,他便回头跟上了他。塌鼻子调动全部记忆细胞走着想着终于想起来了,这圪且人在前年夏天曾带领一拨儿洋学生从太原来到离石,到处散传单作演讲,组织工会农会学生联合会。据知情者说他们是共党派来搞赤化宣传的。由此看来,这人肯定是共党分子,决不能让他跑掉!党部卫书记长讲了,凡是在“清党”中逮住共党分子的一律重重奖赏!看来我又能发一笔小财了!塌鼻子这么想着,偷偷笑了。
他盯梢很有经验,决不会让被盯的人有所察觉。他跟着他从正街进入小巷,走一截儿又拐了个弯,上一道缓坡,见那人进了一所高门大院。他就停在院门外僻静的角落观察等待。从前晌等到后晌,从后晌等到日落西山,仍不见这圪且共党出来。肚子饿得咕咕叫不说,倒霉的天气冻得他就吃架不住。他只穿一件夹袄,原地小跑着还不断地流清鼻打哆嗦。再这样呆下去,非冻病不行!可我一走,岂不白等了一日。就这样越等越冻,越觉得走了吃亏。他吸溜吸溜地自言自语,“日他爹,这鬼营生真不是人做的!”正在这时,就望见戴礼帽的男人陪同一位打扮入时的漂亮小姐从大门里走出。他感到欣喜,就跟着两人往街上走。穿过小巷,来到大街,两人走进一家已亮了灯的饭馆。塌鼻子又停留在饭馆门外挨冻。他正为动不得脱不开犯愁,就遇上一位同僚。他跟他嘀咕几句,同僚便撒腿离去。不大功夫,一队全副武装的黑衣警察跑来包围了饭馆。
高上人表现得总是心神不定、坐立不安,在家中甚事也做不到心上,就三天两头往外跑。不是去中阳、柳林,就是去临县、三交,但去的最多的地方还是离石。因为李春燕来吕梁山最有可能先到离石,那里有她一个要好的同学。庄聪慧不想让他往外走,就变着法儿让他高兴。给他念诗;与他下围棋;玩踢毽子、猜谜语、放风筝;一起到黄河边散步,看艄公们流船过大同碛;一起逛碛口繁华的街道,热闹的商号;逛卧虎山明代古刹黑龙庙;到自家的骆驼场看骆驼;最有意思的还是遛自行车。前不久,庄帮主的商界朋友送来一辆从天津购买的日本造晟冒牌自行车。尽管这种前后两个轮子同时转动人坐在上边却倒不了的铁玩意儿已引进中国多年,但河畔人却从未见过。当高上人骑车带着庄聪慧在黄河滩转圈圈,在马路上跑来回时,惹得男女老少一群一伙围着瞧稀罕。上人在聪慧的陪伴下,有时玩起来倒也痛快,可是当独自躺在炕上,他的心便飞到李春燕的身旁。有时在吃饭的饭桌上,或是同聪慧散步的中间,他的思绪一下就不知飞到哪儿去了。这时他就在家呆不住了。聪慧说:“别往外跑了,眼下国民党到处抓你们的人,听说前几日临县一下就捕了好几个。你一出去我就为你提心吊胆。”上人说:“干这一行就要把得脑拴在腰带上。我们不能因为阎锡山搞清党就甚事也不做了!相反,我们要针锋相对地作斗争!革命工作一天也不能停。即便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下,我们也要联络同志,发动民众,揭露国民党的反革命阴谋!”聪慧的心里很矛盾,即觉得上人的革命精神可敬可爱;又认为他们是以卵击石,怕不会有好结果。她劝不住他,只能由他了。他出去两三日或四五日就回到家,过几天又走了。就这样一晃好几个月过去了。
深秋的一日后晌,庄耐贵两口子把上人、聪慧、还有十八岁的儿子庄聪力叫到客厅,郑重其事地谈了两件事。庄耐贵说:“上人,你今年有二十四五了吧?慧慧也二十出头了。这个岁数在咱们乡下不成家的为数不多,当然,除非穷得娶不起老婆。所以说,你们俩再不完婚就是老人的不对了。我和你妈商量了一下,想在近日把你们的婚事办了,看你俩有甚说的。如果没甚说的,就要请先生订日子了。”聪慧撇了一眼上人,上人没有马上表态。这件事对他来说即突然也不突然,说突然是因为他完全没有精神准备,没想到自己的事情竟然由不了自己!明明是聪慧在后面做了工作,他还不得不哑巴吃黄连。说不突然是因为他和聪慧关系是多年以前就定下来的。要说不情愿有什么摆在桌面上的理由呢?更何况面对的是大恩人,他怎好意思回绝呢?心里打斗了一阵只好说:“请庄伯伯安排吧,我没甚说的。看聪慧有甚意见。”聪慧一听,喜形于色,“我没意见。”父亲说:“好,一切准备由家里安排,不用你们操心。上人,等定下日子,我派人将你全家接过来。”上人心里圪噔了一下,但没有做声。父亲接着说:“成了家就要立业。我看上人暂时也没甚做的,闲逛荡也不是回事。最近家里新开了一个绸缎庄,聪力在兀达照管着。我打算把它交给上人经营,就算是你们小两口的家业。聪力往后主要把驼帮和货栈照管好就行了。”这件事上人没有立马应承,他怕捆住他的身子不自由,只是说外面还有些工作,让我考虑考虑。庄耐贵说也不着急,等你们成婚以后再说吧。
没出三日,结婚的日子便选定了。饭桌上,高上人主动请缨:“庄伯伯,还是我亲自回去一趟接家里人吧,你就不用派人了。”聪慧说:“我跟你去!”上人说:“新娘子哪儿敢离开!”父亲说:“本来慧慧应当跟上去认认门,可是日子紧,你就在家作些准备吧。”继母庄白氏说:“要不要跟上一挂车,带轿顶子的,路程远,坐上舒坦点。”上人说:“用不着姨妈,我们老家山高沟深,盘肠小道,走牲灵都提心吊胆,大车更不能走。我爹妈骑毛驴还行,家里有毛驴。”父亲说:“由你吧,不要叫老人受屈就行。”第二天一大早,高上人骑了一匹枣红马冒着西北风吹来的寒流独个上路了。
但他没回什么老家,更不晓得老家在甚的山庄!心想到时候撒个谎,说老子有病或家中有事不能来参加婚礼就行了,谁还会再去跑一趟核实?他骑马直奔离石县城。翻过王老婆山,便一路策马扬蹄,纵情驰骋。赶半前晌的时候就跑到了。先寻个客店落脚,随后就往春燕的同学家走。这是一家殷实的富商,上人已来过两次,所以不用再问路。一进院子,他便听见西厢房里传出熟悉的笑声,遂喜不自禁!李春燕是夜来刚从太原来到离石的。正打算托人给他送信儿,不想他到来了。春燕表现得更为激动,要不是当着同学的面,她早扑上去与上人搂在一起了。但上人仍能从她会说话的眼神里感受到火辣辣地痴情。上人坐下来问:“太原的局势咋样?”春燕说:“国民党抓人更凶了。听说第一监狱都放不下了,又在上马街成立了个什么‘自新院’。前几天我们班正在上历史课,警察冲进教室就抓走两名同学。据我分析他们不像是真共党。国语孟老师偷偷跟我说,小李,出去躲躲吧,你恐怕也是个目标。第二天我就起身了。看来我这个非党人士也得跟着你们这些共党分子受害噜!”春燕的同学小庞打趣地说:“这哪叫受害,这叫沾光!要不你咋能在我家和你的相好会面!”上人说:“是呀,好事都是被逼出来的。其实你早就应该来的。”春燕说:“你刚走我就想来,可是我妈不让我走。这次是被逼无奈了。”
他们几个凑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天南地北、城市乡村、学校家庭、老师同学,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当前的时局。他们聊到饭时,吃过晌午饭又接着聊。直聊到日落西山,窗牖的亮光变得蒙胧,上人才说:“春燕,上街走走吧!”小庞理解他们,赶紧接过话茬,“对对,别老闷在家里,出去散散心。等一会儿回来,我给你们收拾住处。”她送他俩出了家门,又补充道:“上人,出去当心点。最近离石也不安全,听说也是扑风捉影地抓人。”上人说:“晓得。”就挽着春燕的胳臂走出大门。他根本想不到,门外有个穿黑夹袄的塌鼻子男人已经盯了他一天的梢儿。
两人在饭馆里要了几个菜一壶酒,舒心地边喝边吃边聊。这次聊的都是私房话。上人当然不敢说出被庄家所迫不得不于近期办理结婚的事。相反,他要哄得春燕高兴,表白他心里只爱着她一个,如何爱得发疯发狂!自打太原回家以后,无时无刻不在想她,想她想得昼不欲食,夜不成寐。春燕则说,她亦是如此。两人都觉得呆在县城不是长久之策,正商量下一步往何处去,就突然冲进一帮警察,上人与春燕顿时惊得目瞪口呆脸色煞白!警察把枪口对准他俩喊道:“不许动!”上人哆哆嗦嗦说:“我俩都是好人,你们这是做甚?你们认错人了吧!”警察头儿说:“少说废话,捆起来!”上人愤怒地说:“不要胡闹!我要见你们县长!”警察头儿冷笑着道:“见县长?好吧,跟我们去警察局见。带走!”警察们用枪顶着被捆绑的一对男女青年喝喝咤咤走出饭馆。
他俩被关进县警察局看守所。李春燕不断地长嘘短吁,来吕梁本来是为躲避抓捕,结果躲到敌人的魔爪之中了,她越想越觉得窝囊、气得慌!高上人搅尽脑汁也想象不出他是怎么被抓的。难道他们发现了我的身份?可是这地方谁又了解我呢?奇怪!他更为春燕的受连累而感到内疚!翌日提审时,他当着国民党县党部卫书记长的面大发雷霆,“你们咋能在光天化日之下随便抓人?太不象话了!我们都是中华民国的公民,是安分守己的学生,你们凭甚抓我俩?我们犯了哪一条罪?荷出证据来让我瞧瞧?你们这简直是无法无天嘛……”书记长眯眯笑着,不躁不恼,等高上人的火气发完,才文质彬彬说道:“年青人不必激动,谁也不会平白无故抓人。你只要如实回答我的审问,经查证确实如你所说没有问题,我们自然会放你的。当前处于清党时期,请原谅我们不得不对一切可疑分子进行审查……”如果编造个假姓名就好了。两个年青人吃亏就吃在过于老实。当他们回答完头一个问题姓甚名甚时其实就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侥幸逃出“魔掌”了。下面再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无济于事,因为卫书记长面前放着的国民党省党部下达的通缉共党人员名单中明明白白有这两个名字:高上人、李春燕。前一个名字是共党叛变分子供出的,后一个名字是有关方面检举的。一个礼拜以后,两人被押解省城,送交由省府、党部、绥署、法院、宪兵司令部、公安局共同组成的清共委员会进行审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