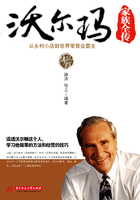这是我新写的一部传记,传主是张颔先生。
老先生还健在,已九十岁了。
他是一位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也可说是一位历史学家。作为学者,他的成就是很高的,堪称大家。又是一位功底深厚的书法家。这两项是他惯常示人的面目。还是一位诗人,作旧体诗的诗人。《侯马盟书》《古币文编》《张颔学术文集》这类着作,见出的是他的才学,而那些旧体诗词,见出的是他的性情,还有他的风骨。他有他的自尊,也有他的谦抑,但我最喜欢的,还是他的自嘲,一种更高的人生境界。
若不是有这样的人生境界,一个人怎么能经历那么多的磨难,活到耄耋之年又有这样大的成就?
我写这部书,不是谁人的托付,也不是哪个部门的任务,是我觉得张先生这样的人,值得我为他献上这么一部书,就写了这么一部书。很想仿效某些大作家的派头,说写什么人就是写他自己,比如郭沫若先生,就说写蔡文姬是写他自己。但我知道,就我来说,无论德行还是才具,哪样都配不上。我枉上了历史系,虚耗国帑,荒废时日,成不了历史学家。能为历史学家写部传记,也算是聊补此生的缺憾吧。
若说此书,写作上有什么可称道的,那就是从容,采访一年多,写作大半年,修订又是大半年。从开始采访到定稿,不觉已四个年头了。
再就是,写法上还是费了些心思,采用一种我过去从未用过的新体例——访谈体。它有它的好处,也有它的局限。最大的好处,是将历史与现实糅合在一起,又以一种随意的方式出之。最大的局限,也正在这里,一种固定的方式,用于这么长的一部书中,显得太单调了。我竭力想做到的是,两端之间,允执其中,将它的好处尽量地扩大,将它的局限尽量地缩小。纵然如此,仍要提请读者体谅的是,它毕竟只是一种写作的体例,又是一种新的尝试(对我而言),迁就之处多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亦多多。
我不敢说这是一部什么人都可以看的书。就我所知,在中国,除了某一特殊时期,有一种书全国人民都要读以外,世界上还不曾有过这样的书。但我可以大胆地推测:它对那些少小就有志于学术,一时又昧于方法的年轻人是有用的;对那些已有相当成就,又不以眼下的成就为满足,年龄已然不小的学问中人是有用的。再就是,对那些不想着述,也不想精研某种学问,只是喜欢看看书,增加一点与朋友的谈资的风雅之士,也是有用处的。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在别的书里得不到的东西,比如诗文掌故什么的,既滋润自己,也娱悦同侪。
不管是哪种人,有一种功效是敢肯定的,就是让你在短时间内,振作起来,聪明一些。至于这种功效能延续多久,那就看你的造化了。这也是我为什么给此书加上“一位睿智的学者”这么个副题的道理。
感谢降大任、张庆捷、姚国瑾、张继红、苏华、薛国喜、张崇宁、梁金平、李海涛诸位先生与女士,在写作过程中对我的帮助。感谢林鹏先生为本书题签。感谢三晋出版社,肯为我这样一个已然淡出文坛的作家,出版这样一本书。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五日于潺湲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