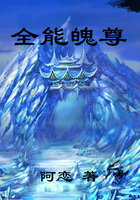甲:你知道,她并不在乎这些。
乙:正因为我知道她不在乎,我才更在乎。
甲:既然你已经做了这样的选择,那就顺其自然也罢,为什么又耿耿于怀呢?
乙:因为我忘不了她。因为我恨自己。是我把她硬推给别人的。
甲:如果她真的如你所愿,过的幸福,你也应该释怀了。
乙:不是这样的。
甲:她很痛苦是吗?
乙:这是她留给我的最后一篇日记:
亲爱的。那天,我走进我们的小屋,一眼看到你熟悉的身影。你知道我有多么想你吗?你为什么狠心留下我一个人出走?这一年,我做梦都是在找你。我曾经千百次地梦到我们能够光明正大地结婚的那一天。你知道我多么想生一个我们共同的小BABY。
可你回来了,却还是要我走开!我就那么令你讨厌吗?我不想说开始是谁招惹了谁。因为我选择了爱你。可你,到底是为什么?
这一年我也想了许多。也许是我错了。我不该按我自己的想法要求你做你不适合做的事。也许我使你觉得太累了。你跟我在一起活得不轻松。所以你走了。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感觉的,我会听你的话走开。我爱你。不想你活的不自在。
明天我要结婚了。你可以自由自在过你想过的生活。不要问他是谁。也不要问我好不好。我只想告诉你,有一个真心爱过你的女人为你祝福。
甲:你真的错过了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乙……
11、笑比哭好
铁轨,明晃晃的。像两条金色的带子,飘向远方。天的尽头是一轮金灿灿的太阳。
那个寒冷的冬夜。整幢大楼黑洞洞的。没有电,没有灯,也没有亮光。我和你蜷缩在那孤独的木板床上。你搂着我的脖子,我搭着你的肩膀。
呼啸的山风,穿透单薄的棉被。我们的脸和脚始终冰凉。不知道雪花什么时候飘来的。只听见冰凌敲打玻璃,就象号哭的狼。
你说:“怕死了。我想我妈。”
我说:“怕,你为啥要来?想你妈,你就该回去过年啊,干吗要留下来值班啊?”
你说:“不来,去哪儿啊?总也找不着工作。我妈我爸已经七十多了。我得多挣点钱,养活他们啊”。
我很吃惊:“什么?你妈54岁才生你?”
你说:“要不我身体总这么弱。我真羡慕你。我要像你有那么多力气就好了。”
我说:“你怎么不说我能吃。我一天的饭,你五天也吃不了。”
你说:“我也想多吃,就是吃多了肚子疼。”
我说:“怪不得你总像个病猫。说话都有气无力!”
我说的你难为情了。你伸过那猫爪一样的瘦手在我胳肢窝抓挠。
你知道我最怕这个。我几乎笑岔了气。一骨碌就滚到了地上。
你使劲抓着被子。我赤条条立在地上:“你再咯吱我就站到天亮。”
你忽然歪着头露出异样的神情:“你要是个男的多好。我就可以嫁给你了。”
我摸摸你的头:“你是不是冻病了?怎么尽说胡话?”
你急了:“谁说胡话?”
我说:“还嘴硬?看我撕你!”
我捂你的嘴。你又咯吱我。直到我不停地打嚏喷,你才说:“我不挠你了,你快来睡吧。”
我们重新裹在被子里。我问:“你是怎么冒出这些怪念头的?我是不是很愣?”
你神秘地笑笑:“不告诉你。”
我说:“不告拉倒。其实我也很想做男的。至少找工作时候不用看那些坏男人的眼色。”
你说:“看不看吧。反正没人把你当女的。”
我说:“那才好呢。谁像你,总像个病西施。团长,连长,总想着照顾你。我也忍不住想照顾你。你准是个妖精。”
你在我额头上使劲亲了一下。
我一急:“妖精真的来了,哈哈哈哈……”。
我很快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发现你又在哭。几乎天天早晨你都在哭。
我真的不明白:“你为什么总是哭啊?又肚子疼了吗?要不你干脆回家看看你妈吧。我去和团长说。”
你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算了吧。”那神情像极了一个小老妇人。
一听到你有事没事的“唉——”,我心里就堵得慌。你哪儿来的那么多愁事儿呢?你总是说父母老了。姐姐在外。自己可怜。那你的爸爸妈妈至少他们还活着啊。像我这样八岁就死了爸爸,弟弟妹妹无人照料,妈妈病得一塌糊涂,我岂不是该上吊去了?
我这样一说,你就又哭了:“我和你不能比。我没力气。我什么也做不了。”
谁说你什么也做不了了?你不能上工地拉平车干活,你不是写的文章和字都挺好吗?你不是做团部文书做得好好的吗?谁也没说你蔼云什么不好呀?那团长政委不是总表扬你懂事吗?像我这样总被人喊愣头青,我岂不是早该把眼睛哭瞎,鼻子飘走了?
你勉强地苦笑着:“我和你说不清楚。反正你也瞧不起我!”
这都哪儿和哪儿啊?我有资格瞧不起别人吗?再说了,就算有瞧不起的人,那也不会是你啊!我想尽了一切办法想让你高兴起来,想让你笑一笑。你可倒好,能把那嘴角往上拉一拉就算是对我开恩施舍了。连笑的时候都能看到眼睛里的泪蛋蛋。
要不是后来响应老人家号召读红楼梦,知道了那书里的林妹妹,我还真想不出来世界上真的有你们这种款式的人。退一步讲,林妹妹哭是因为寄人篱下。你守着自己的爸妈,那谁也不能给你气受,不是吗?又哭个什么劲儿呢?说到挣钱养家,那咱们不是一样的吗?挣钱也不能天天哭啊!先把自己哭死了,谁再挣钱啊?
好不容易,我们结束了深山建矿的日子,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公司机关。我们是被正式招工回来的呀!那是我们盼了多少日夜的事啊!我们一帮舞文弄墨的女孩子堂而皇之住进了钢铁公司的机关办公大楼。笑闹声天天掀翻楼顶。
我天天被主任叫去训斥:“机关有机关规矩。说了多少次,怎么总是嘻嘻哈哈?你这个团支书怎么当的?再管不住她们,我处分你。”
我回来一传达,又多了一条笑料:“哈哈,真的吗?没事。到时候咱们们一起受处分!”因为我们没法儿不笑。
你还是悄悄地缩在角落里。我们几个笑的肚子疼打滚,你也无动于衷。好像你总陶醉在悲哀里。有许多时候,你让我们觉得,笑好像是罪过。
那天,主任告诉我说:“蔼云几次申请要到二级厂去。领导已经同意了。”
我问:“为什么?”
主任说:“她家庭生活困难。二级厂工资高一些。”
我说:“能高多少?”
主任说:“多二十几块吧。”
我想到,我们回到机关以后,工资每月只有33块。比在矿上少了十几块。那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字。至少是一个人每月的生活费。我理解了你的意思。可是我担心你的身体。就对主任说:“她身体那么弱。到厂里干活能行吗?”
主任说:“这点我们也考虑到了。让她到厂机关当打字员。”
走的那天,你没吱声。许多人也不知道。我对你说:“厂里工作比机关累,你自己注意啊!其实你不一定要这样做!我觉得你在机关会发展好一些。”
又是那个苦笑:“没有办法,只能这样了。你好好努力吧。你什么都比我好。”
我无奈:“好什么好?我是傻!我不愿意想那么多。也不想跟领导提什么要求。挣的少,艰苦点。我反正艰苦惯了。”其实,我父亲死时欠的医药费还没全还完呢!
已经二十好几了。我还执守着国家的晚恋晚婚号召。谁让我是团干部呢?我没觉得这有什么不妥。也没觉得找个对象有多么非常重要。时髦话说是响应国家号召。用我妈的话说,就是不开云瓣。我也一直不知道你早已多次沧海。
那个西边火一样燃烧的黄昏,我在公司的门口看到抱着孩子的你。许多女人做了妈妈之后,总是喜形于色的。而你则比以往更加悲哀和憔悴。干燥的头发,和呆滞的目光让我想起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怀中的孩子让我想到非洲的饥民。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慨和焦急:“你究竟怎么了?怎么把自己搞成这个样子?”
你不置可否。只是木木地盯着我。好半天才说:“你好好活着吧。你是个有福气的人。下辈子我一定像你一样活一回。”
我说:“像我一样傻吗?”
你的苦笑:“恩!傻,傻,傻……”
言语之间。我感觉到你飘走了。悠悠忽忽,渐行渐远……
我想喊你回来。可是通勤车已经开走了。
那是一个怎样令人绝望的日子啊。当全公司上下竞相传告着一件令人惊骇的卧轨惨案时,我无法相信那悲剧的主角是我曾经用心呵护爱怜和心痛过的你。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要这样对待自己?是谁把你推向那隆隆前进的轮底?是谁杀害了你?
我向每一个知道你的人打探消息。我向所有处理这件案子的人询问原因和你所遭受的委屈。没有一个人能清楚地告诉我,是谁害死了你。
一次开会的时候,我碰到了你们厂的书记。情不自禁问起了关于你的事。书记说:“这事全怪蔼云自己。我们领导也很被动啊。”
我问:“这事儿不是已经按工伤处理了吗?”
书记说:“不按工伤处理怎么办?从她家情况看,两个老人七八十了,连口棺材也买不起。找的对象是个二杆子。没打死她就够不错。从厂里领导看,咱厂解放以来也没出过这种工人在班上自杀的事。谁担得起责任啊!”
我说:“那她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啊?领导就一点也不知道吗?”
书记:“不是不知道,是不能说。”
我说:“我和她是一个被子里睡过很久的朋友。她是个很柔弱的人啊。领导应该多照顾她才对。”
书记:“当初她从公司下来的时候,领导这么说。我也是这么想的。安排她在机关打字。可是工资按天车工定级。那是厂里女工最高的工资。怎么也该好好珍惜呀!结果时间不长让厂里的一个技术员搞大了肚子。那技术员是不是真的爱她谁也说不清。先答应要和老婆离婚。可她不想想,技术员已经有三个孩子了。能随便离得了吗?他老婆是个医生。就找人给她做了人流。陪了她点钱。这一下把名声搞得很臭。厂里给了技术员党纪处分。她也无法再呆在机关。只好让她下去开天车。因为有了这桩事儿,那些吊儿郎当的小后生都去吃她的豆腐。她害怕,就找了个在厂里打架出名,谁也不敢招惹的愣棒谈对象。结婚以后,只要看见她和男人说话就往死里打她。生下娃娃也不朝理她。她那么文细的人,你想去吧……”
我说:“那也不至于走绝路啊!”
书记说“年轻人不懂事。路子都是自己走歪的呀!”
尽管书记说的有理有据。我还是无法相信这个黑暗的事实。那不是我心目中的蔼云所做的事。
马鬃山下的那个大年初一。我端着从食堂打回来的有一半煮破肚的饺子,狼吞虎咽。你却悄悄地坐在桌前写信。那流利,娟秀,缠绵,连贯的字体,足以胜过多年的老秀才。就因为这,你被推为兵团第一抄写手。团长政委只要看见你写的字儿,就笑逐颜开。我对你的书写佩服得五体投地。总也学不像。只有那时候你是高兴的。你那笑眯眯的样子,总使我幻想自己是男人。我知道我这飞天撂脚的愣性子,永远练不成你那多愁善感缠绵秀丽的字体。只是想看你笑。可是你的笑就象烽火狼烟故事里的主人一样吝啬。
我说:“你不饿吗?再不吃,我可就全吃了啊?”
你说:“你吃吧。给我留几个就行了。”
我急了:“再不吃要成冰坨了,你又想肚子疼啊?”
我不由分说,拿走你的纸和笔,强迫你吃。你含着饺子看着我,眼泪儿又下来了。
真受不了你。我不知道自己哪儿又做错了。赶紧跑到外面去玩冰。我喜欢在冰天雪地里打滚。就像我们村里的小马驹儿。滚出一身汗来,就痛快了。
我知道你在想家,想你妈和你爸。可是哭就不想了吗?我也想,但我哭不出来。我只会喊叫。在那没人的山根下,拔开喉咙大喊一通,听自己的回声。喊的嗓门发烫就好了。
我开始恨那个招惹你的技术员。混蛋!既然有了老婆孩子,为什么还要毁了你?既然爱你为什么不负责任?
我也恨那个可恶的技术员的老婆。她管不住自己的男人,凭什么专欺负你?
我也恨你。你既然知道他有老婆孩子,为什么要献身给他?既然已经有了他的孩子为什么没勇气坚持到底?我知道你一见他老婆就心软了。她有三个孩子。而你只有一个。她是明媒正娶,而你不是。既然你是爱那个讨厌的男人,为什么又要接受他老婆的赔款?你真的只值那几块臭钱吗?既然你已经栽在那个混蛋技术员的手里。为什么不好好找一个懂得疼你爱你的人再嫁?那混世魔王式的凉棒,是你能经受得起的吗?我更恨你,为什么事先你从不跟我说一点点这些事?你从前可不是这样的啊!
我知道你心里爱装事儿。总是自己一个人悄悄地求这个,找那个。找完了受了委屈,就唉声叹气,哭啊哭的。你觉得我不理解你,帮不了你。所以总不告诉我。回想起来,我那时候确实傻帽。你跟我说你十六岁时,就有了一个对象。还说你不喜欢人家。可是没办法。我说不喜欢你就不要和他好不就完了?你苦笑说:“人家天天给我家担水和泥,买粮买菜。还补贴我们一家的生活费。我怎么说不?我要是不,人家凭什么照顾我们家?”
其实,要我看,就是那个你不喜欢的男孩子也比你后来遇的那两个混蛋好。你为了补报人家对你家的帮助,硬是求团长求政委把他弄到矿上。又求领导把他调回来转成正式工。一切办妥了,和人家分了手。那次,我就说你是冒傻气。你照样回我一个苦笑。
你那个抹不去的苦笑,害得我神经衰弱,好长时间睡不着觉。
和小L结婚以后,我跟他说起你的死。他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你知道的,他支左任务完成以后就回部队了。我差不多有四五年的时间没见过他。他父亲病危期间,因为买药的事儿,我们有了联系。后来就结婚了。
有一天,他拿出一个铅字并在一起的图章给我看。那是四个工整的二号篆刻绑扎在一起的图章。精美而幽雅。根本看不出是拼出来的。哇,好漂亮的图章!哪里刻的?
他盯着我的眼睛说:“你肯定想不到是谁送给我的。”
我问:“谁呀?曾经的恋人?”
他说:“是蔼云!”
我差点没惊出病来:“什么?你再说一遍?”
他慢慢地说:“是支左和你们一起工作的时候,蔼云在铅印室送给我的。”
我忽然想到了你下厂以后的许多事。急忙问道:“这么说,她和你谈过恋爱?她爱你是不是?你伤害她了,是吗?你怎么对她的……”
我不喘气地提出一大堆的问题。我没有想过他会怎么反应。我只知道,如果他真的伤害过你,我会恨他。
他说:“我什么也没做。她向我暗示过好多次。我知道她喜欢我。”
我说:“她那么温柔细腻,你为什么不答应她?”
他却狠狠地瞪我:“世界上真是少有你这样的女人。我已经喜欢你,怎么可能再接受她?”
我说:“你是说,你那时候就喜欢我?你告诉蔼云了?”
他说:“我只告诉她,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她只问我是不是你们一起的,我说是。她就再没说什么。”
我真是想不明白。我这样大大咧咧从来没想过要依靠什么人,乞求什么的傻帽,背后总是有我不知道的人跟着。你那么需要人怜惜爱护,却总是被抛弃和伤害。他妈的,这乱糟糟的世界。
火上来我就凶了他一气:“如果你接受了她的爱,说不定她会活得好好儿的!”
他急了,骂我:“真是二百五。我找对象,当然有自己的标准。我不喜欢她为什么要答应她?”
事过之后,他很认真地对我说:“笑比哭好。人活着谁都有难事儿。高高兴兴挺一挺就过去了。成天哭丧,没事儿也哭出事来。再说,人还是傻点儿好。憨憨的省事儿。我就爱你这二百五劲儿。”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不是男人。
一晃快三十年了。那条带走你生命的铁路已经大修过许多次。高速机车在这里进出。厂区的围墙已经拆去。那些主要岗位上工人们,每月平均半个万的收入。那是你我从没想象过的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