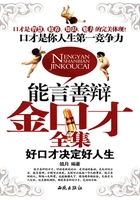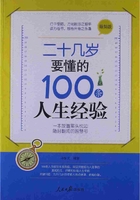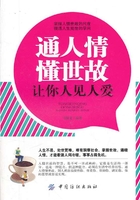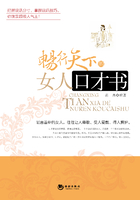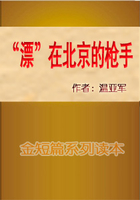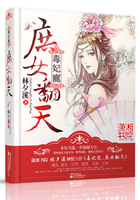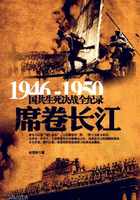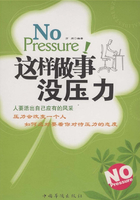萧乾,闻名世界的记者,又是卓有成就的翻译家、作家,被誉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使者。晚年多次出访欧美及东南亚国家进行文化交流活动,写出了300多万字的回忆录、散文、随笔及译作。
他翻译的《篱下集》《梦之谷》《人生采访》《一本褪色的相册》《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尤利西斯》等,皆是畅销书籍。
后来著作等身的萧乾先生,在创作的最开始,也只不过是默默无名的文学青年而已。黯淡无光的开始,却博得了林徽因的赞赏,以及真心的鼓励和支持。
他曾说:"在我的心坎上,总有一座龛位,里面供着林徽因。"
可见他对林徽因的感激之情有多么的深厚。
起初,并未相识的两个人,由萧乾的一篇小说结缘,这才慢慢熟识起来。
当时林徽因给沈从文写了一封邀请信,字里行间透着活泼和热情:
沈二哥:
初二回来便乱成一堆,莫名其所以然。文章写不好,发脾气时还要沤出韵文!十一月的日子我最消化不了,听听风,知道枫叶又凋零得不堪,只想哭。昨天哭出的几行,勉强叫它做诗,日后呈正。
萧乾先生文章甚有味儿,我喜欢。能见到当感到畅快,你说是否礼拜五,如果是,下午五时在家里候教,如嫌晚,星六早上,也一样可以的。
关于云冈现状,是我正在写的一短篇,那一天,再赶个落花流水时当送上。
思成尚在平汉线边沿吃尘沙,星六晚上可以到家。
此问俪安,二嫂统此。
徽音拜上
这是1933年的秋天,冷风瑟瑟,可再冷的寒风也吹不灭萧乾内心的兴奋和紧张。他忽然收到沈从文的来信,"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姐"看中了他发表在《大公报》上的小说,想请他去家里吃茶。这位小姐便是传说中京城文化圈上层精英聚会地"太太客厅"的女主人林徽因。
喜不自胜的萧乾穿上整洁干净的长衫和鞋子,期待着与林徽因相见的那一刻。
他"窘促而又激动"地走进林家,本以为看到的将是一位半躺在病榻上的林黛玉式的美人,结果林徽因穿一套摩登骑马装,精神抖擞,霎时间给了他另一种惊艳,这是他以往没见到过的美。
"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这是林徽因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带着满满的赞赏。随后,这句话被他珍藏在心里,伴随着他的一生。
也许就是这样简单的一句话,帮他度过了无数个想要放弃文学之路的夜晚,无数次给予他继续坚持的信心和勇气。
进屋后,林徽因先向他介绍了刚从正定考察完提前赶回来的梁思成和碰巧来串门的北大教授金岳霖。等到大家都落座后,她热情地为他们沏茶倒水,忙前忙后,不亦乐乎。
第一次见面,林徽因便俘获了一位忠实的"粉丝",萧乾更是深感面前这位刚刚肺病复发,却依旧光彩照人的林小姐,"竟如一首纯净的诗"般潇洒、动人。
林徽因发表在《新月》和《大公报》上的作品,萧乾反反复复读过很多遍,从字里行间,便可以知晓它的创作者定是一位有着纯粹气质的女士。
当萧乾发表在《大公报》上的《蚕》被林徽因发现后,她便想邀请他去家里做客,吃茶聊天。
来到林徽因家中做客的人,多为文坛巨匠、社会名流,第一次被邀请的萧乾难免怀着几分忐忑,坐在角落里,显得很局促。
不多时,他的紧张就被林徽因发自内心的热情所消融了,开始畅所欲言,没了初时的那份拘谨。
"喝茶,不要客气,越随便越好。"林徽因说,"你的《蚕》我读了几遍,刚写小说就有这样的成绩,真不简单!你喜不喜欢唯美主义的作品,你小说中的语言和色彩,很有唯美主义味道。"
那双如水的眸子散发着真挚的热度,她在屋里自顾自地来回走动,说到动情处时,脸颊泛着潮红,感染力极强,也动人极了。
令他感到格外吃惊的是,她竟然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出他的小说,抑扬顿挫的声音,表情丰富,而且一字不差。
她甚至抽丝剥茧,举出文中的几例详细点评,"当蚕幼小的时候,实在常常可以看得出它那腼腆羞涩处,到了中年,它就像个当家人了,外貌规矩,食物却不必同家中人客气。及到壮年,粗大的头,粗大的身子,和运行在粗壮的身子里的粗大青筋都时刻准备反抗的。握到手里,硬朗不服气得像尾龙门的鲤鱼",她高度赞扬如此生动形象的描写,简直要把事物写活了。
鼓励与赞美的话,如果不是发自内心,就完全没有意义。林徽因的这番评价,中肯又积极,完全没有前辈的架子。
林徽因说:"我在香山时,写过一篇小说《窘》,现在看起来,没有你这篇有色彩。读你的小说让我想到,艺术不仅要从生活得到灵性,得到思想和感情的深度,得到灵魂的骚动或平静,而且能在艺术的线条和色彩上形成它自身,艺术本身的完美在它的内部,而不在外部,它是一层纱幕,而不是一面镜子,它有任何森林都不知道的鲜花,有任何天空不曾拥有的飞鸟,当然也会有任何桑树上没有的蚕。"
萧乾入神地听着,生怕漏掉一个字。
林徽因又转向萧乾:"我觉得你那篇小说,最成功的是调动了艺术感觉--那长长的身子就愈变愈透明,透明得像一个钢琴家的手指。一股青筋,絮云似地在脊背上游来游去。我疑惑那就是我所不懂的潜伏在诗魂中的灵感。这段文字真是精彩极了。感觉是什么?感觉就是艺术家的触角。一个作家,在生活面前要有昆虫那样一百对复眼,因为你需要发现的是,存在于人的精神深处的那个不朽的本能,发现人生存于其中的多种形式、声韵和颜色。在感觉过程中,甚至色彩感比正误感更重要。"
在这个时刻,似乎没有人比林徽因更懂萧乾的文字。她的妙语连珠,她的精辟独到,都让他感到深深的钦佩。
他好不容易才按耐住想要呐喊的念头,否则,他一定会当着众人的面,为了心中的喜悦喊出声来。这次茶会之于他的文学生涯,则像"在刚起步的马驹子后腿上,亲切地抽了那么一鞭"。
是她,点亮了萧乾的文学夜空。
1938年7月,萧乾接到从香港发来的电报,告知他去年停刊的《大公报》现已在香港筹备复刊,计划在"8·13"一周年之际出复刊号,请萧乾速速赶往香港。兴致勃勃的萧乾接到电报后,立即跑到林徽因家,把这个激动的消息告诉她。
林徽因听闻他可以重操旧业,也不由得为他高兴,说了许多鼓励他的话,来为他加油鼓气。随后,萧乾马不停蹄地赶赴香港开工。忙碌的日子里,林徽因也不忘时常写信鼓励和支持他。
那一字一句的鼓励,成为萧乾奋然前行的动力,正如一盏明灯,守候在漫长的黑夜中,在孤独无助的时刻,献上最温暖的亮光。
梁从诫曾说:"1931年以后,母亲除诗以外,又陆续发表了一些小说、散文和剧本,很快就受到北方文坛的注意,并成为某些文学活动中的活跃分子。从她早期作品的风格和文笔中,可以看到徐志摩的某种影响,直到她晚年,这种影响也还依稀有着痕迹。但母亲从不屑于模仿,她自己的特色愈来愈明显。母亲文学活动的另一特点,是热心于扶植比她更年轻的新人。她参加了几个文学刊物或副刊的编辑工作,总是尽量为青年人发表作品提供机会;她还热衷于同他们交谈、鼓励他们创作。她为之铺过路的青年中,有些人后来成了著名作家(比如萧乾,又比如沈从文"。"
愿意付出真心的人,才值得深交。在她面前才不会设防,不会绞尽脑汁去反复思量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同时,也不会带着十二分的警惕去揣摩她的言行举止。跟她做朋友不会觉得辛苦,在交往过程中,不由自主地轻松下来。
凡事真心以对,凡事包容以待的女人,她的运气也不会差。她的快乐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去分享,她的烦忧也会有更多的人去分担。能对所有人宽心、包容的人,才更令人钦佩。
不管世界如何改变,怀揣着一颗真心去交朋友的人,才能收获一帮同样真心以待的朋友。真心实意,是太难得的品质。
做自己,最简单也最困难
古希腊的圣城--德尔斐是传说中太阳神阿波罗的驻地,庄严而神圣。太阳神神庙外,刻着一句神谕:"人啊,认识你自己。"
寥寥数字,读起来却令人心潮澎湃,感到一种莫名的感召力。
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苏格拉底也提出过相似的哲学观,即"认识你自己","照顾你的心灵",经过漫长的发展和完善,最后竟成为古希腊哲学,甚至整个西方文化的核心。
德国哲学家康德,将这条神谕归结为三大哲学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
人生是一场奇妙而漫长的旅途,从第一声啼哭开始,直到在别人的眼泪中结束。我们总是与其他人连接在一起,我们受他人恩惠,反过来,我们也去恩惠别人。
很多人无时无刻不在希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和肯定,做别人认同的事情,小心翼翼地征求别人的看法和建议,从别人的眼中找自己,却很少在意自己真正的想法。旁人不会在意我们的内心世界,而我们自己,也稀里糊涂地将它忽视。
真正强大的人,怎会受他人摆布?这是自己的生命,是自己的人生,理所当然要由自己做主。怎么过活,是自己的事情。成为怎样的人,也理应由自己决定。
林徽因这样教导自己的孩子们:"Beyourself。做人不要故意做作,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本分地表现出来。"她用51年的生命历程,诠释了"认识自己"和"做自己"的神谕。
建筑是林徽因穷其一生都在追逐的理想,为之生,为之死。哪怕粉身碎骨,也心甘情愿地燃烧着生命。因为她清楚地意识到,建筑是她生命的不可或缺,是她一生的向导。
1920年4月,16岁的林徽因跟随父亲游历欧洲。在伦敦的房东,第一次让她接触到"建筑"这两个字。从此,与诗歌、绘画同样需要创造力,并且拥有独立灵魂的建筑,在她纯真的心灵里埋下了美好的种子。
1924年9月,20岁的林徽因与梁思成一道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学习。碍于美术学院建筑系没有招收女生的先例,她只得注册了与建筑系最为相近的美术系,并选修了建筑系的主要课程。
相较于得过且过的我们,林徽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知道哪条路通向她的未来。未来确实难以预知,然而我们可以从一个小目标做起,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地走向未来。
未知并不是懈怠、恐慌的理由,些许迷茫也并不能成为无所事事的借口,决不能让一时的彷徨失措,荒废了大好时光,耽搁了未来。
1931年,林徽因受聘于北平中国营造学社,在随后漫长的光阴里,她多次深入晋、冀、鲁、豫、浙各省,实地调查勘测了数十处古代建筑,单独或与梁思成合作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等有关建筑的论文和调查报告,还为梁思成的《清式营造则例》写了绪论。
梦想在心中,目标在前方,路就在脚下,去成为你想成为的人吧!
当林徽因在英国读中学的时候,她认为英国女孩子不如美国女孩子那样一上来就这么友好,甚至因为她们的传统,使得她们性格变得矜持而保守。
矜持是谨慎的态度,而不该是瞻前顾后的墨守成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而对于美国女孩子,林徽因曾回忆道:"开始我的姑姑阿姨们不肯让我到美国来。她们怕那些小野鸭子,也怕我受她们的影响,也变成像她们一样。我得承认刚开始的时候我认为她们很傻,但是后来当你已看透了表面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她们是世界上最好的伴侣。在中国一个女孩子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她的家庭。而在这里,有一种我所喜欢的民主精神。"
这就是林徽因,在小小年纪就能领悟到自身的价值,不应取决于其他人。父母也好,家庭也好,都不应该草率地决定一个人的价值,人们也不应该听凭别人的安排,完全不顾自己的主张,如行尸走肉般为别人活着。
林徽因绝不会因为别人的三言两语就改变自己的初衷,不会因为别人的喜恶来砍掉自己的棱角。她是林徽因,她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彩色人生。
梁思成的母亲李夫人,对于林徽因与梁思成的婚事极其反对。在宾大学习的日子里,梁思成经常收到姐姐梁思顺的信,信中对林徽因加以责难,尤其是曾有一封谈到母亲病情加重,称母亲至死也不可能接受林徽因。
不能被对方的家人喜爱和接受,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打击是很沉重的。这就意味着感情的路上存在一个巨大的阻碍,伤心是在所难免的。
现实中,有多少对苦命鸳鸯,因为家庭的反对而被活生生拆散,有情人难成眷属。梁家母女的种种非难,是林徽因不堪忍受的,更不能容忍的是他人对自己人格精神独立的干预,她是享有自主权的个体,为什么要被别人说三道四,而且她并没有做错什么。
她爱着梁思成,她愿意嫁给他,愿意融入他的家庭,然而,她不能接受他人对自己珍藏的自我持有否定态度,被他们摒弃。
从头到脚,她就是这样的人,她不愿意活在别人的非议里,不愿接受别人对自己人格的横加干涉。如若连最真实的自己都无法坚持,又何谈其他。
正如林徽因创作的《吉公》,讲述了一个身份卑微却灵魂高贵的小人物生命意志的张扬和灵魂对自由的渴求。他不需要别人的恩赐,他要凭着自己的生命去奋斗自己的人生,他要去追求属于自己的生活。
你是谁,由你自己说了算。你喜欢热闹,便去热闹;你喜欢清净,便去清净。怎么能因为旁人说热闹太吵人,清净太孤单而放弃自己想要的呢?
在人与人的关系愈发密切的今天,我们活在人堆里。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逃不过他人的眼睛。评头论足者多之又多,流言蜚语不绝于耳。无形的话语变成有形的压力,压在我们心头,成为禁锢思想的枷锁。
不想被议论,就必须随波逐流,成为大千世界千篇一律的存在。时间久了,连我们自己都忘了自己当初是什么模样,喜好是什么,厌恶是什么,没了自己的想法。
林徽因在那个时代是特立独行的人,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新女性。她无意在男权社会闯出一片天地,也无意要革新、纠正什么,唯一的目的便是活出真我,活出精彩。
她写信给费慰梅说,她写作的动机,是她有真实的感受,有话要说。她笔下的文章,不是为了迎合时代,更不是为了取悦众人。
以我笔,书我心。这是她一直践行的人生准则。
她对自己诚实,对身边的人诚实。隐瞒真实的所想所感,她是做不到的。矫揉造作,假惺惺地伪装自己,更是她难以容忍的,也是让她极其瞧不起的。
如今的时代,备受争议的是女性,备感压力的也是女性。从最古老的三从四德开始,女人就被束缚着。三从四德不见得不好,却用条条框框困住了女人。
形容好女人的词汇很多,我们都在努力做一个好女人,家里家外忙活着,成为好女儿、好妻子、好母亲、好同事、好邻居……
我们为一个"好"字而活,却很少为"人"而活。我们不得不在他人的期许之下,暗自收拾起内心许许多多的小想法、小期待。我们想实实在在地做自己,却又不得不受他人的约束。
我们通过别人来锁定自己的位置,或高或低,似乎总是由别人决定的,随后又因为别人的决定而忽喜忽悲,完全成了木偶人,受别人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