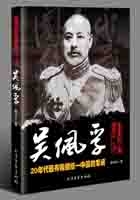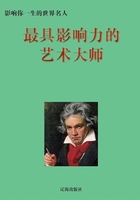甘做"灶下婢"
杨绛的戏剧作品陆续面世之后,杨绛的名字也经常出现在各大报纸和街头巷尾人们的口中,杨绛一度成为当时大学生和戏剧爱好者的偶像,有时钱钟书与杨绛一同出现在什么场合的时候,都会被介绍成:"这是杨绛的先生。"
钱钟书在看过杨绛的《弄真成假》之后,走在回家的小路上,心中有一个想法冒了出来。他对杨绛说,他要写一部长篇小说,这本书就是后来享誉国内外的《围城》。
杨绛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她相信钱钟书有这个想法就肯定会做成这件事,对于文学,他们两个人都对对方有着充分的信任和期待。杨绛为了让丈夫心无旁骛地完成自己的想法,也有更充裕的时间来写作,便让钱钟书减少了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授课时间。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收入紧缩,所以生活上只能更加节俭,恰巧用人家中有事不再做,她便甘为"灶下婢",亲自打理家中一切事物。杨绛曾经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等我是外行,经常给煤烟染成花脸,或熏得满眼是泪,或给滚油烫出泡来,或切破手指。可是我急切要看钟书写《围城》,做灶下婢也心甘情愿。"
那时杨绛想尽办法节省开支,她自己和煤末,做煤球,瘦小的身体踮着脚站在大水缸前,总是弄一脸煤灰;她还负责上街买菜,钱钟书知道她不好意思去菜场,之前的她几乎没有机会去那里,便陪她一起去,两人边说边笑地把菜买回家。
在创作《围城》的时候,钱钟书加入了很多跟杨绛一起经历过的场景,在这本书中也处处能看到现实的影子。在书中,描写苏小姐结婚的场景,就和他跟杨绛结婚的时候如出一辙,那个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新郎像极了结婚那天的钱钟书。
在当时,杨绛的名气是远胜于钱钟书的,后来《围城》的成功证明杨绛的这般付出是值得的。《围城》前后用时两年,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六年。"两年里忧世伤生",钱钟书在《围城》的序中慨叹这两年的时光。
钱钟书也是个浪漫的人,虽然留学西方,但是他更喜欢送东方的礼物给杨绛,比如写诗。
一九五九年他曾经给杨绛写过这样一段带着故事的诗:"弄翰捻脂咏玉台,表编粉指更勤开。偏生怪我耽书癖,忘却身为女秀才。"言下之意,自己的笨拙让杨绛受累了,家中琐事只好拜托她,自己不会家务琐事,只是个会读书的书呆子,由此耽误了杨绛许多读书写作时间来照料自己,从而让杨绛的创作数量大为减少,几乎"忘却身为女秀才"。
这一切可能钱钟书没有说过,但是都在他心中感恩与感动,赞杨绛为"最贤的妻和最才的女"。
八年抗战,全国人民都经历了一场生死的洗礼,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沉重的,对胜利的渴望也就越发迫切,抗战前线捷报频传,一些先进的思想在全国广泛传播,每个人都希望和平民主的那一天快点到来。
上海被日本人控制着,他们像是死神一样,每个国人都怕在街上遇到他们。但这是无法躲避的,就算你躲在家中不出门,意外还是会发生,他们还是会出现。每个深夜的警笛声,都是那样让人心惊胆战,不知道哪天会轮到自己。
一天上午,钱钟书像往常一样去学校上课,钱家众人和杨绛都在家中,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杨绛放下手中的活儿忙去开门,门外站的是两个日本兵。杨绛第一直觉就是来者不善,便客气地请他们进来喝茶,让他们先坐。趁着倒茶的工夫,溜进卧室把父亲的一摞《谈艺录》的手稿藏了起来,稿子是手写的,纸张很薄。
她倒好了两杯茶,端了过来,放在日本兵面前。日本兵问:"这里姓什么?"
"姓钱。"
"姓钱?还有呢?"
"没有了。"
"没有别家?只你们一家?"
"只我们一家。"
杨绛应付了两句后,就退到了屋子里。这时候叔叔看到日本人手中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杨绛的名字,便告诉杨绛躲一躲,她便从后门走了,去朋友家待了会儿,还吃了饭。这时候弟弟来了,说日本兵找的就是杨绛。如果杨绛不出现,日本兵就要把钱家人都抓走,杨绛就慌了神,让弟弟转告钱钟书千万别回家,说完自己就往家走。
路上,杨绛买了一篮子鸡蛋,拎着继续往回走。她走到家门口,敲了敲门,开门的是婆婆,看到杨绛拎着篮鸡蛋站在门口,很是吃惊。杨绛忙摆摆手,示意婆婆别说话,然后自己说:"我给您买鸡蛋回来了。"然后往楼上走,日本兵还在,家里被翻得杂乱不堪,东西散落一地,家中的柜子也东倒西歪。
日本兵问她是谁,她说是"杨绛",日本人大怒:"那你为什么说姓钱?"
她恍然大悟地说:"我嫁在钱家,当然姓钱啊!原来你们是找我呀!咳,怎么不早说?我给婆婆买鸡蛋去了,她有胃病。真对不起,耽搁你们了,我这就跟你们走吧。"
最后日本兵告诉杨绛第二天十点来宪兵司令部受审,说完就走了,军靴走起路来的声音都是那么让人心慌。
全家人都惊慌失措,担心杨绛第二天去会不会出什么事,倒是杨绛不慌不忙,开始整理翻乱的东西,清点是否有东西丢失,最后发现日本人拿走了一本通讯录,还有几封信,钱钟书的手稿幸存。
杨绛并不知道自己到底因为什么得罪了日本人,但是也没有办法,只好晚上准备了很多,比如,日本人提问问题,自己要怎么回答才能解围。第二天到了宪兵司令部,杨绛被问了几个问题,填了个表,就回来了,告诉她可能还会找她,并没有受什么刑罚,万幸。后来听说日本人找的是跟她同名的别人而已。
一同搞戏剧的朋友也有被叫到宪兵司令部的经历,显然没杨绛那样顺利,少则挨两个耳光,多则酷刑加身,生不如死,在日本人的黑暗笼罩下,人人岌岌可危。
父亲去世后,杨绛汇集了父亲生前的一些文章,取名为《老圃遗文辑》。杨荫杭丰富的经历、正义的文笔,加上对现实有力的抨击,有了"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评价。
杨绛曾写过这样一段文字,字里行间都是对父亲无尽的思念:"我父亲去世以后,我们姐妹曾在霞飞路(现淮海路)一家珠宝店的橱窗里看见父亲书案上的一个竹根雕成的陈抟老祖像。那是工艺品,面貌特殊,父亲常用"棕老虎"(棕制圆形硬刷)给陈抟刷头皮。我们都看熟了,决不会看错。又一次,在这条路上另一家珠宝店里看到另一件父亲的玩物,隔着橱窗里陈设的珠钻看不真切,很有"是耶非耶"之感。"
钱钟书写《围城》的时候,进度不算快,每天五百字左右,但基本是一次成稿,很少再改。他每段文字新鲜出炉,第一个"品尝"的一定是自己的妻子杨绛,他喜欢把写好的稿子让杨绛看一下,还跟杨绛交代接下来要怎么写,然后就盯着杨绛的表情,紧张得像个孩子。
《围城》定稿之后,最开始是在《文艺复兴》上以连载形式出现的,随后又编入《晨光文学丛书》。读者反响很好,前后几十载,由多家出版社多次出版印刷,读者遍布国内外,都被这本小说所吸引。钱钟书的知名度迅速提高,之前那个戏剧作家杨绛也变成了"钱钟书夫人"。
当李健吾看到钱钟书的手稿时,十分吃惊,不住地感叹:这个做学问的书虫子,怎么写起了小说呢?而且是一个讽世之作,一部"新儒林外史"!
钱钟书的围城写得实在生动,很多人都信以为真,以为是真发生在钱钟书身上的事情,把《围城》当成了钱钟书的自传来读。读者纷纷来信,表示同情,一些心地善良的漂亮小姐还写信表达要与他做"非一般的朋友",就只因为读了书,实在是同情钱钟书的婚姻,也倾慕他的才华。
就算死,也要死在祖国
随着书籍的畅销,很多电视台向钱钟书发出请求,想把《围城》从书中搬到荧屏上。最开始钱钟书是拒绝的,他觉得小说妙趣横生,拍成电视未必会有同样的效果。
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上海电影制片厂的黄蜀芹,偶然间在延安的一个小书店里看到两本《围城》,便都买了下来。说起来,黄蜀芹与钱家还有些缘分,她的父亲就是当时钱钟书的旧相识──黄佐临。黄蜀芹在拍戏的间隙就靠在小土炕上读这本书,被故事深深地吸引。她就有了拍《围城》的想法,但是她怕去了会被赶出来,之前便听说钱钟书先生曾言"拙作上荧屏实不相宜"。要拍《围城》,必先拜访钱钟书夫妇。
黄蜀芹便联系了父亲,让父亲帮自己写封"介绍信",而且做了充分的准备,跟其他的工作人员反复阅读原著,体会其中含义,编写了电视剧本,然后带着信来亲自拜访两位老人。
到了钱家,两位老人得知是朋友的女儿,十分热情,杨绛给她讲了钱钟书创作《围城》的始末,让大家更好地感受这个故事创作的背景。还对她说:"写《围城》的是淘气的钱钟书。"这句话给了黄蜀芹很大的灵感。
黄蜀芹的父亲黄佐临正是杨绛话剧《称心如意》的导演,在黄蜀芹小的时候,父亲经常骑着自行车带她去当时的长城电影院剧场排演这部戏剧。那时总会遇到在路上散步的杨绛、钱钟书,经常都会聊两句再各自去忙,黄蜀芹对这个镜头记忆深刻。
黄蜀芹带来的剧本,杨绛仔细地读了两遍,标记出来四十多处她认为不妥的地方,并且提出修改的意见,连道具和场景的选择上,她也给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后来都被采纳到拍摄中。
如何突出主题成了黄蜀芹的困扰,杨绛便写了几句话给她:"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钱钟书很同意杨绛的这句解析,对他作品最了解的人,永远都是他的夫人杨绛了。后来这两句话作为旁白,出现在了电视剧的一开头,也成为了这部剧的灵魂。
《围城》拍成电视剧总共十集,导演当时因为受伤,是在轮椅上完成这个工作的。当时导演和演员陈道明、葛优等人认真地核对剧本和原著,前后拍了一百多天,每个镜头和环节都力争体现原著风格,让那些本在书本里的人物,立体地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电视剧上映之后,他们一家三口都看了,很欣赏里面人物的表演,他专门写信给黄蜀芹说:"与适自英国归来之小女,费半夜与半日,一气看完。愚夫妇及小女皆甚佩剪裁得法,表演传神……此出导演之力,总其大成。佩服佩服!"
那段时间他们的生活中,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朋友,就是傅雷。傅雷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和美术评论家。他也曾留学法国巴黎大学,算起来还和钱钟书、杨绛是校友。
傅雷一家那段时间与钱钟书、杨绛也走得很近,两家住得不远,所以有时间了就会互相走动,促膝长谈。大家都对这个社会有太多要控诉的事情,都在黑暗中期待黎明。人们在畅谈中释放压力,抒发情感,那种心灵与心灵碰撞的火花,在回忆中依然闪亮。
在杨绛的记忆中,傅雷总是挂着笑容的,与外界说的"严肃死板"截然不同。他总是和钱钟书面对面聊天,手拿着烟斗,嘴角含笑,他和钱钟书很聊得来,可以聊很长时间,按照杨绛的说法就是:"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钱钟书是唯一敢与他当众开玩笑的人。一次还有其他朋友在的时候,钱钟书和傅雷开了个玩笑,另一个朋友以为钱钟书是个"没轻没重"的主儿,便赶忙使眼色,告诉他"闯祸了"!傅雷不但没生气,还跟着大家一块笑。
不过,在孩子面前,傅雷几乎是不笑的,傅雷的两个孩子阿聪、阿敏喜欢留在客厅里,听大人们聊天。傅雷是不允许的,他或许出于自己的考虑,怕孩子理解错误,或出去说给别人听,那个时代是真正的"祸从口出"。
一次,朋友们在客厅里聊得风生水起,好不热闹,不知他是突然想到什么,就轻手轻脚地来到客厅门旁,一把拽开门,看到两个小顽童正侧着脑袋听声儿呢,傅雷大声吼了一下,两个孩子急急忙忙跑上楼梯。太太忙跟了上去,唱白脸,两边疏通。大家继续聊天,笑声四起,傅雷又过去拽那扇门,两个孩子还在那里,跟着大家笑,真是"知子莫若父"啊,他就知道孩子还会下来。
傅雷比之前更加愤怒,大声地呵斥着孩子,太太想劝却劝不了,其他人想劝不敢劝,孩子委屈地在那哭,只能待傅雷呵斥结束。这也许就是外界盛传的"严肃的傅雷"吧,大家面面相觑,领教了!
胜利像黎明一样终将到来,人们殷切期盼的和平像温暖的阳光,温暖着被战争冷却的生活。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前方传来日本投降的消息,举国欢庆。钱家人都聚在一起,商量着要纪念下这个日子,庆祝黑暗的过去。杨绛心里有些难过,便独自躲到了亭子里,默默地流泪,钱钟书过来安慰她。
她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在世之时只愿能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可是这一天来了,父亲却不在了。钱钟书安慰她,紧紧地握着她的手,说:"爸爸会为我们高兴,为国家高兴,我们终于熬过来了。"
抗战结束后,钱钟书辞去在震旦女子文理学院的工作,来到中央图书馆做外文部总纂,主要负责编写《书林季刊》,徐鸿宝先生曾对战时中央图书馆馆长说:"像钱钟书这样的人才,两三百年才出一个。"
《围城》受到广大读者的热捧,钱钟书又在暨南大学兼任教授,还兼任英国文化委员会顾问。随着工作重心的改变,钱氏夫妇的生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之前只顾埋头创作的两人,有了越来越多的社交生活,也结识了更多志趣相投的朋友。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很多爱国知识分子都收到了国民党投过来的橄榄枝,钱钟书、杨绛也不例外,但是两个人毅然地放弃了去台湾的机会,不仅仅是因为拥护共产党,他们也不愿意离开自己从小到大生活的热土,这片土地刚刚经历了创伤,需要人们去抚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