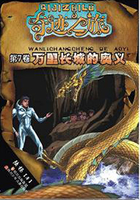谨小慎微的患者往往令人疲于应对。“鸥庄”的徐铭义刚感到身体有点儿发冷,就马上给“桃源亭”打来了电话。
“现在是十二月,谁都会觉得冷的。”陶展文走进徐铭义公寓里的房间,放下皮包,随后继续说道,“还有,那绷带太碍眼了,能否先摘下来?”
徐铭义老人额上长了一粒仅比粉刺略大的疙瘩,他却小题大做地用绷带缠了起来。
患者无精打采地坐在床边说道:“不只是发冷,从前些日子起,我就开始觉得恶心,浑身上下都直打哆嗦……莫不是长久以来过于勉强,日积月累,最近一气爆发了?”
“我看看。”说着,陶展文将转椅拖至苦恼的老人面前。
看着他的举动,老人的样子显得有些胆战心惊。徐铭义有洁癖,房间一向都收拾得极为整洁,哪怕仅仅挪动一个物件,也会令他感到明显的不安。
顺着朝西的窗户并排摆放着办公桌和书架,桌上只在靠左边的位置放有一个手提保险箱。若在平日,这里一尘不染,诸如便条之类的更是无处容身。但现在,桌上却大咧咧地摆着陶展文那可怕的皮包。这个无视场合的不速之客似乎已深深触痛老人的神经,而他则尽力装作视而不见。
衣柜和床贴着东侧墙壁,房间正中央摆着一个貌似小方桌的东西,那是某外贸商转让给他的打字机台座,两侧各放一张折叠椅,整齐地相对而立。在靠近门一侧的椅子后面,还放着一个很大的火盆。
陶展文刚才是拖着办公桌的专用转椅,绕过火盆,径直来到床前的。看着他那经由拳法锻炼出的魁梧身躯如此毛手毛脚,也难怪老人会在一瞬间露出近乎于恐惧的神情。恐怕不仅是房间被搅得乱七八糟,老人觉得自己的神经也难于幸免。
当陶展文宽大的手掌接触到徐铭义的面颊时,老人终于放下心来,眼前这只手的确是医生的手。很快地,那只手便拿开了。
“只要摸摸额头,就能立刻知道是否发烧,可惜你头上缠着绷带,无法下手。虽然仅靠触摸脸颊难以得出准确的结论……”
接着,陶展文又检查了老人的双眼。
“你没生病。”他断言道。
“不,不可能。”老人呻吟般地说道,“我全身上下到处都疼,浑身没劲儿,说不出来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是生病了……肯定是生病了……”
“好吧!”陶展文打断了老人,继续说道,“那你把头低下。”
徐铭义低下了头。兼任中医的陶展文伸出胳膊,将手探入老人稀疏的头发中,挠了两三下,随后便开始观察残留在指甲缝中的头皮。过了片刻,他慢慢伸出舌头,凑近自己的指尖。
“嗯,你的健康状况的确有些问题,但并不要紧,只是乍感风寒,而且仅仅处于病菌潜伏期……什么?头疼?暖暖和和地睡一宿,很快就会好的。不必担心,我现在就开方子,到明天就会痊愈的。”
据传,中医里有一种秘法,便是通过品尝头皮的味道来诊病。陶展文在国内时也曾见过这样的医生。据说,为了保持舌尖的神通力,这类医生禁忌一切刺激性食物,至于烟酒更不待言。然而陶展文是个烟鬼,对所有烈酒又来者不拒。纵是食物,他也偏爱又麻又辣的。因此,他的舌头不可能拥有那种神奇的能力,但他不时地仍会使用这一招。他会装作舔尝头皮的模样,但实际上并未舔到。但作为取信于患者的小把戏,这一招可以起到很好的心理疗效,尤其是针对徐铭义这样的患者。
“是这样啊,那就拜托你了。”听到自己确实染病在身,徐铭义似乎终于松了口气。
陶展文再次拖动转椅,回到办公桌前。他必须要写处方。原本他并未打算成为医生,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开始研究本草,不知不觉间就变成了半个中医。他先是熟记医诗,接着研究大量处方,渐渐地,便开始回应殷切企盼的患者们的要求了。
所谓医诗,是指以诗的形式表述疾病的性状以及治疗对策,以易于初学者记忆。徐铭义的伤风实际上并无大碍,问题在于他的慢性胃病,头痛和恶心的原因皆在于此。
有医诗曰:
温温欲吐心下痛,郁郁微烦胃气伤。甘草硝黄调胃剂,心烦腹胀热蒸良。
亦即是说,君药(君药,药方中对主要症状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为“甘草”。硝指“芒硝”,黄即“大黄”。先取“大黄”四钱,去皮后用清酒洗净,继而配以三钱“甘草”、两杯清水一同熬煮,而后滤掉渣滓,加入“芒硝”,再以文火加热服用。“芒硝”的分量以三钱左右为宜。
“给,只要喝下这剂药,立刻药到病除。”
徐铭义毕恭毕敬地接过了处方。
“别闷闷不乐的。”陶展文一边将钢笔插回胸前的口袋,一边说道,“不如下盘象棋吧!这个月你总是输,我已经赢了有二百日元了吧?怎么样?来场雪耻战?”
“今天不行。”老人答道。
“为什么?”
“因为没有棋子,想下也下不成。”
“没有棋子?这是怎么回事?”
“打翻墨水时,把棋子弄脏了。”
“原来只是墨水……多脏我都不介意。若是觉得影响心情,用消字水擦掉不就行了?”
“墨水已经渗入木中,用消字水也无济于事。”
老人摇摇晃晃地来到折叠椅前,一屁股坐了下去。
“那太可惜了。”陶展文说道。
“棋子脏了也没心情去碰了。”徐铭义一副可怜相地说道,“上次我托南京街(南京街,神户市中央区的唐人街。)的刘先生帮我买副象牙棋子,他明天大概就能带来。”
徐铭义的洁癖实在太严重了。只是下一盘棋而已,用脏掉的棋子又有何不可?不知为何,陶展文此刻变得无比渴望下一盘象棋。
“能否将就一下,就用染上墨水的棋子下一盘?只下一盘总可以吧?输赢不记账也行啊!”“没办法。”徐铭义摆了摆手,“那副棋子已经送给朱汉生了。”
“什么?被朱汉生拿走了?”陶展文不禁大失所望。
徐铭义的中国象棋的棋子虽为木质,却是上等货色。只因染上一点点墨水,就被朱汉生不费吹灰之力地骗到了手,而新棋子要明天才能送到。看来,现在只能去找朱汉生一解棋瘾了————想到这里,陶展文便站了起来。
“不是二百日元。”徐铭义突然说道,“我应该输给你三百日元了,不信我拿给你看。”
“不用,不用。”
可是,徐铭义依然颤颤巍巍地站起身来,将手探入红色套衫的口袋。
陶展文曾建议老人穿红色的衣服,说这样有益健康。一个独居的忧郁老人,他觉得还是稍微打扮得艳丽点儿好些。徐铭义在自己的房间里时,一直忠实地遵从着陶展文的建议。此刻,他从这件红色套衫的口袋里取出了一串钥匙。
徐铭义打开桌上的手提保险箱,里面放着三本黑皮出纳簿,封面上分别写有“壹”“贰”“杂”三个白字。徐铭义取出写着“杂”的账簿,翻了开来。
“我记的果然没错。十二月以来我们下了七盘,你赢了五盘,我赢了两盘,到现在我已经输了三百日元。”
徐铭义将那一页摊给陶展文看,上面一笔一画地记录着输赢情况。真是位一丝不苟的老人。
“我知道啦!”陶展文点了点头。
徐铭义仔细地将保险箱内部整理妥当,小心地合上了箱盖。
“这个世界真是越来越可恨了。”徐铭义一边上锁,一边说道,“有人竟然说要杀我,要杀我这个病得骨瘦如柴的无辜老人。”
倘若继续留在这里,势必要听老人唠叨足足一个小时。若在平日,陶展文早已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迅速逃之夭夭。然而,前几天他刚从小岛那里听闻徐铭义与吉田庄造之间的关系,虽然他并无心刺探这位与自己同为中国人、又是个可怜患者的老人,但陶展文的好奇心异常强烈,他心里想,或许能打听出些什么。于是,本来已经站起来的身体又重新坐回了转椅之中。
“你就听我说说吧!”老人说道,之前有人向我借钱,还是跪下来求我的,可如今不要说还钱,他甚至扬言要杀了我,你怎么看?”
徐铭义一直在放高利贷,有时难免遭人记恨。所谓的“杀了你”不过是那些自暴自弃之人的陈词滥调,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是真的,那人还给我写了封信,我拿给你看。”
老人打开办公桌右侧的第一个抽屉,里面放有一个装信的文件夹。他取出文件夹,放在桌上翻看起来。
陶展文也飞快地瞥了几眼。会不会有吉田庄造的信呢?徐铭义用微微颤抖的手翻动纸张,但其中似乎大多是政府机关的通知及不动产登记的相关文件。陶展文的眼部神经立马松懈下来。自己这种好像偷腥猫儿的眼神实在可笑,像吉田那样的大人物,想来也不可能用能当做证据留下的文件形式与徐铭义联络。
“找到了。”
徐铭义将文件夹递给陶展文。虽然兴致寥寥,他也只有粗略地浏览一遍。不出所料,字里行间都是些表达怨恨和痛苦的语句,结尾部分也的确出现了几句威胁的话,但语气并不强硬,更像是战战兢兢地写出来的————就算我完了,也要拉你当垫背……之类的。
“仅就此信来看,对方是做不出杀人这种事的。放心吧!”
“你不知道,那人非常狂暴,说不定真会杀了我呢!他好像是挪用了公司资金,为了填补漏洞才向我借钱。唉,当初不借给他就好了……”
“只是威胁而已。”陶展文断言道。
“是这样吗?”老人有些怀疑。
“老爷子,你只关注世界的阴暗面,有点过头了。这个世界并非只有那些令人讨厌的事。既然有威胁要杀你的人,就肯定有帮助你的人。你算一算,包括养育你的双亲在内,至今已有多少人对你好过?用两只手肯定数不过来吧?”
陶展文凝视着对方的眼睛,口中循循善诱,宛如一位运用暗示疗法的医生。
似乎有些效果了。老人微微点点头,貌似有了新的认识。
“的确如此……你就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好多人————朱汉生也可以算一个,还有那些已经淡忘的昔日友人……对了,不久前我意外地遇见了一个人,是我以前工作的上海银行里的大人物,说是几年前就来日本了,真令人怀念啊……对了,他还开了家店,和你在同一幢大楼里,没错,就是东南大楼……”
“东南大楼?如此说来,是五兴公司喽?”
“哦?你知道?”
“我只知道店名。自半年前五兴公司挂牌营业时起,我就开始留意,因为都是中国人。虽然时常会在走廊里遇见店主,但对方好像并不知道我是中国人,至今连招呼都从未打过。”
“他住在山本大街,还叫我去玩……在上海时承蒙他多方关照,如今他好像是孑然一身。”“和你境遇相同啊!”
“这些倒无所谓,总之很令人怀念。我应该过去坐坐……”
“五兴公司现在来了一位重要的客人,是个很有钱的客户,说是南洋的席有仁……”
“席有仁!”听到这个名字,徐铭义不禁叫出声来,“瑞和的席先生?他也很令人怀念啊!”“你认识席有仁?”
“岂止认识!他以前陷入困境时,是我们银行帮助了他。他确实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不到两年就来将贷款全部还清了。当时我还给席先生做向导,带他把整个上海都游玩了一番。”
“这可真是巧啊!你竟然认识席有仁,实在厉害。”
“席先生已经成为真正的大人物了……对了,现在席先生住在李先生家吗?”
“你所说的李先生就是五兴公司的社长吧?我不太清楚。像席有仁那样的大富豪,想必会住在某个大酒店里。他应该会经常去五兴,你若想见他,只要联系五兴就可以了。”
“这样啊————席有仁……”徐铭义像个小女孩一般神情陶醉地嘀咕了片刻,然后回过神来,继续说道,“我要去见他。我想,无论他如何飞黄腾达,都不会忘了我的。毕竟在上海时,是我每天带他四处游玩的。”
“他如今是举世闻名的大富豪,甚至有人说过,总有一天,天下的财富都会被席有仁尽数收入囊中。你若去见他,总能得到些零用钱的。”
“胡说!”徐铭义急忙否认,随后陷入沉思,片刻之后才说道:“我可没有那么卑鄙的念头……不过,或许我的确得请他帮个小忙……”
“只要席有仁稍微动动小指头,你的伤风什么的很轻易就能痊愈。还是去见见他为好。”
“我最近,嗯,工作上……那个,不太顺利……同伴洗手不干了……唉,这些事对你说也没用……”
徐铭义虽然言辞含糊,陶展文的眼中却在瞬间闪过一道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