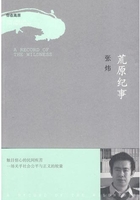新加坡以及马来亚 (马来亚,马来西亚独立前对马来西亚西部地区的称呼)的诸位读者,请你们以手扪胸,细细回想。敢问各位,对你们而言,日本真的是一片前所未见的土地吗?的确,各位想必并未亲眼目睹过日本的风物,但你们定在十几年前见过满城皆是的日本人。不只是军人,还有执政官、军属、百姓,各种各样的日本人成群结队,在我们的土地上招摇过市。难道不是吗?新加坡也好,马来亚也好,都成了日本人的天下————这里我所指的并非仅是新加坡市被更名为充满日本色彩的“昭南”一事。我们都曾见到,他们将日本带进新加坡。那时我是抗日团体的干部,一直在槟榔屿(槟榔屿,位于马来西亚西北部、马六甲海峡北部的岛屿。)躲避他们的追捕,整日躲在藏身之处提心吊胆。我当时很怕日本人,做梦都未曾想过有一天会来日本游玩。但如今,日本的河山正展现在我的眼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片土地并非是我从未见过的。相较于纯粹的陌生土地,这里似乎更能激起我格外的热情。
不知不觉间,我已感到眼眶发热。或许有人会提出非难,认为这种表述夸张得让人唾弃。为了让各位能准确理解我情不自禁流下的泪水,我必须在此略作说明。虽是个人私事,本人亦甚感惶恐,但若不作说明,在今后连载时,我所写见闻的背景————换言之————笔者的内心状态就会被厚厚的幕布彻底遮挡。对写文章的人而言,最渴望的大概便是得到读者尽可能多的理解。因此,请允许我在这里对我的个人私事稍作提及。
二十多年前,我事业失败,进退维谷。倘若不得脱困,只怕将就此没落。于是我多方奔走,希望能够摆脱眼前的窘境,却没有一家银行 肯理会我。但出乎意料的,上海的 H银行向我伸出了援救之手,提供给我超出事业重建所必需的贷款资金。这无异于雪中送炭。我原本消沉的内心立马坚定起来,高举得来的这柄利剑,重新杀向事业的战场。
据说,当时 H银行的干部一致反对向我融资,只有董事长 L氏不顾众人反对,断然决定向我提供援助。L氏那时刚成为董事长,也很年轻。或许有些僭越,但我不得不说————他的确很有伯乐之能,因为我没过多久便将贷款悉数还清了。那时我给 L氏写了一封信,其中附有事业重建方案,L氏在避暑地看了一遍后,当即就作出了融资的承诺。可以说,他一眼便看出了我对事业的无比热忱。
当时,我在心底发誓,终生决不忘 L氏的大恩。我一头埋入事业之中,虽然贷款已经还清,但我要获得更高的成就给 L氏看,这是我的心愿。不幸的是,战争爆发,这一夙愿终究化为泡影。然而,在我事业复兴期间,正在海外视察旅行的 L氏不断来信激励我,我也给他写去回信,表达了自己不甘做吴下阿蒙的决心。由于战争,我们的书信往来暂时中断。更令人难过的是,L氏的银行不幸倒闭了。后来我才得知,他在日本的神户。
而正是这个 L氏,今天亲自来神户的码头迎接了我!
席有仁放下钢笔,望向窗外。湛蓝的天空中悠然飘荡着两三朵薄云,令他忆起了南洋天空的颜色。在他出发时,新加坡的天空呈现出一种仿佛用牛奶稀释过的蔚蓝色。
片刻之后,他重新拿起钢笔,继续写道— ———
L氏的帽子上插着一朵黄色的小假花。他主动伸出手向我走来,开口说道……
同样在神户市内,还有一个人的思绪也飘向了南洋。只不过,那人心里想的并非天空,而是更低的地方————某处地下,以及周围的标记。
市议员吉田庄造抱着胳膊,双眼紧闭。他的一张红脸看起来精力旺盛,颧骨附近还泛着黯淡的光泽。
吉田的侄子田村良作此时正端端正正地坐在叔父面前。他偷偷地瞥了叔父一眼,却猜不透他的心思,不禁感到坐立不安。自打从东京来到这边,他一直装作老老实实。眼下,他只能仰仗这位叔父,故而努力抓住一切机会来迎合对方。他会配合叔父的心情,采取相应的态度。在这方面,他还是颇为自信的。
但即便如此,倘若无法摸清对方的心理状态,终究无计可施。吉田庄造此刻看似精神恍惚,田村心想他或许正在思考什么对策。
关于叔父的工作性质,田村渐渐地也开始有所了解,毕竟他来这里已有一个月了。
吉田庄造的所作所为并不光彩。坦白来说,便是在工商业者和政府机关之间斡旋,从前者手中敛取酬谢金。而且,他并不直接经手所敛钱财。吉田庄造是一个格外谨慎的人,所有这些钱都会通过专属的秘密渠道洗白。不过,他最近觉得有必要对部分洗钱人员进行更换,田村似乎便已被提拔为新的一员。
叔父脸上的肌肉一动不动,不知他是在思考对策还是心情不悦。若是后者,原因恐怕便在于《中央报》今早的报道。那篇报道的标题 是“与工商业者的孽缘”,虽然并未指名道姓,内容中却写有“某有权有势的市议员……”显然是在暗指吉田。
“今早报纸上的那篇报道……”田村小心翼翼地开口说道, “想来想去,还是徐铭义那老头儿较为可疑。”吉田庄造微微睁开双眼,开口喝道: “混账!他可是这个世界上最能守口如瓶的人。”既然如此,那又为何要剥夺他洗钱人员的资格呢?不过很快,田村的这一疑问便告消解。吉田有点恍惚地说道:“只不过,他有些不知变通,算是白玉微瑕。”
说到变通,田村对自己相当有信心。他以前一直变通得太过离谱。年到四十的他经历过无数失败,而究其原因,其一是酒,其二在于女人,其三便应该是变通过度。
吉田庄造再次闭上双眼,想着埋在地下的小铁盒,不知是否已经锈蚀破裂?不过,纵然有所损坏,也不会伤及里面的东西。
然而,他的思绪并未在遥远的大洋彼岸多做停留,他是一个现实的人。吉田庄造睁开双眼,瞥向桌上的一张纸片,上面罗列着一串数字。
“还有没处理完的?” “还有四十多万日元。”田村立即答道。 “四十多万?”吉田有点儿不快,“太不小心了。” “总之我会在近期全部处理干净。” “处理完记得将以前的账簿收回。那人虽然嘴巴很牢,但手中握着可疑之物,也可能会出意外,还是小心为上。” “明白。”说完,田村轻声吹起了口哨。 吉田庄造不禁皱起眉头。虽然田村已尽力装出叔父喜欢的态度,但人的恶习却是很难改变的。
一位满头银发、身材瘦高的绅士走出 S酒店,仰头望向天空。阳光中还残留着对晚秋的留恋。这位老绅士————五兴公司的李社长继而左右张望,像是在寻找计程车,却连影子也没看到,只好迈步前行。天气无比晴朗,就这样步行回事务所也不错。
当行至东亚大街(Tor Road)时,他与两名男子擦肩而过。那是两个衣着邋遢的男人,其中一人头缠绷带、面戴口罩、弯腰曲背,无疑是个老人,但恐怕实际年龄并没有外表那么老;另一人身材矮小、略微跛脚,额上有道小小的伤疤,且目光混浊,看起来毫无生气,年龄在五十左右。
双方刚一错过,头缠绷带的男人便回过头来。他摘下口罩,开口唤道:“这不是李先生吗?”银发绅士面带疑惑,久久凝视着对方的脸。 “啊,你是……”他似乎终于想起了对方的脸,却又说不出名字, “你是会计……兴祥隆银行的会计……”“没错,是我,徐铭义,曾经当会计的。”头缠绷带的男人说道。 “对对,我们多少年没见了?” “都二十多年了。” “有那么久吗?” “您的头发可都白了一大半儿啦!”头缠绷带的男人说道。“的确。”老绅士摸了摸头, “不过,没想到你竟在神户……”
徐铭义解释道,他离开银行后便立刻来了日本,历经千辛万苦,如今终于拥有了一幢公寓,好歹能够维持生计…… “我已将公寓交给他管理,他是日本人。”
同行的矮小男人脸色阴沉地盯着电线杆上的宣传画,并未意识到自己成了二人交谈的话题,不过这两位旧相识一直是在用中文交谈,也难怪。
“我已尽了最大努力,可银行还是在战后倒闭了。”当提及银行时,银发绅士似乎仍很伤感。接着,他扼要地讲述了自身的一些境遇,如今他在做生意,来这边也才半年左右,现住在山本大街的公寓,最近正打算另寻租处…… “有空去我那儿玩吧,虽然地方有些小。”“一进那条巷子就是我的住所。”头缠绷带的老人也向对方告知了自己的住址,他就住在属于自己的那栋公寓里。
“有空我会去的。”五兴公司的社长说道。随后,二人便郑重地握手道别。五兴公司处在海岸大街东南大楼的二楼。李社长沿着东亚大街,朝着海岸大街的方向径直走去。
东南大楼共有六层,建于战前,相比近期在周围林立起来的新建筑而言,难免给人一种人老珠黄之感。大楼的持有者————东南汽船公司占据了整个一楼,自二楼以上都是外租事务所,多为外贸商社、保险公司、船运企业等,也有几家外国公司,但只有二楼的五兴公司是中国企业。
身形瘦削的李社长登上略显昏暗的楼梯,身影消失在了二零八号房间。
五兴公司的确是东南大楼内唯一的一家中国企业,但除公司外,楼里还有一家中国人经营的店铺,便是位于地下室的餐馆————“桃源亭”。
《中央报》的记者小岛和彦此时正坐在空无一人的“桃源亭”里。他看了看时钟,站起身来说道: “店里马上就要忙起来了,今天先告辞了。”
店里晌午时分是最忙的,过了五点的下班时间后,也会有些客人。浑身肌肉虬结的店主陶展文从座椅上站起来,说道:
“不好意思,小岛君。徐铭义既是我的朋友,又是我的病人。我不能去刺探他,这点还请见谅。”
“没关系,我会自己调查的。” “既然你要自己调查,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一送走小岛,陶展文便大大地打了个哈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