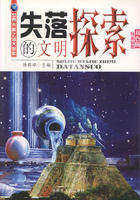如今黛玉却也被安上了一个“掌柜”的名号了。对黛玉来说,这仅仅是一个名号而已,并没有其它任何意义。她并不是因为这君安客栈有多么华贵、有多么舒适、有多么多金而沾上了这个名号,她仅仅是为了胡秀才的那句话“生在君安,魂归君安”。
她不希望这七人眼睁睁地流亡他乡。这七个人与其说身无分文的流亡他乡,还不如说这是一次具有悲壮意义的慢性自杀过程。
她想到这里,便说道:“你等待我盛情难却,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那七人听了,各个喜逐颜开,于是君安客栈的主人从此换了姓名。
黛玉自接管了君安客栈之后,各事还依旧例,并无创举,只因扬州正闹洪灾,客栈生意门可落雀,又因她只是个滥竽充数的名誉掌柜,并不起什么实质作用的。她便依然将事情放到了帐房、厨子、杂工、保安的手里。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七个人因忽然手里有了自主的权利,因此倍加珍惜,各个勤奋做事,虽是淡季,君安客栈的生意反倒一日胜似一日。那七人都赞那黛玉领导有方,而黛玉心里本无心为此,却见这生意蒸蒸日上,她的心事更不在这上面了。
这样过了几日,君安客栈的生意也好了起来。黛玉便派保安步求败出外打探消息,以便她买布事宜。
这一日她正忙得昏天暗地之时,忽然杂工高媛媛嗫嗫嚅嚅的跑来了。
“林掌柜,大难临头了。”高媛媛咋咋呼呼地说。
“谁给你这张乌鸦嘴的?”黛玉看她一脸惊恐的模样,因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依然笑问道。
高媛媛听了,便指了指外面。
“有什么话便说,说什么哑语,打什么哑谜?”黛玉说这话时微有怒意,又忽然笑道,“你可是有步求败的消息了?”
高媛媛听了,又指了指外面,复而直接拉了黛玉往那边走。
黛玉见了,忙道:“高媛媛,快放开我。你可知你是个黄花闺女,怎么可以光天化日之下非礼你的掌柜公子呢?”
高媛媛不依,依然一边往前走,一边仿佛若无其事的说:“我的林掌柜、林公子,现在可是夜晚!”
黛玉终究只是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哪里比得上那常做杂活的高媛媛力气大,便只能被她拉着往君安客栈的大门而去。
黛玉却什么声音也听不到,周围的夜色显得格外寂静,仿佛那些喜欢在秋天夜色里思春的昆虫们、雀鸟们、猫儿们也停止了动作。
看来这君安客栈真是“大难临头”了!
那高媛媛把林黛玉拉到了君安客栈的接待大厅里,只见其余六人已经像做了错事的小绵羊,各个低头垂手的立在接待大厅的左侧。
“听说君安客栈生意红火,下官特来拜访拜访,如果贵客栈的致富经验可以借鉴并加以普及推广的话,说不定扬州百姓从此便可安居乐业,日子一天更比一天好起来。”那为首的一个身着白袍子的人抑扬顿挫地说,仿佛在吟诵一首唐诗。
黛玉刚刚看见这身衣服的时候,还以为这君安客栈闹鬼呢,吓了一跳,毕竟前不久真的死了两个活生生的人的。
这抑扬顿挫的话仿佛催眠曲一样催促着黛玉的心情平静了下来。冷静的她马上意识到这扬州县官说话装腔作势,照理她本应该说些“无事不登三宝殿”的客气话的,如今她偏偏既不叩拜,也不行礼,装作是没有见到一样。
那白袍子旁边的人见这君安客栈的新主人对他的旧主人如此轻慢无礼,激动的捋了捋他青青的胡须,大声说道:“大胆刁民,见了我们县太老爷,还不下脆行礼?”
黛玉听那青胡须的说话,便猜测他是个师爷。
只听“呼”的一声,黛玉一边打开她的扇子,一边上下打量这二人,说道:“我看你二人是招摇撞骗之辈,我从未在书里见过‘县官穿着像鬼,师爷说话像狗’的记载。你说你二人是官,可有证据没有?”
她在说话的时候,君安客栈的七个人却面露惊恐之色,心里实不知这林掌柜在打着什么算盘。
那扬州县官听了黛玉的话,知是骂他。他本想生气,又怕失了他扬州县官的威信,笃定要叫这外来的生意人心服口服,于是他忙将一双猛眨的眼睛移向那个青胡须的师爷。那师爷露出一脸无奈又无辜的表情,囧然的两手一摊。
黛玉见了,便知道他二人并未带官印在身,也没有其它可以证明他们身份的证据。于是她便说道:“既然你们无话可说,本店也早已打烊了,二位客官要是没有什么别的事吧,还请回去吧。这风高天黑的,真要出了什么事,我们君安客栈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
“哼,你是新来的不是?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你当掌柜的不认识我,难道他们不认识我吗?”那师爷说。
一旁的县官听了,便用手里的纸扇子敲了敲那个师爷的头,“你真是吃饱了撑的,还有我呢!”
那师爷忙用手护着他的头,回头以一种极尽谄媚的表情看了看县官,然后无比抱歉地对林黛玉及众人说:“还有他。”
黛玉回头看了看那六个人,纷纷如小鸡啄米一样直点头,便确定了白袍子和青胡须并无虚言。因想着这县官是个装腔作势之辈,却掩饰的极好,如今全赖这青胡须师爷周旋。若是落了什么话柄在这师爷手里,恐怕后面的事情更加难办。
她便拱手以礼,笑道:“在下素闻扬州师爷才高八斗,今日可否见识一番?”
那师爷因听眼前公子赞他“才高八斗”的话,心里的虚荣心像干柴遇着了烈火,一下子就被点燃起来了,于是他也便来了兴致,扬眉吐气道:“尽管出题便是。”
黛玉便问:“《论语》‘八佾第三’卷中第十八句怎么说的?”
那师爷对《论语》是耳熟能详,只想着破题,便喜道:“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此话一出,这师爷的头又与他后面官老爷手里的扇柄来了次亲密接触。
黛玉随即笑道:“师爷果然才艺不凡。刚刚师爷亲口说了‘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的话,也正好回答了我刚刚不能拜见县太爷的原因。我想县老爷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文圣人孔夫子作对,偏我要这个不起眼的君安客栈的掌柜做个‘事君尽礼’的谄媚之人吧?”
那师爷听了,便是气得直咬牙牙,一时却也没有什么话来挡回去的。
白袍子的县官又是将扇柄敲了敲青胡须师爷的头,走到前边,略一拱手,依然是抑扬顿挫地说道:“本官看你虽是个客栈的掌柜,却是这般的铁齿铜牙,你可知道我扬州县衙前不久不见了两位差官,当日他二人有来你这君安客栈巡逻,如今他二人不知何往,你可要如何交待?”
黛玉听了,便佯装不知,问道:“真是天大的笑话,你县府衙门少了干活的伙计,今天却找到与你县府衙门井水不犯河水的客栈寻人来了,不知是依的什么道理?”
那师爷听了,便笑道:“县衙差官做事向来秉公守法,他二人当日奉命只到你君安客栈巡逻,却偏偏七天都未回府报道,又派人到他二人家中询问,亦不曾见他二人回家。要不是你们君安客栈里谋害了人,莫非他二人插翅飞天了不成?”
还未等黛玉说话,那后面站在左侧的厨子夏西施失口骂道:“狗日的师爷,竟然拐着弯儿骂我们开黑店呢?”
“哪里来的泼……”那青胡须师爷话到嘴边硬是又把话给咽了回去,只见那骂他的厨子夏西施生得妖艳若花,肤白似玉,一顾倾城,再顾倾国之态,不禁心里生了爱慕之心。可怜这师爷日夜侍奉这扬州县官,如今空有一身才情和那青青胡须,仍是孤身一人。
这青胡须迟疑的片刻,又挨了那县官老爷的一次扇柄的猛击,只听那扬州县官老爷不无生气道:“真是成事不足,办事有余,等回去我必要修理你一番。”
众人见了,心里好笑,却终究未敢笑出声来。
忽然那扬州县官脸色一变,怒道:“师爷所说,并非全无道理。我今日必要查个水落石出,否则绝无罢休的道理!”
只听那扬州县官两个手掌相击,随之在寂寥的君安客栈里响起了被那历朝官员用过无数次并将仍然要用下去的口头禅:“来人啊!”
白袍子的县官的回声还未消亡,潜伏在君官客栈黑暗角落里的士兵忽然潮水一般涌了出来,将黛玉等八人团团围住了。
“你到底安的什么心?”黛玉见了这种架势,心一下子悬了起来,这完全出乎她的意料,虽然她想这县官哪里不对劲,但并没有想到他会来这一手。戏似乎越来越有味道了,林黛玉不知不觉中被推到了这出戏的风口浪尖上了。她现在必须对此抱一颗淡然的心境,她从来都是这样娴静若姣花照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