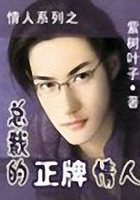1
下一站就是Belleville。
对于叶子来说,Belleville是个陌生之地。但是她却如来过千百次一样,熟悉它。早听母亲说过,那里是巴黎一个华人聚居地,中国人叫它美丽城。
地铁哐当哐当地行驶在昏暗的隧道里,叶子望向窗外,车窗玻璃映着她自己的脸,除此之外,她什么也看不见。她定定地看着车窗上的自己,一张焦虑、憔悴,明显睡眠不足的脸。自己这个样子,母亲见了,肯定会心疼!她想着,抬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把嘴角向上翘了翘,笑容也许能掩盖自己的倦容……
地铁要进站,明亮的灯光照亮了车外的一切,瞬间淹没了她的脸,也淹没了她那个还未来得及浮现的笑容。Belleville,叶子一眼就看到站台白瓷墙上蓝色的站名,心跳得厉害,手猛然攥紧,手心里的纸块生生地刺进她的肉里,她却浑然不觉。
那纸块,确切地说是个信封,母亲写给她的信的信封。信封上有个地址,她就是倒着背也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可她仍不放心,怕记错;来时把信封折成四四方方一小块,藏在手心,一路就这样紧紧地握着。
还未等地铁停稳,她便蹭地一下站起来。由于力度太大,把坐在旁边一法国老太太吓了一跳,老太太不高兴地嘟哝着白了她一眼。可她什么也顾不上,拼命地向门边挤去。下了地铁,她跟着人流涌出去。
天阴沉沉,风呼呼地刮来细雨。她从背后竖起外套上的帽子戴在头上。心想,母亲的话一点不错,巴黎十一月的天说风就是雨。钻出地面,长长地舒了口气——这就是Belleville,美丽城啊!
星期天,巴黎各大商场超市都关门休息,大街上往往比平时冷清。而美丽城却是行人如鲫,车水马龙,一派喧嚣繁华、拥挤嘈杂的景象。大道两旁鳞次栉比、挂着中文招牌的店铺餐馆,都按照中国人的习惯照常营业,热火朝天地迎来送往。
一股浓郁的玉米香气扑面而来,叶子深深地吸了一口。这好闻的香味是从地铁口旁一个烤玉米摊飘来的。一个脸色黝黑的印度男人,刚才还双手举着玉米,冲着来往的行人不停地吆喝着“Pas cher pas cher,un euro!(不贵不贵,一欧元)”。这时却手忙脚乱地抢救雨中的玉米,显然这突来雨打乱了他的阵脚,也搅黄了他的生意。他不时看看天,耸着肩不满地嘟哝着。
看来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即便是一场不大的雨,人类也总是束手无策,如此无奈。
叶子瞟了那印度男人一眼,心里虽对他抱有无限同情,脚却没有停下来。她匆匆地走着,突然一只酒瓶滚过来,一旦一脚踩上去,绝对会摔倒。叶子急忙收住脚,她看见路旁栏杆下倚躺着一个流浪汉,正把一个个空酒瓶滚向人行道。
他裹着一身看不出什么颜色,脏兮兮的厚衣服,脸却是出奇的红,稀疏的白发被雨水打湿,乱糟糟地贴在头皮上。空酒瓶四散向路中央滚去,不时引起路人的惊呼。可他完全无视周遭的这一切,红脸似笑非笑,一只手抱着酒瓶,另一只手忙不迭地滚着空酒瓶。雨无声地打在他的身上,他好像没有感觉似的,仍旧专注着自己的游戏。直到身旁的空酒瓶滚完了,他才慢腾腾举起那只老得不能再老的手,擦了一把脸,然后一仰脖子,抱酒瓶猛灌……
叶子有些恍惚,感觉自己落入了一个什么都不真实存在的世界。
这是美丽城,巴黎的美丽城,母亲住过的地方。
街拐角处有个书报亭,一群中国人在那里大声吵闹。叶子顿时像见到亲人一般,拔腿跑去,到了近旁好不容易找了个空当挤进人群,问:“对不起,请问去玛格日特路怎么走?”
没有人理会她,所有的人都被一个站在台阶上的大胡子吸引。大胡子还在扯着嗓子高呼:“还差三个!”
底下的人顿时像发了疯,挥着手臂一边高喊“我我我”,一边向前涌去。叶子被挤得东倒西歪,好不容易才钻出来。站在一旁喘气,一个推着婴儿车的中年女人走过来对她说:“大妹子,你是抢不过他们的,别费劲了!”
“抢?抢什么?”
“工作呗。”中年妇女撇了撇嘴。
“工作?”
叶子愕然,看着那群你推我搡的男人女人们,猛然想起母亲说过的偷渡客。难道就是这些人?母亲说,在巴黎,没有身份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他们的工作越来越难找。正因为僧多粥少,一些能够找到工作的中国人,便高价贩卖工作,从中渔利。叶子望着大胡子,望着那些涌动在他周围的男男女女们,不禁呆了。她仿佛在群情激愤的人堆里看到了瘦弱的母亲……叶子的心猛地像被人捏了一下,痛得几乎要晕过去。
推婴儿车的女人往叶子身边凑了凑,忽然压低声音很神秘地说:“姑娘,我看你也挺不容易的,我手头正好有一个保姆工,东家挺大方的,给的工钱很高,可以介绍你去做。至于介绍费嘛,我只收你半个月的工钱,比那大胡子收得少多了。你也看见了,现在工作不好找,一有工作大家都来抢……”
叶子缓缓摇了摇头,说:“我,我不是来找工作的,我只是想问个路!”
“唉,你这孩子真够傻的,问路随便找个人问不就成了,还跑这儿来瞎挤。”
“我刚来巴黎,都不熟。这不,一见到咱们中国人就觉得特别亲,所以就……”
“中国人中国人!哼,这年头巴黎的中国人太多了,都不亲啦!没遇上个中国人把你卖了就算万幸!唉,时间长了,你就知道啰——”这时推车里的孩子醒了,哇哇乱哭,一伸腿把毯子踢到地上。女人叹了口气,俯身去哄孩子。
叶子讪讪地在她身后站着,不知如何是好。好不容易等她弄好了孩子,叶子赔笑道:“阿姨,你知道玛格日特路往哪个方向走吗?”
“哟,这我可还真不知道。别看我已经在这儿住了好些年,可这些法国路名我根本记不住!姑娘,你别急,我帮你找个人问问。”她说着转身挤在人堆里拉出个小伙子,对叶子说:“这是我儿子,问他吧!”
叶子正要与他打招呼,没想到他不耐烦地冲着女人嚷道:“妈,你干嘛呢,我正跟大胡子谈价呢!”
“大胡子太黑心,要收两个月的工钱,有什么好谈的。”
“有什么办法,现在只有他手中有活儿。妈,啥事,快点说!”
“这姑娘问路,啥路来着?”
“玛格日特路。”叶子把信封展开给他看。
他没看,伸手向前一指:“你顺着这条美丽城大道一直向上走,到第三个路口向左拐就是。”话音未落,人一溜烟便跑了。女人推着婴儿车跟在他身后喊:“阿强,千万别去餐馆,现在餐馆查得紧……”
母子俩一前一后跑开,谁也没有理会叶子的道谢。叶子呆呆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心里蓦然生出一种羡慕。
2
美丽城大道是一条依着地势而建的大道,越往上走越吃力。叶子怕自己走错路,一路仔细搜寻着。终于来到第三个路口。
左边是一条高低不平的青石路。一幢面目有些狰狞的旧楼,墙上有五颜六色古怪图案。这也许就是老外有名的涂鸦艺术,叶子看不懂。旧楼墙壁上有个白色指示牌,指示牌上写着:“Rue marguerite”,这就是她要找的玛格日特路。
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青石板被雨水冲刷后,干净冷幽。
玛格日特路远离了美丽城大道,也远离了美丽城大道的热闹。长长的一条路,只有零星两三家店面,显得破败不堪。一家无人光顾的中餐外卖店旁就是她要找的21号。黄色木门半掩着,叶子迟疑了一下,推门进去。一推开门,一个尖尖女人的声音便冲进耳里。
“……华姐你命真好,这么快就可以离开这鬼地方!”
“羡慕吧!羡慕你就加把劲,赶紧找个法国男人嫁了呀……”另一个女人咯咯地笑着。
“我是想找呀,可两眼一抹黑,啥法国男人也不认识。”
“那就在大街上,闭着眼睛撞,撞上谁就是谁!”
也许是在异国他乡,耳朵对中国话更敏感。楼上女人们的调笑声一字不漏地冲进叶子耳朵里。既然这里住着中国人,那就说明她没有找错地方。她有一种莫名的狂喜。
“喂,华姐,你那法国老公怎么还不来啊?你看看你,东西堆得到处都是,我的脚都没地方站了……”
楼道里黑乎乎的,那些声音近在耳畔,叶子却寻不到人。她在昏暗的走道里摸索了半天,才找到上楼的门。但门推不开。正着急,猛然发现右手边墙脚有个小按钮,她伸手迟疑地按了一下,只听轻轻地一声“嚓”门就开了,楼梯蓦然出现。
母亲住在二楼二号房。
法国人计算楼层的习惯与中国人不同,他们把一楼称为零层。二楼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三楼了。叶子脱掉帽子,像探密似的,心跳如撞鹿,上了楼,那些说话声也更加清晰。
“……华姐,嫁了法国人,那你就有身份了?”
“没有,听说现在法国政策又变了,要三年以后才能换到十年居留,现在我只能拿到临时身份。”
“管它临时还是正式,反正你终于脱离苦海,再也不用像我们一样担惊受怕啦!”一个尖嗓子女人高声说:“唉,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命苦,怎么就没个法国男人看上我呢?”
“你呀,就是没长一张像华姐那样的脸,咯咯咯……”这个女人笑起来像鸡打鸣。
“看来我得去整整容,整得跟咱华姐一模一样,连皱纹都一样……”尖嗓子又叫起来。
“好了,你们俩就别取笑老姐了。”那个叫华姐的女人,声音有些低沉,却很好听。
“取笑?”尖嗓子嗓音更尖了,“华姐,我们姐俩羡慕都来不及,哪敢取笑您老人家呀。不过华姐,你进天堂了,也得想着点我们这些还在地狱的姐妹们,等你嫁过去,你可得把你法国老公的哥哥弟弟,表哥表弟啥的,介绍介绍给我们呀,好歹看在我们一起搭过铺的情分上!”
“没有哥哥弟弟,公公爹爹也行啊!”
“哈哈哈……”
叶子就在一屋子人都在哈哈大笑时,出现在二号门门口。门是开着的,一间仅有十平方米的房间,里面紧紧排放着三张高低双层床,所有的空间都堆满了衣物用品。也许是因为有人要搬家,房间里显得更加拥挤零乱,令人窒息。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母亲会住在这种地方?在母亲的信中,她住的地方客厅外是个大花园。这里哪有什么花园,哪有什么随风而入的花香?有的是一种人物饭菜混合的湿漉漉的怪味。
“喂,你找谁?”
睡在门边上铺的女人欠起身问。听到她的声音,收拾东西的两个女人也一起回头望着叶子。
“对不起,对不起,我找刘春!”叶子蓦地慌了神。
“刘春?你找错了,我们这里没有这个人!”回答叶子的是那个尖嗓子。
得到这种回答,叶子莫名其妙松了口气。说实话,她的确不愿意看到母亲住在这样的屋子里。但是,她清楚记得,在母亲写给她的信中,留下这个地址的就五六封,这说明她确实曾住在这里。而且至少住了五六个月。
“麻烦你们再想想,她以前就住在这里。你们看,这是她写的信,地址就是在这儿?”
尖嗓子拿过信封看了看,笑道:“地址没错,可你看这邮戳上的时间,都过去快两年了。太久了,我们这地方,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谁还会在这种地方长住呀,肯定是搬走了。”
“是呀,说不定也像咱们华姐,找个法国男人嫁了享福去了!咯咯咯,我们这儿有姿色的女人很吃香哟……”上铺的女人鸡打鸣似的笑起来。
“你积点口德吧……”收拾行李的女人扔下手中衣服,拍了一下上铺的女人,回头对叶子说:“一定是搬走了,你再去别的地方找找吧!”
叶子从声音判断出她就是华姐,她比另外两个女人要老,态度也和善许多。叶子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般拉住她:“大姐,求求你再想想,或许这里还有别人认识她?”
“她是你什么人,你这么着急找她?”她问。
“她,是我妈妈……”眼泪在叶子眼眶里打转,她尽量忍着不让它掉下来。“……我我已经快两年没她的消息……”她的声音小了,但屋里的人全听清了。一时间没有人说话。
华姐她迟疑了一下,对叶子说我帮你问问。她掏出手机一连打了好几个电话,最后摇了摇头:“住这儿其他人也都说不认识。”
不认识,就等于没有线索,我该怎么办呢?叶子心一急,眼前一黑,身子晃了几下——
“喂,你怎么啦?”华姐一把扶住她,“别急,你可以到别的中国人多的地方去问问。”
话虽这么说,但连华姐自己都知道她说的这句话毫无意义。住在这种地方的人,都是些萍水相逢的陌生人,谁也不知道谁的底细。当然各自为了生计,也顾不上去了解别人的底细,当然,也没有那个必要,住在这里的人经历目的都大同小异。即便有幸在一起住上一年半载的,但分开时也不过只知道彼此张三李四的代号。她们匆匆地来,匆匆地去,残存在这里的点滴痕迹即刻就会被后继者代替。甚至连这间小屋也不知道这里来来往往有过多少过客。
不知过了多久,楼下传来一阵尖锐的汽车喇叭声。上铺女人抬头向窗外看了看,说:“华姐,你法国男人来了。”
华姐一听,冲到窗边,挥着手叫道:“Mon cheri,je suis là(亲爱的,我在这里)——”
尖嗓子拍拍上铺女人,女人会意,恶作剧地叫起来:“Mon cheri,je suis là。”话音刚落,两人便爆笑起来。
面对两人的调笑,华姐并没有恼,她笑道:“两烂嘴的,还不帮你老姐搬东西。”
上铺女人跳下,在地上一堆东西里翻了翻,嚷道:“华姐,你这些破烂还要干什么呢?这跟你马上要去住的别墅可真的不相配,我看还是扔了吧。”
“不能扔不能扔,我们华姐虽没那法国人有钱,好歹也要带点嫁妆过去!是吧?华姐!”尖嗓子抢着去提箱子,“我送你,华姐。”
两人抬着箱子往外走。
“哎,等等我!”上铺女人趿着鞋,抓起个塑料袋追了出去。
在面对喜事和伤心事的时候,人们往往更喜欢选择喜事。在巴黎,哪个中国人没有伤心事。更何况这些没有身份的女人呢。骨肉分离,甚至生死离别,时时都发生在她们周围。也许她们看得太多,也受够了,她们的同情心已经麻木——如果她们不在困苦的生活中发现点喜事,看到点希望,那她们也许真的活不下去了——
叶子的脑子乱极了,她知道自己不能就如此脆弱,她要站起来,去继续寻找母亲。她晃晃悠悠地站起来,走到门边。
妈妈搬走了,她搬到哪里去了呢?一定是那个客厅对着花园的房子。母亲最爱的就是花。想到这里,她有些释然。就在这时,她听见上铺女人和尖嗓子上楼的声音。再问问她们,也许还能打听到点什么。这样一想,她便站住了。
“我还以为华姐找了个法国老头呢,没想到那男人还挺年轻还挺帅的。”
“呵呵,你可别小瞧了华姐,我真羡慕她,她可真给我们中国女人长脸。听说那法国帅哥迷她迷得昏头转向,华姐说东他不会向西。”
“真不可思议,那男的脑袋叫驴踢了吧!你说华姐有啥好呀,一个四十岁的女人,离过婚还有个十几岁的拖油瓶,长得嘛又不好看,一脸老相,又没身份。那帅哥怎么就看上她了呢?”
“呵呵,这就是爱情,伟大的爱情。”
“见鬼去吧,你还真相信爱情呀,幼稚不幼稚呀!”
“不管怎么说,华姐是脱离苦海啰!有身份,能正儿八经打工赚钱啦。可我们还得熬呀!”
“是呀,没身份打黑工真他妈不是人受的罪,不仅受老板克扣,还担心警察抓!唉,我哪天也能走狗屎运,撞上个法国男人愿意娶我,哪怕是个老头也行啊!”
“得得得,就你那几句四不像的法语,也想跟法国人交流,别做梦了!”
“那我就不可以找个会中文的法国男人呀。”
“哈哈,做梦吧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