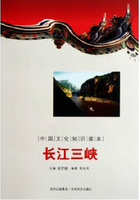钟玉行正背对大门,于榻上运气疗伤,他的上半身裸露着,肩背上满是细密汗珠,冰魄寒毒入骨太深,他驱毒竟有些力不从心。
朱红镂空雕花木门洞开,晚风携凉意入室。男子双手划环相合调息,如月白华在手掌间氤氲。
忆薇看着男子光洁赤/裸的背部,站在门口愣了两秒钟,“啊”地叫出声来,脸上火烧似的发烫,双手紧紧捂住了眼睛。
钟玉行本在聚力疗伤,被她这一声惊叫弄得半途而废,剑眉紧蹙着扭过身,只见面前瘦弱的青衫“男子”双手覆眸,叫道,“你···你怎么不穿衣服。”
钟玉行浅灰的瞳子里闪出一道莫名的光华,看着紧捂双眼的忆薇有气无力道,“大家都是男人,你如此大惊小怪作甚?莫不是你喜欢男人?”
忆薇这才反应过来自己还是男装,故意埋下头将玉手慢慢挪了下来,看着足尖支支吾吾道,“我才···才不是断袖。”
他低声问,“你来叫我泡药浴?”
“嗯,药汤已经备好了,就在西厢,你···你自己去,我···你饿了吧,我去拿些糕点。”
说着,忆薇已经颠颠地跑到了厨房,将门“砰”地关上,边搓着自己滚烫的脸,边暗自恼恨自己刚才的紧张与大惊失色。
她在心里默默告诫道,沈忆薇,你是男人,你现在是男人。
钟玉行看着忆薇消失在回廊尽头的身影,冷峻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些许笑意,这青衫小哥还真有意思,言语行动总跟个姑娘似的。
他唇角噙笑,摇头披了衣服,顾自向西厢行去。
整个西厢房内都笼罩着腾腾白雾,他将衣衫抛挂在碧茜纱屏风上,飞身入浴桶,依旧背门而坐,头倚在桶沿上,将星目微阖。
他眉峰舒展,鼻梁高挺,眼睫如墨色蝶翼随眼睑轻覆,鬼斧神工雕琢的脸庞,在这似真似幻的白雾中,更添了一番仙意。
忆薇端着盛满茶水和糕点的木托盘进门,绕过碧茜纱屏风,将托盘置在浴桶旁红木桌上,她端了碗茶递到钟玉行面前,边说道,“钟楼主啊···”
声音却随发出一半的“啊”字戛然而止,她杏眸圆睁,嘴唇微张,如水秋瞳里映着男子的面容。
钟玉行睁开眼,就看到她一副见了鬼一样的惊讶表情。
两人对视半晌,钟玉行从她木木的手中拿过茶,心里生了无数道黑线,边喝边鄙夷道,“看你这副样子,你确定你无断袖之癖?”
忆薇并不接他的话,双手垂了下来,痴痴道,“青哥···”
“嗯?”钟玉行看着眼前的男子,浅灰的眸子里全是疑惑。
“是你吗?”忆薇问道。
“你说什么?”他眼睑微垂,似在思考什么。
忆薇回过神来,眸子带着急切的神彩,异常郑重虔诚地看着钟玉行,“南綦绿洲、玉笛、吹雪、笑语···你还记得吗?”
南綦是嵌在漠北荒芜之地的一颗绿明珠,关内鲜有人去过,钟玉行也自然不知。
他听着她莫名其妙的追问,又抬眸看了她一眼,接着继续闭目养起神来。
“六年之约,普生寺,只剩三天就该见面了。”忆薇继续说道。
钟玉行无动于衷,那样子像是睡着了一般。
她看着他如水轻淡的神情,心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细碎裂开,有血液渗出。
他这样的不悲不喜,这样的清冷淡然。
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见面,他对此一点反应也没有。
她知道,他定是不记得她了。
与她有六年之约的人,居然不记得她了。
忆薇突然想起什么来,“钟楼主向来不以真面示人,对吗?”
“确实,”钟玉行冷冷开口,顿了一下,又继续道,“不过今日恰巧被你看到了真容。”
原来真的是青哥,那样神似形似的面容,那样如出一辙的眉眼,那样相同的润泽的唇。
真的是他,可是他忘记她了。
钟玉行也不知道自己为何对她这样坦白,或许是她救了他,也或许是因为她碎嘴子而又毫无心机的表现,面前的清瘦男子总让他情不自禁地说真话。
忆薇唇畔闪过一丝苦涩笑意,他忘了她,可是她的心里还深深烙着他呀,笑语的青哥。
她似是下定决心一般,佯装恍然道,“噢!我认错人了,我要找的那个人应该已过不惑之年了,你还这样年轻。”
她想,既然他不记得她了,那她能一直以男子之容陪在他身边也好,只要能在他身边,就好。
她又深深看了他一眼,正准备转身离开,钟玉行幽幽启唇道,“小哥姓甚名谁?”
她已经知道了他的名字,公平起见,也该告诉他自己的名字。
只是她没有料到他会主动问出来,怔忡半刻才说,“小弟沈氏忆青。”
“沈忆青。”钟玉行听着她渐行渐远的脚步声,喃喃道。
忆薇在门口停住,“半个时辰后,我来给你运气疗伤。”
话音未落,她早已迈门而出,月如钩挂在泛了鱼肚白的天际,这个时候的天气异常清冷。
忆薇拢了拢衣襟,指尖不自觉抚上腰间的玉笛。
他曾对她说过,待你学成吹笛,便来寅城找我。
如今,她已经能将笛曲吹得出神入化,如歌似泣,她已经遵守诺言来到了寅城,她甚至已经见到他了。
可是,面对的却是这样的他,他又回到初见她时,遥不可及的陌生里,这让她情何以堪?
青哥,既然你不再记得我,那么从此以后,我还是不是你的笑语呢?
忆薇回到房间,将腰间玉笛解下,挂在僻静的角落里。
往事蒙尘,执念该化作另一种方式,存在于她的心里。
钟玉行,我要留在你的身边,做你的兄弟沈忆青。
第一束晨辉微光照进窗格子,落在忆薇清澈的眸子里,照的她眼中仿佛含了泪花一般,闪闪烁烁。
这两年来,她每每夜晚之时,总会将房门紧闭,自己一个人偷偷地钻研武功,因此昨日熬了一夜,也并不觉得累,只有心里稍觉疲乏。
时间已过了半个时辰,她起身朝西厢房去。
院中黄花堆积,如火的红枫树如华盖一般,层叠如红云的枝叶在清晨的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