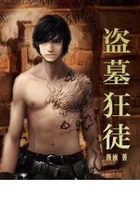江南。
郊外小镇。
鹅毛大雪铺天盖地的席卷了一天一夜尚未全部消停,却舍得小了许多。
一架灵车正稳妥妥的于夜色中诡谲地飘着,「嘀铃铃」的响声断断续续,被那偶尔刮过的烈风一席裹,反而更添几分凄凉的呜咽。
一袭红衣的女子在这暗夜白雪里更显单薄,她单手拿着九节墨色的鞭子,一动也不动的站在林间,她的头发已然全被白雪覆盖了,看样子,是已经站在那里好久好久了。
灵车仍旧诡异的漂浮着,没有急一步也没有缓一步,慢慢的朝着那女子去了。
尔后在十丈远左右,停了。
一道稚嫩的童声自厚重的车帘后响起,孩童尚小的年纪声音糯糯甜甜,分辨不出男女:
“请问姑娘何事?”
“三件命案,五个死婴,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们,不能在修罗门的地界里犯事?”话音还未落,就听车帘内响起一声笑,声如温玉,却偏生含了那么一两丝刻薄冷清,倒是个男子的动静:“怎么?南方不是由江湖四大世家公孙家接管的么,何时……又多出个修罗门?”
似乎是卡着他尾音落地,灵车旁倏忽响起两声不似人能发出来的鬼叫声。
那姑娘眼力劲儿极好,别看他们叫了一个修罗门的名字,她可是不信神魔不拜鬼神的,主人给她命令,她就杀。刚从远处瞅着她就不信那辆车会这么飘,待得不用太近,她也看出来了,那其实是两条巨大的蛇……大概是蛇吧,只不过刚被她抽断的那两条蛇的对半身子一落到地,又开始诡异的扭曲起来,不一会儿,就已然出现六条了。
而且,那六条蛇显然脾气都不太好,此刻也不管要顾着灵车了,“轰隆隆”的一下子都冲着那姑娘去了,黑色棺材一样质地的灵车带着一阵铃铛猛晃的声响,“咣当”一声落了地。
前方雪地里翻滚起滔天白沙,红衣女子不敢再妄然拿她手里上好的利器对敌,却又不知掏出火折子来在这风雪天里能燃多久,愈显招架吃力的时候,几声轻微的咳嗽却从不远不近处传来,她只见身前闪过一道白色的影子,尔后刚才围攻她的那六条怪物全部都消散成碎渣渣了,风一吹就跟白沙似的远去了。
她是没看清楚,可蹲在灵车旁一直关注战局的小孩可看的一清二楚。
他正想着呢,万一那个姐姐招架不住了,就快些把泥鳅叫回来吧,别伤着人命。这下可好,他刚才就见着一个白衣服的男子从远处像个真正的“鬼”一样飘了过来,还从怀里掏出一方素白的帕子来,捂住了口鼻,於是那咳嗽声就被压抑的极低极低了,再然后就是这个白衣鬼也不知从哪儿又掏出了把同样雪白的扇子来,“嗖”的一下出现在红衣服姐姐身边,接着一面往前继续诡异的飘着,一面左右开弓像是扇嘴巴子似的扇了那泥鳅几下,然后泥鳅就挂了。
小孩现在眼眶就红了,那泥鳅是先生好不容易才养活的呢,小时候就跟泥鳅似的,慢慢才变作这么大的,都不知养多久了!刚才早一点喊停就好了!
正在这儿后悔的时候,那雪白衣衫的翩翩公子也终于停止了咳嗽,素白的帕子上是一小滩血迹,红衣女子有些着急的向前,被他轻微抬手的动作给止住了,只好呆在原地听令。
“在下修罗门二当家,何人在此放肆?”
灵车里久久没有动静,蹲在灵车门口的小孩悄悄掀个帘子边儿,想看看是不是先生又睡着了呀,只是手指还没触到厚实的门帘,就听见灵车里传来一阵惊天动地的笑声,连他都被吓到了。
他跟了先生好多年了,头一遭听见他这种笑,特别特别开心的那种笑。
素白衣衫的男子那好看的眉头都快揪到一起去了,这人难不成是个疯子吗?
“沉瑟,”含着笑意的温和嗓音从厚厚的车帘内传出来,“我说……几年不见,你怎么比我这个病的快入土的还要严重?”
名唤“沉瑟”的男子一愣,随即眉头彻彻底底的拧在了一起,淡定道:“我这是病的快死了不假,你那是作的快死了。”
五年前见着他还是人模狗样温和有礼至少没丧心病狂的喜欢坐在棺材里故弄玄虚,这会儿真是延续了羅迦的毛病,藏头露尾顶不是东西端的是一个模子顺出来的。
这除了是在作死还能有甚么别的解释?
腹诽完毕,冲一旁的女子轻声道,“十七,我们走了。”
“喂!”车帘内传来重重的不满,“我身上可是有三件命案五个死婴啊!”
“大善人,”沉瑟忍无可忍的回头,“你不会闲着没事从南疆跑到中原来就是为了讲笑话与我听的吧?”
“当然不是,我是来抢亲的。”
沉瑟一愣,一个“化鸿”使出来就来到了灵车前,掀开了帘子,仔仔细细看了一眼确实是他认识的那个人不假,这才反问,“你刚说甚么?”
“顺道来给你治病的。”
“甚么?”
“守葬阵有法子破了。诡域找着了。羅迦死了。阵法机关甚么的也不惧它了,我都有法子了。”
“於是?”
“正渊盟退隐江湖了,四大世家也不必存在了。中原武林要死的人也开始多了。”
“所以?”
“所以我来拯救苍生。”
沉瑟憋了半天的严肃脸终于破功,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十七也愣了,她很多年很多年没曾见过她家主人这么个笑法了。
沉瑟惊天动地的笑还没持续太久,就有一只惨白的手伸了出来,骨节分明但确实是有肉罩着的,但在这暗夜里,不知怎么,在十七眼里就觉着是一只手骨伸出来捂住了主人的嘴巴。
“沉兄莫要再笑了,隔着这么厚一层帘子我都闻得见你笑崩了伤口重新溢出来的鲜血味儿。”
“挤一碗给你喝汤好不好?”
沉瑟今晚真的挺开心的,一是没想到还真能与这个人再次相逢,二是……
“沉!瑟!”
灵车里不出意外的传来那略显抓狂的声音。
“修罗门地处偏远,僻静小地,你去了晚上睡觉要是遇见老鼠横身爬,或者蜈蚣耳朵钻之类的事,都莫要惊慌,知道你喜干净,那么就喊人捉住便好了,倒时候交给我,我亲自下厨与你做下酒菜吃。”
“沉瑟,你还想不想把病治好了?”
“往我的药里放巴豆这种不入流的事你又不是没对我做过。”像是刚才听到那人说他要拯救苍生后开始的猛笑真个扯痛了伤口,沉瑟索性斜坐在车辕上,对十七淡淡道,“你先回修罗门一趟吧,叫几个有力气的人过来帮忙把这口棺材抬上去。”
眼看着女子远去了,沉瑟突然沉下了一张脸,恢复了惯有的冷漠表情:
“先说好了,动她不行。”
“那你便去死吧。”
轻轻笑声又从门口那个带伤男子嘴里发出,“你刚才提到的那些个事,我都不想管了,只要她在,我的病也解决了,我就走。”
“是,只要她在,你就死定了。”帘子再次掀开了些,那惨白的手指一根一根的抓紧了沉瑟的素白衣衫,狠命的将他往里扯了扯,沉瑟半推半就的爬了进去,顿觉那股子暖意真是活生生能把人热出汗来,可对面那人仍旧裹得厚厚的,怀里还抱着个暖炉,瑟缩着,惨白着一张脸,脚边是一盏暗红色的灯笼。
本就逼侧狭小的空间内,那股子清神的香气便显得愈发明显了。
沉瑟已经不年轻了,也算阅人无数,他见过很多漂亮的人,男的女的都有,他们披头散发神情慵懒的时候也是各有各的风情,但远不如眼前这位来的更风情万种,却偏偏让人不敢生出一丝亵渎的情愫来,这人好似生就一幅慈眉善目的娃娃脸,好似也就永远年轻着,明明是个黄土埋到脖子上的人,却很爱笑,虽然那笑容半是怜悯半是冷清……他突然又想到,有人曾对他说过,“这个人每次笑起来的时候,我都有种想要给他下跪的冲动。”
只可惜那个人已经死了,三件命案中的死者之一。
对方显然这时候也发现了沉瑟脸上的表情,有些不悦的将刚才小憩时解下来的发冠重新束起,他当然知道沉瑟真正在看的是甚么,於是便打算说点原先江南城里的案件扯开话题,却见沉瑟不怕死道:“其实你和她真的很像……你不必那么讨厌他,就算是赌气,去了南疆那么多年也该……”
“我把你眼珠子挖出来下酒喝,再把蛊虫灌进你体内,把你嘴巴缝起来当作人蛊养好不好?”
“不好,我看十分的不好。我沉瑟如今就算是病入膏肓,在这里将你就地正法也不是件太难的事情。”
话未说完就见帘子被掀开了,原先待在门口的孩童不知是气的还是冻的,红彤彤一张小脸,有些不悦的看着沉瑟。
对方将怀里原先抱着的暖炉塞进了他手里:
“你也进来吧,外面风大。沉兄是在同我开玩笑呢。”
小孩固执的摇了摇头,把暖炉重新塞回他家先生怀里,又仔仔细细帮他把头冠弄好了,衣领也紧了紧,他记得的,先生最讨厌散着头发,但无论怎样,他都觉得他家先生顶好看。
办完这些事,小孩就打算退了出去,只是还未等退,就突然一头栽到了他家先生身上。
沉瑟平静的看着对方将那小孩放平躺到身侧,把暖炉放在了他旁边,尔后亮着一双眼,依旧笑的悲天悯人:
“沉瑟,我这次回来,原本真的只是打算抢亲的。”说着,一面抬手敲了敲后面的暗格。
那声音沉闷,不像是中空的,就算原本是中空的,现在也已经塞进去甚么东西了,或者,甚么人。
沉瑟突然出手如电的抓住了对方的手腕,他病了这么多年,真应了那句古话,得的病多了反而也能自治了些,半吊子医术虽然没有对方那么精通,可还是有的。
“别探脉,我受不起了。你摸摸就成。”语毕又开始吃吃的笑起来。
沉瑟的脸色愈发难看了。
沉公子严肃起来那是很恐怖的一件事,他当年名震江湖就是靠着黑了一张俊俏的脸,拿着那把扇子连杀了鬼头九、鸠鹤丘、满碟跑这三个臭名昭著的恶人,最后一个还是被他活生生吓死的。
可同样,沈公子也是恶人,他是修罗门的人。
修罗门办事向来亦正亦邪,杀人与否决战与否,都是凭着自己喜好来的,好人也杀,坏人也杀。
但他出名却确确实实是因为杀了那三个正渊盟都无法彻底杀掉的恶人。
江湖人也同样知道,这位爷随便往哪个人堆一放,都是个世家贵公子的模样,甚至还有些病弱的感觉,若不是真听他冷冷淡淡的报出名姓来,大抵都是拿他当个不会武功的清高世家子弟看待的。
可眼前这人不一样,他知道沉瑟的武器其实是两把扇子,可以展开了对到一起,就成了个轮刺似的,千里取人首级都是眨眼闭眼的事,同样,他也知道沉瑟真的沉下脸来了,就是真的很生气很生气了。
能让他动气的事太少,因为沉瑟不喜欢多管事,为人也冷淡。但他上头却压了个修罗门的老大,也是他的师姐,所以他有时候就算不想管事也得管事,要不然今天也见不着他了。
内心默默数了七个数,觉得沉瑟现在已经把脾气压下去了,对方这才又继续嬉皮笑脸道:
“公孙家尚且不敢出面管的事,你修罗门好生大的面子竟要来插手。”
“你得罪谁了?”
“三件命案和五个死婴的凶手已经让我给解决了,那个幕后黑手显然近些时日也不敢有太大动静。但这几件事还劳烦你帮忙压一下,等我缓过来了,再细细盘算日后事。我可不是个做亏本生意的人,他们无缘无故往我头上扣了这么大一个屎盆子,我定然要还回去一座山的量。”
沉瑟收回手,那俊朗的侧脸在暗红的灯笼下映衬着阴晴不定,自己默数了七个数打算忽略他不回答自己言语的态度,这才抬起一双深邃的眼睛,盯了对方半天,缓缓吐出一句:
“你这是抢的**?”
“去你大爷的,你他娘才抢**呢。”
“是,她是活着的,死了的是你。”
“沉公子,你该吃药了,这些年没见,你不止眼睛和脑子不好,连人话都不会讲了。”
沉瑟摇了摇头,有些疲倦的靠在车璧上,看了看面前那个仍笑的开心的家伙,看了半天也不由得挤出抹苦笑,尔后轻轻抬手反叩了叩车璧,轻声道:“有难处可以跟哥哥开口说一下的,哥哥能给你准备口更好的棺材,这个配你……太亏了。”
“别跟我称兄道弟,”对方笑的更开心了,出口的言语却讥讽刻毒,一字一顿道,“你配么?”
“是,我不配,但真正配的那些,也不见得想有你这么个弟弟。”
“我说的自然不是他们。”
沉瑟一愣,就觉脑子里的思路一下子清晰了起来,这人先前提到的那些个事情不说,但冲着後来他说他本来只是抢亲的,抢完了不滚回他的南疆,还在这里呆着,莫非是他还不死心……
“他姓柳。”对方意味深长的看了沉瑟一眼。
沉瑟扶额:“你究竟想怎样?”
“不是我想怎样,”对方神神叨叨的从怀里掏出几个铜板,尔后非常没有规律的往前一撒,接着随意挑出一枚来,向沉瑟那个方位推了一下,这才慢吞吞的装神弄鬼道,“天意如此啊。”
沉瑟连个虚伪的笑容都懒得给他,冷声道:“我认识了羅迦近二十多年,才知道原来他还会卜卦这一说。”
“非也非也,”对方笑嘻嘻的把那几枚铜板收回了怀里,一双眼睛亮过天上辰星,“是我突然发现,我自己有算命天赋的,他可不会教我这个。那天我算出来,他要死了,於是他果真就死了。”
沉瑟原本没打算继续听他鬼扯,掏出那个已经染血的帕子又捂着嘴咳嗽了几声,为了分散痛楚便当做个笑话顺耳溜了几句,这一阵几乎能背过去的咳嗽完了,沉瑟突然惊讶的瞪大眼:
“羅迦……是你杀的?”
对方的脸上又挂起了常有的那副悲天悯人的笑容,眼瞳里满是痴眷的神色,单手向后伸,轻轻触摸着那个暗格,连话语都是罕有的温柔,不似他那老是掺了一半的冷清语调,像是怕吵醒甚么人一样,轻声反问:“你说呢?”
沉瑟思虑了半天,他早已不敢细想这件事了,他不能相信他只是单纯回来抢亲的……就算他真的只是为了抢亲回来的,又出了这么几档子的事让他想要打算留在中原,那确实就只能说是天意如此了……
“你这算是弑师?”
“我还杀了我父亲。”
沉瑟转过头去,就见对方还是那么一副痴眷的神色,一遍遍摸着那个暗格,似是漫不经心又似是认真的语调。
不可能,那个男人要是死了,全江湖说不定都得给他披麻戴孝……心思刚转到这里,沉瑟突然哑声道:
“你的意思是……你杀的是苏景慕?”
“就算我不杀他,他也被云姨折磨的活不长久。”末了轻轻一叹,“这人呐,叫情字缠住了,就变成傻子了。”
“那你现在是甚么?”
“一个疯了的傻子。”
“很好。”
沉瑟的心凉了个透彻,可又隐隐从心底深处泛出一股子疼来,刚想闭眼理一下这些事件的思路,突然又想到甚么似的“唰”一声睁开了眼,拿过那盏暗红色的灯笼仔细闻了闻,语气同心底一样凉:
“这里面到底叫你装了甚么?”
“沉兄何必明知故问。”
“那么……离开灯笼你能活多久?”
“片刻也不成。”
“你真是……太胡闹了。”
“与你相比,好像是。”
沉瑟也懒得再训他了,做都做了,还能怎样?死了的还能复活不成么?
因此只是不轻不重的叹了口气:“所以你这次……会在中原待多久?”
“待到……”对方突然狡猾一笑,“你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