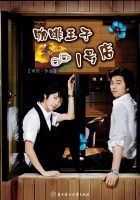到不了的都叫作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
1
因为工作关系去了趟上海,对方知道我是南京人,很体贴地在南京路步行街附近安排了住宿,说是这样我会感觉亲切一点儿。
我说:“你们上海人心思果然细腻。”
对方在电话那头笑着说:“哈哈哈,开玩笑的,主要是我们公司就在步行街附近,个么(这样)来往方便点咯。不用打车什么的,省时又省钱,你说对哇耀一老师?”
我说:“你们上海人果然精打细算。”
对方说:“那我等下把地址和房号发给你,你下车就直接过去好了。打车票留着,回头好一起给你报销。”
我说:“好。”
对高速运转的上海来说,时间比钱更宝贵,因此,很多生意人愿意用钱买时间,就好比对方宁愿让我自己打车到目的地再给我报销也不愿意开车来接我,因为接我的时间,他们可以挣到打车费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钱。
也正是因为对方没有来接我,我才会遇上之后的一些人和事。
2
替我办理入住手续的是一个老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说着典型的上普话(即带着上海口音的普通话。)。
老伯看了看我的身份证,说:“哟,南京来的呀,南京是个好地方呀。”
我刚准备客套两句,老伯又说:“不过比起阿拉(上海话,指“我”“我们”。)上海嘛,总归是要差一些的咯。”
我有些尴尬地笑了笑。
老伯也有些尴尬,说:“哎哟,小伙子,我没有别的意思啊,你不要往心里去哦。”
我笑着点了点头,不料老伯又补充一句:“我这个人嘛,脑筋不会转弯的,就喜欢实话实说,我老伴儿说我这辈子就毁在这张嘴上了,呵呵呵。”
我这会儿已经不知道该做出什么样的表情了,只是预感到老伯至少还有一个包袱没有抖。
果不其然,老伯说:“老伴儿在的时候,我没听她的话,现在她走了,我这个毛病……”老伯说到这里停了一下,苦笑着摇了摇头说:“看来是要带进棺材咯。”
说完他看着我说:“走吧,我带你进去。”
可能是起太早的关系,也可能是被老伯强大的语言魅力所震慑,我的思路混乱得如同隔夜的方便面,一个愚蠢的问题脱口而出:“带我进棺材?”
老伯一下子愣住了,之后大笑起来,说:“哈哈哈,哦唷,看不出来呀小伙子,你这个人蛮幽默的嘛!”
幽默?在这样的老伯面前,我哪敢自认幽默呀!
不知道老伯有没有玩微博,如果玩的话,应该会是个很红的段子手。
3
南京路步行街上有个七重天宾馆很有意思,它其中一面墙上有支硕大的温度计,而我刚巧就在这支硕大的温度计正对面的广场上等客户。
因为之前没有见过面,所以在告知对方我的所在地之后,我又在电话里描述了一下我的装束,黑色货车帽,黑色帽衫,内搭牛仔衬衫,下穿卡其色工装裤,配黑白色新百伦运动鞋。
当我挂上电话时,无意间瞥见左侧有个人正看着我。当看清楚这个人时,我不由得在心中大喊一声:“卧槽!”
这个人戴黑色货车帽,穿黑色帽衫,内搭牛仔衬衫,下穿卡其色休闲裤,配黑白色……哦,仔细看看,那是双白色的耐克,黑色部分都是污垢,占据了鞋的一部分,不难看出,这双鞋已经三四岁高龄了。
这个人走到我面前问:“你刚刚是在说我吗?”听口音像是四川那边的。
我赶紧摇了摇头,说:“不是不是,你误会了,我说我自己呢。”
那人点了点头,转身走到不远处坐下,边上堆放着一些破烂的纸盒和纸板。很明显,这个人是拾荒者。
出于好奇,我继续观察这个人。我总觉得他和一般的拾荒者有点儿不同,至于哪里不同,我说不出来,完全是直觉。
没一会儿,那人从衣服里掏出一盒维他奶,然后举着放在眼前,时不时对着这盒维他奶做一些表情和动作,感觉就像是在自拍一样。
我又仔细观察了一会儿,的确,他就是在自拍,因为他时不时会把拿着维他奶的手收回来,用另一只手的手指在盒子表面划过,估计是在看刚刚拍的照片。
这时不远处来了一对乞讨的母子,母亲推着轮椅,儿子坐在轮椅上,准确地说,是瘫坐在轮椅上,就像霍金那样,头稍稍往后,几乎是靠轮椅背支撑着的。
母亲推着儿子挨个儿乞讨过来,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会给些钱。当他们来到那个拾荒者面前的时候,母亲没有停留,而是直接向我这里走来。
拾荒者显然有些不高兴,他把维他奶放下,然后几步走到那对母子面前,拦住了他们。
那个母亲显然是被吓着了,表情显得有些紧张和尴尬。
拾荒者说:“妹子啊,你打麻将啊,怎么到我这儿了还跳牌?看不起我还是怎么?”
那个母亲赶紧连连摇头:“不是不是,你也挺不容易的。”
轮椅上的儿子也跟着轻微地连连摇头,含混不清地说着些什么,应该同样是辩解的话吧。
拾荒者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钱放到那个儿子的腿上,说:“好好听你妈妈的话啊。长大了要孝顺她,知道不?”
儿子微微点头,含混地说:“知……道。”
那个母亲还想上前说些什么,我起身走到他们面前,也掏出些钱,连同刚刚拾荒者给的钱,一起交到那个母亲手里,说:“阿姨,什么都别说了,走吧。”
那个母亲看着我点了点头,把钱收进口袋后,对着我双手合十作揖表示感谢,然后推着儿子准备离开。
那个儿子抬起一只手指了指我身后,含混地说:“小……心……”
我转头看去,他指的是我的手机。刚刚着急起身,所以随手把手机放在了石凳上。
我微笑着对那个儿子说:“谢谢。”
那个儿子也努力地挤出一个微笑。
挺帅的。
拾荒者双手背在身后,看着那对母子走远,一副深藏功与名的样子。他转身走回原来的位置,抬头看向那支硕大的温度计。
我的手机响起,是客户打来的,我接通电话,对方告知大约十分钟后到达。
我挂上电话的同时,拾荒者拿起了那盒维他奶,放在耳边,说:“喂,对,是我。哦,没什么事,我就是问一下,你们这个温度准的吧?哦,好的好的,谢谢啊。不用不用,我改天过来好了,这里还有个会要开,先挂了啊,好。”
拾荒者说完把维他奶放下,按了一下盒子表面,然后又按了一下,再次放到耳边,说:“喂,妈妈啊,今天晚上要降温啦,你不要出去啦。我赚了很多钱的,明天一早寄给你。哎呀你听话嘛,不要出去啦,太辛苦了。这就对了嘛。先这样啦,人家等着请我吃饭呢。好,妈妈再见啊。”
拾荒者说完把维他奶放进了衣服口袋里,双手重新背在身后,看着那支硕大的温度计,表情有些凝重。
4
第二天吃过早饭,我下楼准备去附近逛逛,刚好遇到来上班的老伯。
说了几句客套话后,老伯说:“我昨天下班看见你在广场上和那个重庆人聊天呀,你心肠倒蛮好的嘛。”
我想了想,老伯应该是说那个拾荒者。于是我问:“那人是重庆的?您认识?”
老伯说:“认识的,我们这里很多人都知道他的。蛮可怜的人,说起来要掉眼泪的。”
我说:“能说给我听听吗?”
老伯说:“好的呀,那我长话短说好了。个宁(这个人)姓黄,以前是工程队的包工头,好像主要是做霓虹灯维护之类的,六七年前来的上海。来了以后嘛,据说做得还不错,接了好几单大生意。不过你也晓得的,做工程什么的,拖欠工程款是最严重的。工程是做了不少,可是款子嘛总也收不全,时间一长,发工资就成问题了。个么工人们嘛就闹情绪了呀。”
这时来了几个新入住的旅客,老伯暂时停下,做了些接待工作,大约十分钟后回到前台继续说。
“喏,屋漏嘛又偏逢连夜雨。这边款子的事还没有解决,那边家里来电话,说是他老母亲生病住院了,急等着用钱。小黄一下子慌了,工程也没心思做了,天天到处讨债,最后好不容易要到一部分,就想着先寄回去给老母亲治病。没想到还没出公司就被几个工人堵住了。他们以为小黄准备带着钱开溜,没说几句话就动手了。几个人打一个人,总归要出乱子的,个么好了,不知道谁踢到了他的头,人嘛一下子晕过去了。那几个工人吓住了,赶紧把他送去医院。送到医院后几个人就跑掉了,还好钱没敢拿。”
几个旅客来到前台办理退房手续,老伯只好再次把话头放下。办好退房手续,老伯干脆让边上一个小姑娘先照看一下,以便顺利地把故事和我说完。
老伯问:“刚刚说到哪里了?”
我说:“黄师傅被送到医院了。”
老伯微微点头,说:“医院一看情况不对,赶快报警。警察来了后,让医院先救人,他们负责联系小黄家里人。医院一看他身边还有些钱,好,个么就先抢救好了。警察这边也很快联系上了小黄家里人,一听他出了这么大的事,老母亲一着急,人就没了。他老婆也没办法,只能把老婆婆的丧事处理好了才赶过来。你等下啊,我喝口水。”
老伯端起茶杯咕噜咕噜连喝了几口,然后放下杯子继续说:“哎,你说说看哦,这个小黄上辈子是不是造什么孽了呀?”
我说:“听您这口气,这事还没完呀?”
老伯摇了摇头:“他老婆嘛急急忙忙带着小孩子赶过来,个小宁(这个小孩子)一路发高烧,小黄还没出院,他儿子又进医院了。中间七七八八的事我就不说了,反正最后小黄父子俩命是都保住了,不过两人都傻掉了。小黄还稍微好点儿,他儿子直接瘫掉了。
“小黄老婆带着小黄和儿子准备回老家,谁知道在车站等车的时候,小黄跑掉了。最后你猜在哪里找到的?在重庆路。小黄站在路牌下面说到家了。他老婆说这里是上海,不是重庆。小黄指着路牌冲老婆发火,说这里就是重庆。他老婆没办法,只能抱着孩子哭。唉……作孽哦。”
老伯说到这里叹了口气,拿下眼镜揉了揉微微发红的眼睛,然后戴上眼镜继续说:“好好一个家就这样毁了。老公嘛傻了,儿子嘛瘫了,小黄老婆想要找个工作也没办法找,总不能三天两头地请假吧。家是回不去了。她托亲戚把家里的东西都卖了,折现给她汇款过来,这些钱前后也就撑了一年吧,又是给儿子看病吃药,又是租房子什么的,再加上平时的开销,一家三口很快就流落街头了。”
我问:“为什么不回去呢?在老家有亲戚照应,日子也不至于过成这样吧。”
老伯说:“小伙子呀,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啦。以前的亲戚嘛叫亲戚,现在有的亲戚说难听点儿,就是有点儿血缘关系的路人。再说了,你是没见过小黄发病的样子,很吓人的。他认定重庆路就是重庆,死活不肯走。他老婆还带着个瘫掉的儿子,怎么争得过他?这还是刚开始,后来小黄的病也越来越严重了,经常连自己老婆儿子都不认识了。”
我问:“那他老婆、儿子呢?怎么没见黄师傅跟他们在一起?”
老伯说:“哦,刚才忘了和你说了,昨天那对母子就是他老婆儿子。他到哪里,他老婆就带着儿子跟到哪里,生怕他发病做出什么事来。以前他发病和人家闹,被人打得不轻。”
听到这句话,回想起昨天的情景,我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堵着,难受。
老伯说:“本来想着出来做生意挣钞票,可以衣锦还乡,谁知道连家乡都回不去了。哎,你说说看,可怜哇?以前我们那个年代说,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现在嘛小年轻做生意,一口一个‘亲’。‘亲’是这么好叫的呀?爹亲娘亲总归要走的,小夫妻再恩爱也逃不过生离死别。老天要收人你也拦不住,但只要还在家乡,还在家,个么回忆就还在。落叶归根是多少人的愿望啊。所以我说啊,再亲也亲不过家乡。我就觉得上海老好哦,就算上海变成南京那样,我家在上海,我家里人在上海,我家老太婆的魂在上海,个么我就觉得上海始终是最好的。你说对哇?”
我点了点头,内心却忍不住问:“南京怎么得罪你啦?”
晚上回来从南京路路牌下走过时,我停留了一下,看着上面“南京”两个字,突然有种莫名的亲切感。
5
高铁正以三百公里的时速开往南京。
我面前的小桌板上放着一盒维他奶,是我临上车前在超市里买的,算是这次来上海的一个纪念。
看着这盒维他奶,我回想起中午再次遇到黄师傅的情景。
再次遇到他是在地铁站入口,他依旧是三天前的那套装扮,坐在入口的台阶上不知道在想什么。
我拖着行李箱走到他面前的时候,他看了看我,然后站起身来。
我问:“你还记得我吗?”
他皱着眉摇了摇头,问:“你来这里出差呀?”
我想他是不记得我了,我又不想在他面前提起“回家”这两个字,索性点了点头。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盒维他奶递给我,说:“给你家里人打个电话报平安吧。”
我接过维他奶,是个空盒子。盒子的表面用圆珠笔画出了手机键盘的样子,其中数字1的位置上写着“家(妈妈)”。
六七年前触屏智能手机还很罕见,但是很多人都有设置快捷键拨号的习惯。显然,黄师傅就是其中一个。
耳机里传来南拳妈妈《牡丹江》中的一句:到不了的都叫作远方,回不去的名字叫家乡。
归心似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