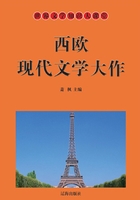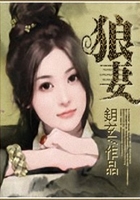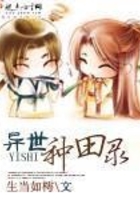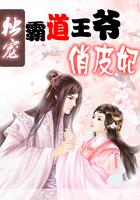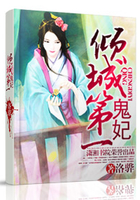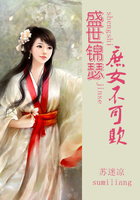小说语言要求生动、形象、得体,能够突出人物的鲜明个性,将事件讲述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这不仅需要作者拥有敏锐的生活触角,能准确地把握人物的特色和故事的关键,更需要作者能够准确而灵活地运用语言来表达。句子是表达完整语意的最小的言语单位,不构成句子,便不能表现为言语。刘勰的《文心雕龙》说:“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1]说的便是,字(词)、句、章、篇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字句的选择是基础,关乎全章全篇的得失。好的小说,词语的锤炼必不可少,句式的选择和运用也至关重要。小说写作,是一种创造性劳动,是对语言的同义形式的选择过程,是在所指相同的情况下,选出适合题旨情境的能指。这个选择的过程,就是修辞活动。
下面我们根据不同标准所划分出的不同句式,来探讨莫言在句式选择和运用上的特点。
不同语气的句式的选择
从语气上分,现代汉语的句子有陈述句、感叹句、祈使句和疑问句。陈述句是用平直或下降的语调来陈述说明的句子类型,可以表示肯定或否定,又叫直陈句。感叹句抒发强烈感情。疑问句包括疑惑和询问,可以既疑且问,可以疑而不问,也可以问而不疑。祈使句是向听话人提出要求、表示命令或请求的句子。这四种句式,陈述句、问而不疑的疑问句、感叹句、祈使句都可以表达确定不疑的意思。在使用的过程中,他们可以表示相近的意思,例如:武汉的春天很美。武汉的春天真美啊!武汉的春天难道不美吗?让武汉的春天永远都这么美吧!不同的语气,表达的感情强烈程度不同。作家在写作的过程中对不同的句子的选择,主要依据语言环境和表达目的。
一、陈述句与疑问句的选择
陈望道先生在《修辞学发凡》中提到,有一些疑问句是发话者“胸中早有定见,话中故意设问”[2]的句式。现在汉语中,往往把它们分为反问句和设问句两种。
反问又叫反诘、诘问,反问句是用疑问的形式表达非疑问的——即肯定或否定的意思的句式。吕叔湘先生在《中国文法要略》中指出:“反诘实在是一种否定的方式,反诘问里没有否定词,这句话的用意就在否定;反诘句里有否定词,这句话的用意就在肯定。”[3]也就是说,反问句所表达的意义其实是确定无疑的,要么是肯定,要么是否定。而陈述句可以表达肯定的意思,也可以表达否定的意思。反问句和陈述句是可以构成同义关系的不同形式。反问句是表达否定的一种方式,所以肯定的反问句可以转化成否定的陈述句,否定的陈述句可以转化成肯定的陈述句。但是,我们会发现,反问句在转换成陈述句之后会失去部分话语功能。例如:“你不是说过要跟我一起去吗?”转化成陈述句是:“你说过要跟我一起去。”那种反诘、质疑的语气失去了,所表达的不满情绪也淡化了。与陈述句相比,反问句的主观性更强,表述的观点更加明确,语气更加坚定。正是因为反问句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色彩,在小说写作当中,合理地运用反问句,能够鲜明地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既营造出人物的“势”,也增加小说语言的“势”。
莫言常常将反问句式运用于故事中人物的口语之中,表示不同的话语功能。
用反问句来辩驳、说理,比陈述句语气强烈,尤其是连珠炮似的反问句连用,说理性更强。如:
(1)“跑,跑到哪里去?!”上官吕氏不满地说,“福生堂家当然要跑,我们跑什么?上官家打铁种地为生,一不欠皇粮,二不欠国税,谁当官,咱都为民。日本人不也是人吗?日本人占了东北乡,还不是要依靠咱老百姓给他们种地交租子?他爹,你是一家之主,我说得对不对?”
(《丰乳肥臀》)
(2)村长说:孙马氏,你这话是怎么说的?现如今谁家还有两个三个的儿子预备着?我家也只剩下一个儿子,不是也当兵去了吗?
(《儿子的敌人》)
(3)如果女人不生孩子,国家到哪里去征兵?天天宣传美国要来打我们,天天吆喝着解放台湾,女人都不让生孩子了,兵丁从哪里来?没了兵丁,谁去抵抗美国侵略?谁去解放台湾?
(《蛙》)
(4) “告诉我,你怕什么?”猛兽管理员的声音像小号一样悠长雄辩,“你一听到人肉,就想到了活人。这是自己与自己为难。死人在你的手里,就像泥巴在塑神的匠人手里一样,就像猪肉在大师傅的肉案上一样。要揉要搓,要捏要摸要削要剁——还不是由着你?人死了有什么?你说人死了有什么?大首长都把遗体捐献给医院解剖——一点下脚料算什么——大首长生为人民谋幸福,死为人民作贡献——下脚料算什么?狮虎是珍贵动物,人民群众要观赏,大熊猫下崽登报纸上电视全世界都知道,下脚料算什么?”
(《十三步》)
有时候用来表示斥责、不满和抱怨。如:
(5)她恼怒地骂道:“你这个小子,锃明瓦亮两只贼眼,盯着我的抽屉,是不是要撬我的锁,偷我的钱?给你的零花钱花完啦?老兔崽子,告诉你,必须戒烟,我勒令你戒烟!你挣几个工资,也配抽烟?烟是为你们这些喝粉笔末子的家伙准备的吗?瞧瞧你这幅德行样子:红墨水蓝墨水,一脸晦气,当年算我瞎了眼,被你运动衣上那几个字迷住了……”
(《十三步》)
(6)姑姑咬着牙根说:什么这活儿你干了一半?……你这个老妖婆子,你以为女人的阴道像老母鸡的屁股一样,用力一挤,鸡蛋就会蹦出来?……你还想去告我?
(《蛙》)
(7)王超一屁股坐在被子上,毛猴着脸,自言自语地念叨着:“我怎么这么倒霉?别人碰不上的事为什么偏被我碰上了?我招谁惹谁了?”
(《丰乳肥臀》)
有时候表示讽刺、揶揄。
(8)村子里那些坏人看到黄彪发了狗财心怀嫉妒,便恶语攻击:黄彪黄彪,你把老牛当娘养,好像是个大孝子,其实你是个虚伪的家伙,如果老牛是你的娘,你就不应该挤你娘的奶水喂小狗,你用你娘的奶水喂小狗,你娘岂不是变成狗娘了吗?而如果你娘是狗娘,你不就成了狗娘养的了吗?而如果你是个狗娘养的你不也成了一条狗了吗?
(《四十一炮》)
(9)别装了,我说,谁不知袁半仙是大能人?
(《蛙》)
反问句表达的意义非常丰富,除了以上这些表达消极意义的,也有表示中性的建议或催促,甚至是积极的客气、鼓励和夸赞。例如:
(10)姑姑说:小跑,长大了跑远点,还愁没表戴?
(《蛙》)
(11)还有什么能比生出优秀的孩子更令爸爸自豪的吗?没有啦。
(《十三步》)
人物的语言特色,能够反映出人物的性格特点。莫言笔下,有一些人物的语言中经常出现反问句。反问句常常是用来否定对方肯定自己获得话语权和话语地位的表达方式。
获得了矛盾文学奖的《蛙》中,故事的主人翁“姑姑”是一位豪爽开朗、爱憎分明、行事狠辣干练有雷霆之势的的事业型女性,她的语言便常常用反问句来表示辩驳、怨责和讽刺。
如:
(12)姑姑瞪我一眼,说,连古典文学名着上都有,你还怀疑什么?!
(13)我(姑姑)就说:奶奶,娘,别哭了,哭管什么用?哭能哭出翅膀来吗?哭能哭倒万里长城吗?
(14)你们说说,这些当官的,按说也都是有点文化的人,怎么这样蠢呢?胎儿的性别,怎么能转换呢?我如果有这神通,早就得了诺贝尔医学奖了是不是?
(15)老姑奶奶什么阵势没见过?老姑奶奶少年时连日本鬼子都不怕,七十多岁了反倒怕你个小杂种不成?
“姑姑”的反问句,气势汹汹,激情澎湃,常常让人无可辩驳。莫言正是利用了反问句式的这一特点,树立了姑姑说服力强、工作责任心极强、“可以指挥千军万马”的女强人形象。可见,如果将这些反问句换成直陈句,“姑姑”的气势就弱多了,直陈句远远没有反问句更能体现“姑姑”这类人物的性格特点。
再如,《丰乳肥臀》中的上官吕氏,是一位专横凶悍的女性,她在全书中共说过110句话,有三十六句是疑问句,其中又有二十七句是反问句,可见反问句所占的比重比较大的。反问句的频繁使用对塑造上官吕氏的强势形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例如:
(16) “谁告诉你日本人要来?”上官吕氏恶狠狠地质问儿子。
(17) “跑,跑到哪里去?!”上官吕氏不满地说,“福生堂家当然要跑,我们跑什么?上官家打铁种地为生,一不欠皇粮,二不欠国税,谁当官,咱都为民。日本人不也是人吗?日本人占了东北乡,还不是要依靠咱老百姓给他们种地交租子?他爹,你是一家之主,我说得对不对?”
(18)上官吕氏怒道:“我问你哪,龇牙咧嘴干什么?轱辘轧不出个屁来!”
(19)她几乎是哭着说:“樊三啊,难道你能见死不救?……”
(20)上官吕氏愤怒地看着儿子,道:“正八经的话你一句也听不到,歪门邪道的话你一句也落不下。亏你还是个男人,是一大群孩子的爹,你脖子上挑着的是颗葫芦还是个脑袋?你们也不想想,日本人不是爹生娘养的?他们跟咱这些老百姓无仇无怨,能怎么样咱?跑得再快能跑过枪子儿?藏,藏到哪天是个头?”
莫言的小说中有大量的独白性语言和演讲式语言。他曾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提到,自己幼时是一个特别爱说话的孩子,还常常复述说书人的故事并且在故事中添油加醋,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促成和培养了他在叙述过程当中适时穿插议论表达观点的特点。用反问句来发表议论能够更鲜明地体现说话人的立场,表达强烈的感情。莫言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常常借用第一人称的“我”,用反问句来发表议论。这些反问句,从文章本身来讲,能够体现人物“我”的性格特点,从作者的角度来讲,能够反映作者对人物性格特征、心理特征和语言特征的正确把握。
在作品《蛙》中前四个部分,作者是以第一人称的角度来叙述的。第一部分中“我”还处在孩提时代,他的童言童语中便多次出现反问句。如:
(21)我们都是七八岁孩子,怎么还可能吃奶?即便我们还吃奶,但我们的母亲,都饿得半死,乳房紧贴在肋骨上,哪里有奶可吃?
(22)森林是绿色的,怎么可能变成黑色的煤炭?
(23)我知道陈鼻这样说是出于对我的嫉妒,他生在我们村长在我们村,连条苏联狗都没见着,如何知道苏联飞行员比中国飞行员技术好呢?
(24)难道它要在我们操场上降落吗?
(25)但,怎么说呢,能开上这种飞机,也够神气了是不?把这么沉重的一块钢铁开到天上去的人,哪个会不是英雄呢?
例(21)中,“我”对老王的话感到不满和不服,于是承接老王所说的“吃奶”提出反问,体现了儿童思维的简单和好辩的个性。例(22)用反问的语气表达了儿童对事物的好奇和疑惑。例(23)体现了孩子好强的心理。例(24)则生动地体现了孩子容易大惊小怪的特点。例(25)中“也够神奇了是不”的“是不”这种稚嫩的口吻也是孩童特有的语气。以上反问句恰当地表现了儿童天真烂漫的特点,符合写作者叙述时的角色心理。倘若这一部分用严肃成熟的大人口吻,便远没有这种这种活泼可爱的语言来得有趣和吸引人了。
《丰乳肥臀》中,“我”上官来弟幼时是一个被母亲宠坏了的小男孩儿,也时常发出具有儿童特色的反问。
(26)那人嘟嘟哝哝走了,我们替三姐感到害躁。蚂蚱呀蟋蟀呀,都是鸟儿的美食,怎么可能治好人的眼疾呢?
(27)连我八姐上官玉女都没资格分食我的乳汁,凭什么给她吃?!上官来弟那两只奶子闲着干什么呢?
设问是为提醒下文而问,下文就是答案。莫言是一个非常善于讲故事的人。他讲故事的方式,可以分三层。第一层,作者本身要对整个故事的讲述有全局的把握,如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第二层,是被作者用来讲述故事的第一线索人物“我”,间接地承担了讲故事的责任。“我”发表的议论,并不代表作者的观点,但是“我”的所思所想,是吸引读者的关键,也是引发读者共鸣感情的桥梁。第三层,是线索人物“我”所见所闻的其他角色人物“讲故事”的方式,人物的语言特点能很好的体现人物的性格特征。设问句能巧妙地承接前文,引发话题,无论是作为角色人物的语言,还是作为作者的叙述手段,都能起到很好的修辞效果。
作者将设问句安排在全篇或者段落之首,是为了引起注意,引发新的话题。例如:
(28)陈鼻为什么生了一只与众不同的大鼻子呢?这事儿大概只有他母亲能说清楚。
(《蛙》)
(29)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怎样变成了香气馥郁、饮后有蜂蜜一样的甘饴回味、最后不损伤大脑细胞的高粱酒?母亲曾经告诉过我。
(《红高粱家族·高粱酒》)
(30)为什么要在办公室里安一口釉彩大缸呢?为了防火?不是,因为二楼上的水龙头从不出水,水塔太低压力不够,流体力学,公式。
(《十三步》)
用在叙述段落的中间,往往是为了承前启后,从述题中引出新的话题,吸引读者继续阅读。
(31)老王狐疑地看着我们。他以为我们要冲进伙房哄抢食物吧?所以他说,滚,小兔崽子们!这里没有你们吃的,回家吃你们娘的奶头去吧。
(《蛙》)
(32)很久之后的日子里,物理教师还在解答这道难题。我为什么迟迟不愿睁开眼睛呢?是我怕一睁眼睛就丢掉什么吗?是的,无论多么辉煌的臀部也代替不了人的脸,冲淡得了但毕竟代替不了对旧时面容的回忆。
(《十三步》)
(33)但二姐的哭声又使我们陡然紧张起来。二姐为什么哭?二姐哭决不是因为高兴,而是因为悲哀,我马上想到:支队司令员摔死了。
(《丰乳肥臀》)
用作角色人物语言的时候,有时正是用反问句作设问。说话人对听话人的某一观点进行反诘,表示强烈的否定,进而引出自己的观点,说理性更强。如:
(34)刘贵芳:什么差不多算是伟人?姑姑本来就是伟人!
(《蛙》)
(35)母亲对着骂道:“来弟,你这个不要脸的臊货!沙和尚,你这个黑心肠的土匪!你们只管生不管养,你们以为扔给我就会给你们养?你们做梦吧!我要把你们的野种扔到河里喂鳖,扔到街上喂狗,扔到沼泽里喂乌鸦,你们等着吧!”
(《丰乳肥臀》)
(36)李武把牙缝里的绿豆芽呸地一声啐到地上,然后把手中的筷子,重重地拍在桌子上,用明显不快但是又宽容友好的口吻说:“刘老大,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以为俺是冲着吃来的吗?你大叔要是想开荤,随便到那家馆子里一坐,用不着开口,那些海参鲍鱼、驼蹄熊掌、猴头燕窝,就会一碗接着一碗地端上来。吃一尝二眼观三,那才叫筵席!你家这算什么?两碟子半生不熟的绿豆芽,一盘腥骚烂臭的瘟猪肉,一壶不热不凉的酸黄酒,这也算喜宴?这是打发臭戏子!俺们到你家来,一是给你爹捧捧场,撑撑门面,二是与乡亲们拉拉呱儿。你大叔忙得屁眼里蹿火苗子,抽出这点工夫并不是容易的!”
(《檀香刑》)
有时候是说话人自己在说话过程中用设问句承前启后引出新的话题,是一种适应听话人从新信息到旧信息的接受心理的说话技巧。如:
(37)黄秋雅这个上海资本家的千金小姐,名牌大学毕业生,被贬到我们高密东北乡,真是“落时的凤凰不如鸡”!谁是鸡?姑姑自我解嘲地说,我就是那只鸡,跟凤凰掐架的鸡,她后来可真是被我揍怕了,见了我就浑身筛糠,像一条吞了烟油子的四脚蛇。
(《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