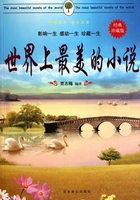1935年,国民政府为挽救经济、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紧急实施新的货币法案,于11月3日宣布实施《紧急安定货币金融办法》,11月4日实施《法币规定》,由政府授权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发行法定货币——“法币”,并规定“法币”为中国唯一的法定货币。
由此,银元作为中国合法货币的历史终结,史称“法币改革”。
与一系列货币政策改革相伴随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四大家族”对金融业的垄断和兼并。
1927年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之初,立即着手重建中央银行,资本额定为2000万元,由政府以公债形式一次拨足,并指定该行为国家银行,具有经理国库、铸造货币、发行兑换券、经募内债和外债的特权。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正式在上海开业,同步在南京、九江、徐州等12个城市设立分行、支行及办事处,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兼任总裁、理事会主席。
开张之初,中央银行的实力远远不如当时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但它在政府的扶植下,凭借各种特权迅速壮大。1935年4月,中央银行乘发行金融公债之便,增资为1亿元,一跃而成为全国最大的银行。同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改革”,这一措施为中央银行的金融垄断开了方便之门。
创办中央银行的同时,国民政府控制了原本由北京军阀政府统治、具备国家银行性质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并于1928年对其进行了改组,将其总部搬迁至上海。
改组前,中国银行原有资本2000万元,其中商股占全部股份的99.75%,改组后,中国银行资本新加入500万官股而增至2500万元;而交通银行改组后,总资本1000万元中加入官股200万元(实际只交了一半)。这样,南京国民政府取得了中国、交通两行各20%股权。
在“白银风暴”中,1935年3月,国民政府以救济金融恐慌为理由,发行金融公债1亿元,并以增加中央、中国、交通三行的放款能力为借口,将其中的1500万元公债交由中国银行认购、1000万元公债交由交通银行认购。这些公债被当做了国民政府在两家银行中的增资扩股。增资后,中国银行官股2000万元,占总资本的50%;交通银行官股1200万元,占总资本的55%。
与此同步,两行进行人事调整,由宋子文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宋汉章为总经理;胡笔江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唐寿民为总经理。从此,中国银行、交通完全被国民政府所控制,成了官僚资本性质的银行。
同一时期,国民政府还设立中国农民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和中央信托局三家大型的金融机构,分别垄断了农业、邮政和公共事业领域的金融业务。
正是凭借以上所述的“四行二局”为中心,南京国民政府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国营金融体系,并实现了对全国金融的垄断。
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合称“大四行”,属于国家银行性质,分别由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果夫)四大家族把持,是国民政府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的主要机构,也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建立金融垄断的核心。
这还远远不够,控制了中国、交通银行这两家具备国家银行性质的银行后,国民政府又将兼并、掠夺的魔爪伸向了民间的商业银行。
在同一时期,国民政府继续通过增资改组等方式,控制了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广东银行等。
其中,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加上原由政府控制的中国国货银行,构成了国民政府的“小四行”。
傅宗耀弄权
国民政府贯彻其金融统制政策,对商业银行尽力兼并和掠夺,而此时的中国通商银行,仅从自身的经营角度讲,面对时局的变幻也早已无力抵制。
中国通商银行自身的积弊,需要从傅宗耀(1872—1940)说起。
1916年盛宣怀去世的当年,傅宗耀(字筱庵)开始担任中国通商银行董事,兼任招商局董事。在此前后,身为盛宣怀义子的他,翻云覆雨,得鱼忘筌,使用蚕食的方法,攫取盛氏财产与招商局资产;辛亥革命后,招商局、电报局把通商银行的认股,以股息金的名义悉数分派给1600多户股东,傅宗耀更是乘机低价收购商股,以充实他的股数。
从1919年开始,通商银行的主要权力就落到傅宗耀的手中,他先是取得了第三任华大班的地位(后改为总经理),后是在盛氏、李氏、傅氏三派斗争过程中,操纵了通商银行董事会,独掌实权。
在北洋军阀期间,擅长投机的傅宗耀投靠北洋军阀。1926年,上海总商会改选,傅宗耀在孙传芳卵翼下,当选为上海总商会第六届会长,作为回报,傅宗耀除了运用通商银行的资金力量支持孙的军用开支外,还利用他招商局董事的权力,为孙运送军火和军队,阻挠北伐军,以致招商局在1926年和1927年两年中亏损达404万两之巨。
1927年春,蒋介石领导的北伐军打败了孙传芳的主力。傅宗耀终因长期投靠北洋军阀而与蒋结下宿怨,又因招商局抵制国民政府的“清查整理”,于是,傅宗耀成为打击的目标。傅宗耀(1872—1940)一度在招商局呼风唤雨,却终因成为遭众人唾弃的汉奸,被国民党特务设计杀死。
1927年4月,傅宗耀逃亡大连,成为著名的亲日派人物。
1931年,经过傅宗耀在上海时的“狗肉朋友”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的一再疏通,国民政府终于撤销了对傅宗耀的通缉令,傅宗耀从大连回到上海。随后,傅主持召开了中国通商银行股东大会。
不久,董事会改组,傅仍任董事长兼总经理,重用有业务才能的人担任各分支行经理,又调整了总行各部门的负责人选,同步精简机构,老弱冗员逐步淘汰;不久,又在宁波、定海之外设置汉口、南京、苏州、厦门分行,并增设办事处和兑换处,扩大业务和钞票流通范围。
1931—1934年间的通商银行,营业虽有所恢复(1934年度,中国通商银行的营业额为6364余万元,在各华资银行中位居第12位),却终因傅宗耀的攀权附贵、投机取巧而危机四伏。
傅宗耀起家,最初靠的是投拜盛宣怀门下,并认盛为义父。此后,傅每每投机攀附,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军阀王金钰的儿子王麟公皆被安插在会计科。1931年董事会改组时,傅还将其狐朋狗友极尽所能地网络在内;对于权贵,傅更是不惜亲自登门拜访,许愿介绍他们的亲属来行工作。
如此复杂的股东及存、贷款客户关系,导致了通商银行经营上的腐败。
为了笼络权贵成为股东,该行长期派发高额股息,自1919年后基本按既定的8厘股息发派,有些年份则高达1分甚至1分2厘;而为了吸收存款,傅宗耀则不惜采用高利率手段,譬如,定期存款大户华成烟厂给美丽牌香烟的商标费就只存不支,存款利率年息7%~9%之间,个别年份达到11%,远比一般银行利率高。
而权贵色彩浓厚的放款对象,导致了通商银行比重巨大的呆滞放款。到1935年6月底,该行放款总额为2228万元,其中26个大户的呆滞放款达1276万元,占放款总数的57%。这些大户中,最大的呆账户是倒台了的北洋军阀政府财政部,呆欠230多万元。长期放了收不回的,则有长兴煤矿、招商局、汉冶萍煤铁矿公司,仅这三个大户就拖欠了500多万元。
1933—1935年发生的“白银风暴”引发工商业倒闭风潮,黄楚九的九移公司、日夜银行宣告破产,通商银行又吃进了一笔倒账;中国通商银行苏州支行经理卢少棠、卢炳生父子共同侵占行款23万元,还有“谢伯记”以大量房地产作抵押,拖欠本息达100余万元。
在个人放款中,上海的虞洽卿、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都向该行借用,从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长期拖欠不还。其他商业及个人方面的放款有15个重点户,呆欠达400多万元。
而通商银行在政府公债和房地产等方面的投资也不顺利,该行的放款余额至1934年年底已达3057余万元,但相当部分或以厂房作抵,或以政府债券作抵,甚至有些还是信用放款,致使呆账庞大,资金周转不灵。
另一方面,为吸收巨额存款冲抵呆坏账,通商银行除高利息手段外,还冒险发行巨额钞票。截至1935年11月3日,该行钞票流通额为2806余万银元,占具有发行权的12家商业银行钞票流通总额22268余万元中的12.9%,居第三位。
隐患重重,傅宗耀却搞起了“形象工程”。
为了装潢门面、欺骗社会,傅竟不顾本行“负债大于资产”的严重情况,从1934年起,在福州路、江西路转角斥资210万元营造一座17层的“中国通商银行大厦”。1935年春末大厦建筑就绪,傅却以某些地方不合格为借口拒付施工方陶桂记营造厂尾款。
于是,施工方带领一批包工在总行大门口坐讨,声势浩大,引起外界舆论哗然,市场传说纷纭,传言中国通商银行将有大变化,这使得该行现金周转越发困难。
终遭改组
“白银风暴”中,国民政府与“四大家族”趁机于1935年3月改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大银行,同时,又唆使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积聚大批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的钞票,一次性向该三行兑现,造成“挤兑风潮”。
中国通商银行系三行中发生挤兑的最后一家。事发前,傅宗耀已估计到“四大家族”要来这一手,就请求杜月笙与张啸林向“四大家族”疏通,求其不要并吞。杜、张一口答应,杜还叮嘱傅做好准备,对“上面”见机行事。
傅宗耀心领神会,就决定把将落成的“中国通商银行大厦”按已付部分的造价180万银元出让,请杜、张转达“上面”予以收购。两人将此事汇报给孔祥熙,孔就让邮政储金汇业局宋子良出面收购了这所大厦。
宋子良将大厦的名称立即更换为“建设大楼”,并连夜动工把大厦的招牌换掉,引起外界纷传:中国通商银行连大厦也得出让了。孔祥熙还通知中央银行,处处对通商银行刁难,外资银行也很势利,借口不予通商银行拆借放款。
1935年端午节前夕,身陷挤兑风潮的傅宗耀向中央银行要求抵押贷款300万银元,拼凑了一些有价证券送去作抵。过了端午节,傅宗耀认为难关已过,但突然接到中央银行电话通知:“账上没有头寸。”傅宗耀就急忙跑到财政部次长徐堪家里下跪叩拜,哀求帮助,仍告无效。
此时,孔祥熙又火上加油,策划了兼并整理的策略,并授意杜月笙、张啸林“出面维持”。山穷水尽、无可奈何之下,傅宗耀只好双手捧了通商银行资产负债清册交给杜、张二人,自己则以生病为理由,请求辞去通商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职务。
随后,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答应各拨100万银元予以接济,其中,中央银行的100万首先拨到,使得中国通商银行的挤兑局面得到缓解。
6月7日上午,中国通商银行召开董事会。中国通商银行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以杜月笙为董事长,张啸林为副董事长,傅宗耀改任常务董事,并聘请顾诒毂为总经理。
此次董事会上,傅宗耀黯然出局,国民政府完成了对通商银行初步的人事控制。
1935年11月3日、4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法币改革令”,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钞票定为“法币”,并剥夺其他银行的发行权利。其后财政部迅速采取一连串行动,对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除外的原发行银行的库存钞券进行清理和接收,并催促各行缴纳流通券的准备金。
中国通商银行的准备金迟迟难以按照财政部的要求缴足。至1936年12月12日,该行尚短少现金准备1344余万元和保证准备约645万元,共计1989余万元。
对此,财政部长孔祥熙向行政院提议:除旧财政部欠款及招商局、江南造船所之欠款由财政部查核属实并准予抵充外,中国通商银行其余欠缴之数由该行以政府公债按照额面计算予以抵充。具体来说,该行欠缴之1980余万元,以政府公债1430万元、其他证券100万元、房地产80万元、旧欠375余万元抵充。该行按上述办法抵缴准备金之后,账面上即显示严重亏损状况。据孔祥熙估计,该行约亏400万元。
在追缴发行准备金的过程中,国民政府趁机加入官股。1936年12月,孔祥熙对该行增股贬值之事提出方案:该行由财政部加入官股300万元为优先股,该行原有旧股由股东会依照公司法规定贬值为10%或5%,另行换给普通股票与优先股,以示区别。
对此,通商银行1937年1月召开临时股东会予以讨论,认为折减率10%太低。2月,该行续开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向财政部提议将原有股本折减率酌量增加,并增加官股为450万元。2月27日,财政部批示该行,将其旧股折减率增加为15%,即原有股本350万元折为52.5万元,并加入官股347.5万元,凑成资本总额400万元。此官股循财政部拨中国、交通两银行官股办法,以“复兴公债”拨充。
3月22日,通商银行召开临时股东会,通过章程修正草案并选举董事和监察人。在11名董事和5名监察人中,官股代表分别占7名和3名,并由财政部在5名常务董事中指派一人为董事长,总经理于董事中选定聘任。
经财政部指派,杜月笙为该行董事长,中央银行业务局副局长胡以庸为该行总经理,两人均为官股代表;4月30日,该行对各处部处长、经理、副处长、副经理及稽核处稽核进行委派。同日将虹口、南市、汉口三分行改为支行,并委派三支行的经理和副经理;5月6日,又委派各处部各课课长及办事员。
至此,国民政府完成了对中国通商银行的增资改组,中国通商银行由一家民营的商业银行,转变为“四大家族”金融垄断的一颗棋子。
风雨通商银行(中):抗战内迁
总行内迁,资金内移
国民政府完成对中国通商银行的增资改组后不久,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随后的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11月12日,上海沦陷,11月13日,国民政府军队撤出上海南市,蒋介石完全放弃上海。
纷乱的战局中,1937年11月中旬,中国通商银行特设上海分行,同时将总行机构迁至法租界霞飞路,以便相机内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