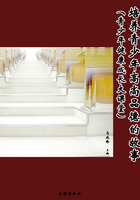诺第留斯号于11月26日凌晨3点在西经172度越过了北回归线,第二天,夏威夷群岛已隐约可见了,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驶出了4860海里!
现在的船向依然是东南方。12月1日,在西经142度穿过赤道,4日,在经过快速的顺利行驶后,远远看到了马贵斯群岛,西经139度32分,南纬8度57分的奴加衣瓦岛的马丁尖岬,它是法属马贵斯群岛中地位最高的一个。那山岭上覆盖着茂密的丛林,不过尼摩船长并不想靠近它。
这些美丽的富有诗意的岛屿渐渐远去了,自12月11日一个星期驶出了4000海里。这期间我与尼摩船长谈话的机会很少。大部分时间是在客厅里读书,或者欣赏窗外的海底世界。隔着客厅墙壁上打开的厚厚玻璃,每天都觉得受益匪浅。
海洋向我呈现出层出不穷的各种神奇景观,有时会搞得人眼花缭乱。
有一天,我正捧着一本书读得津津有味,那是让·马西所著的一本极富情趣的《胃的奴仆》,突然康塞尔的喊声打断了我!
“先生能到这儿来一下吗?”他用一种惊异的声调说。
“是什么,康塞尔?”
“还是请先生自己来看吧。”
在电灯照射下,有一团巨大的、静止不动的黑乎乎的东西悬浮在海水中。我认真地观察着,努力想分辨它是不是某种鲸类,但是,一个念头突然闪过我的脑海,我惊叫道:
“是只船!”
“不错,”尼德·兰答道,“是一只沉船的残骸。”
那的确是一只沉船,船上已经断了的桅绳还系在链上,船体看来还很完整。看来这次事故就在几小时之前,船向左侧斜躺着,可以看到几具尸体拴在绳索上,还可以看到他们临死前的挣扎,保持着生命最后的动作。里面竟有一个妇女和一个小孩,她曾想把孩子举向头顶,那可怜小家伙的手臂还紧紧地搂着妈妈的脖子,妇人绝望的脸上刻画出生之渴望与死之恐惧交织而成的神情。
我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没有想到在这大洋底部,有那么旺盛的生命,也有这么悲惨的幽灵,在它广阔的胸怀中,凝聚着那么多的苦痛与欢乐,包容着万物生灵的爱与恨。
在后来,我们又能看到了其他遇难的船只,那一幕幕惨剧,一场场恶梦,在我沉闷的航行中增添了凝重。
我在12月11日又远远看到了帕摩图群岛,它延伸在西经125度30分至151度30分之间,南北纵横于南纬13度30分到20度50分之间,自度西岛跨至拉查岛,东南伸向北,起伏绵延在海面上达5000海里。把它扯平了,面积是370平方里,内含60个小群岛,其中有不支属甘比尔群岛,全是法国国旗下的珊瑚岛。地面由于珊瑚的堆积而缓慢但不间断地升高。所以,这些小岛终有一天会被连成一个整体,日久天长,就会有一个新大陆自新西兰到马贵斯群岛,那可能是新人类的第五大洲。
有一天,我把新大陆的构成理论讲给尼摩船长听,他只是冷冷地答道:
“地球上现在并不缺少新大陆,而是缺少新人类!”
我们的航向是克列蒙端尼岛,这个岛在群岛中最特别。我在那儿可以研究这个太平洋中的小岛是如何由石珊瑚建成的,我发现,石珊瑚不能与普通珊瑚相混淆,它由一种裹着一层石灰石的纤维组成,可根据其构造不同将其分为五类。这些组成珊瑚的细小微生物,成百万地生活在石珊瑚的细胞之中。这些石珊瑚堆积起来,形成岩石、礁石和岛屿。有时它们还会形成一个圆环,组成一个环礁湖的洞。其边缘的缺口与大海相通。有时会形成高高的、陡峭的礁石,有时则形成一道礁石屏障,跟一堵高耸的石墙一样。
沿着克到蒙瑞尼岛航行了几百米,我惊叹不已地打量着这些微型工作者们建成的“大厦”。这些大厦的墙壁主要是干孔珊瑚,滨珊瑚、星状珊瑚等造礁高手的杰作。这些珊瑚虫主要生长在动荡的海水表层,所以它们的工程是从“空中楼阁”开始,向下建起,上层“地基”带着分泌物向下层伸展。
“先生,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建起这面巨大的墙垣?”康塞尔问。
“科学计算,每个世纪才长出1/8寸的厚度,也就是100年左右!”
他听了非常吃惊。
“那这墙看来大概有1000多英尺,那肯定要花……”
“1920000年,康塞尔。”这个朴实的康塞尔可真是张大了口许久合不拢了。
当诺第留斯号回到海面,我能够辨认出覆着低矮灌木的克列蒙端尼岛的整个发展历程,岛上的珊瑚石明显地被暴风雨侵蚀,成为了肥沃的土壤,接着可能有可可果的种子被海浪冲到这片未来的海滩上,在这里发芽扎根,渐渐成为大树和树林,阻止水的蒸发。于是逐渐形成了溪流,慢慢地,植物有了生长的土地。一些小生物、爬虫、昆虫随着大风从邻近岛屿刮过来,海龟也来这里产卵,鸟儿在树上筑巢,动物于是繁衍起来。最后,这片青翠、肥沃的土地也吸引了人类,来到这个岛上。这就是这些微小动物们建造岛屿的过程。
傍晚,当克列蒙端尼岛融入远方的夜色中时,诺第留斯号的航向改变了。在西经135度处跨过南回归线后,船又改向西北偏西、向着回归线区驶去。当它在东加塔布群岛和航海家群岛间穿过时,测程仪上表明已航行了9720海里。
我已经有一个星期没见到尼摩船长了。这天早晨他走进客厅,跟往日一样,仿佛刚离开我们只有5分钟。
我正忙着在地图上寻找诺第留斯号多变的航向。他修长的手指按在一个点上,说:
“万尼科罗。”
万尼科罗是一个神奇的名字,那是拉·白鲁斯探险沉没的地方。我当即站起身来。
“诺第留斯号将把我们带向万尼科罗去吗?”
“是的,教授。”
“那么,我将可以看到罗盘号和浑天仪号两只船触礁沉没的地方吗?”
“只要你愿意,教授。”
“那我们何时到达?”
“已经到了,教授。”
我爬上平台,急切地扫视着天际。尼摩船长也随后上了平台。
在东北方向有两个高低不一样的火山岛,周围环绕着40海里的珊瑚礁,万尼科罗群岛就在眼前了。
这时,尼摩船长问我对拉·白鲁斯的失事知道多少。我说:
“也就是每个人都知道的那些,船长。”
“你能告诉我每个人都知道些什么吗?”他带着一点挖苦的味道问。
我告诉他这事件的大体情况后,他说:“那么,这些遇难者建造的第三条船是在哪里失踪的呢?恐怕人们不会知道吧?”
“是的,没有人知道。”
尼摩船长不再说什么,不过他示意我跟他来到客厅,诺第留斯号向海水下潜入几米深,并打开了嵌板。
我冲向玻璃窗,只见菌生植物、管状植物、翡翠莫石竹草下面的珊瑚礁石基上,沉甸着无数可爱的鱼,我可以分辨出一些不能打捞上来的残骸,有铁马蹬、大炮、炮弹绞盘架和船头废料等,都是那些沉船上的东西。
我久久地凝视着这些触目惊心的场面,这时,尼摩船长在我身边严肃地说:
“1785年12月7日,罗盘号和浑天仪号在白鲁船长率领下出发,开始时,它在植物湾靠岸,探查了友爱群岛、新喀里多尼亚,然后驶向圣克鲁斯群岛。至哈巴与群岛时停靠在摩加岛。最后他们驶向从未知晓的万尼科罗群岛。罗盘号率先撞在了南岸的礁石上。浑天仪号慌忙来救,撞上了暗礁,罗盘号当时就沉没了,浑天仪号仍苦苦支撑了几天。幸好他们受到当地土著人的好意收留,遇难者们在岛上居住期间,把两艘船的船骸又加以拼凑,建造了一艘小型的船。当时,有的船员就在岛上定居下来没随船走,另有一些老弱有病者,又在白鲁斯的率领下出发了。他们打算驶向所罗门群岛,但是,当他们行至万尼科罗群岛的主岛与西岸之间时,再次遭到不幸,船上人等无一生还。”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我叫道。
“这是我在他们失事的海底找到的证据。”
他指着一个铁盒子对我说,上面还印着法国的国徽,把盒子打开,里面是一卷已有些发黄的公文。
那是法国海务大臣为白鲁斯船长下达的指令,下方还有路易十六的亲笔批语!
“啊!”尼摩船长叹道,“作为一名海员,这样才算风光!多么幽静的珊瑚公墓啊!请上帝保佑,不要让我和我的同伴们葬到与此不同的坟墓中!”
12月的末尾3天,诺第留斯号离开了万尼科罗群岛,向西北方向疾速行驶。自拉·白鲁斯群岛走出750海里到达巴柏亚群岛的东南尖角。
今天是1868年的第一天,一大清早,康塞尔也爬上平台问候我。
“先生,祝你新年快乐,一年幸福。”
“谢谢你,康塞尔,我接受你的祝福,但就我们现在的处境,你所谓的一年幸福,是我们结束囚禁生活后的一年呢?还是说我们要在船上继续一年这种神奇旅行呢?”
“上帝呀,”康塞尔答道,“我该怎样回答先生呢?这两个月以来,我们始终觉得很充实,游历了许多奇异的景观,虽然将来还生死未卜。但我却知道我们再不可能有这种机会了。”
“因此我想说,先生,”他顿了一下说,“我想说的一年幸福,就是可以在一年内看到一切……”
“你想看到一切,康塞尔?那一年时间恐怕不够,而且也不知道尼德·兰是怎么想的。”
“尼德·兰与我想得恰好相反,”康塞尔答道,“他这人很务实,而且胃口特棒,每天只是看鱼和吃鱼并不能令他满足。一个真正的萨克逊人,如果失去了酒、面包和肉,那是很痛苦的。”
自从登上诺第留斯号,我已随船驶出了11340海里,再往前行就是澳大利亚北边的珊瑚海,那可是个危险地带。我们将从暗礁几海里远的地方驶过去。
我却希望能看到这条360里长的礁脉,暗礁上时常巨浪滔天、奔腾鼓荡、震耳欲聋。但诺第留斯号这时却向深海潜下去,我想看这座珊瑚长城的愿望破灭了,看到的只有钻出来的各种鱼类:有嘉蒙鱼、青花鲷鱼,还有被称为海底飞燕的锥角飞鱼,黑夜中磷光闪闪,照耀在空中和水中。我还在鱼网中捡到一些软体类和植虫类动物,有翡翠鱼、海猬、槌鱼、马刺鱼、罗盘鱼和樱子鱼、硝子鱼。另外网中还有漂亮的海藻,如刀片藻和大囊藻,它的表面上有一层从细孔中分泌出的粘液。并能采出一种美丽的胶质海藻,这在博物馆中一般都要被奉为“天然珍宝”。
离开珊瑚海两天后,巴布亚岛映入了眼帘。这时尼摩船长对我说,他计划穿过托列斯海峡去印度洋。
听到这个计划,我感到高兴而又害怕,高兴的是能游历号称世界最危险的海峡,害怕的是,那里曾令许多航海家都望而却步,我们能否闯得过去?但有一个人却高兴得跳了起来,那就是尼德·兰,因为欧洲海正是他向往的地方。
三十四里宽的托列斯海峡来到了,小岛、岛屿、暗礁和岩石星罗棋布,不时拦住去路。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尼摩船长亲自驾驶诺第留斯号,他使船浮上水面行驶,鲸鱼尾巴似的推进器,在后面慢慢揉搓着海浪。但海水被激怒了,张牙舞爪地翻腾起来。海浪气冲冲地从东南跑到西北,见到那些露出头来的珊瑚礁,就拳打脚踢,发泄一通。
“大海真是太可怕了!”康塞尔富有诗意地说。
“这古怪的船长,”尼德·兰却说,“对这条航道一定非常熟悉,因为在这礁石密布的地方,稍不注意,船身就会被撕碎……”
的确,我们正身处险境,但船长也真是神通广大,竟能神奇地穿过一个个险关。它并没有沿着浑天仪号和热心女号原来的航路,而是稍微向北沿着莫利岛,又转向西南方,驶向甘伯兰海道,忽而它又转向西北,从很多不知名的小岛间穿过,驶向通提岛及一些凶险的航路。它又一次改变方向直往西方的格波罗尔岛。
下午3点时,大海更加怒不可遏,到了涨潮期,诺第留斯号靠近岛屿并绕着它走了大约两海里,我一个没留神被突然震倒了。原来船碰到一座暗礁,它不再前行,而是在这里搁浅了。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船长。
“没什么,只是一次偶然。”他答道。
“是一次偶然,”我说,“但它却可能会造成使你成为陆地居民的必然!”
尼摩船长怪异地打量了我一下,用一个否定的手势来回答我。
“教授先生,诺第留斯号完好无损,它仍将带你去游览海洋的奥秘,真正的海底旅行才刚刚开始,既然很荣幸能请到你,那就肯定不会让你扫兴。”
“尼摩船长,”我丝毫不在意他的嘲讽,“但诺第留斯号搁浅时正值涨潮,太平洋的潮水一般不会上涨太高,假如这时你都不能将船浮起来,请问你还有什么机会使它离开暗礁,重返大海。”
“你说得对,教授,”尼摩船长答道,“太平洋的潮水的确不会涨得太高,但这是托列斯海斯,潮峰谷底仍会有15米的差距。5天之后的月圆之夜,我们会有好运气的。”
“教授,有什么结果?”尼德·兰在船长走开后凑近我。
“哦,是这样,尼德·兰,等到9号再次涨潮时,船长说圆圆的月亮会好心地把我们送回大海。”
“有这种事?”尼德·兰像个行家似地耸耸肩,“教授,你该听我的话,听着,这个铁筒永远不会再回到海上或海底了,现在,趁着没生锈还能卖个好价钱,其他的用途没有了,现在,我们只好跟船长说告辞了。”
“好朋友,”我答道,“我对神奇的诺第留斯号很有信心,在这四天中,说不定真会有涨潮到来。另外,等我们到了英国或法国的海岸,可以随时实施逃走计划,但现在是在巴布亚海域,那则另当别论,而且,等诺第留斯号真无力脱身时,我们再离开它也为时不晚。”
“难道就这么干耗着?”尼德·兰的火又上来了,“哪怕到岸上走一走,看一看,重要的是换换口味!”
“我也这么想,”康塞尔赞同道,“难道先生不能向你的朋友尼摩船长请求一下,我们哪怕只是到陆地上踩踩脚,可别到时回到地面上连路都不会走了。”
“我试试看,”我犹豫着说,“不过他可能不会答应。”
令我惊奇的是,尼摩船长竟爽快地应允了,并出奇地友好和关怀,嘱咐我们可以不回到船上来了,岛上的土著人可能会对我们有特殊对待。
第二天早晨8点,我们驾驶着诺第留斯号的小艇穿过格波罗尔岛周围的珊瑚石区,停在了沙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