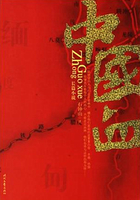第十五章狂欢之苦涩 (2)
残酷可憎的幻灭感又笼罩了她。同样的黑暗和强烈的忧伤,意识到了丑恶永远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她永远也不会安宁。一天下午,她到学校去。草地上开放着雏菊,椴树枝在阳光下柔软地垂下来,显得很绿。哦,她痛不忍睹那些雏菊,那是在地面泛起的白泡沫。在学校里,她知道自己必须走进那虚假的工作间。它一直是个虚假的商店,虚假的货栈,只有一个物质获利的目的,没有生产能力。它装作因宗教的美德——知识而存在,而知识这宗教的美德却成了物质胜利之神的仆从。一股惯性支配着她。出于习惯,她呆板地继续学习。不过,几乎没有什么希望了,她很难专心做一件事。下午的盎格鲁—撒克逊讲座课,她坐在那儿,眼睛往下望出窗外,贝尔武甫(贝尔武甫——英国传奇长诗《贝尔武甫》中的主人公。
此诗被称为英国的民族史诗。——译注。)也好,其他的什么也好,一个字也听不进。下面街上,木栅栏边是阳光照耀的灰色人行道。一个身着粉红色上衣,打着猩红阳伞的女人横过马路,步子轻快有节奏,一个小影子伴随着她。厄秀拉看得出神。打猩红阳伞的女人和她脚边忽隐忽现的小狗走了。何处去了?这穿粉衣的女人走在什么样的现实世界中?她把自己托付给什么样的死气沉沉的不现实的货栈?这个地方,这个学院有哪一点好?如果学盎格鲁—撒克逊只是为了答考试题,为了将来有个更高的商业价值,学它有什么益处?长期在心里供奉着商业意识,她厌恶极了。可是,还有什么?生活就会是这些,仅仅是这些吗?处处、事事都因此而贬值。事事都产生庸俗的东西,妨碍物质生活。她突然放弃了法语,要在植物学拿优等成绩。
植物学是一门为她而存在的学科,她进入了植物的生命中。植物世界奇怪的规律强烈地吸引着她。在这里她看到了一些活动是完全背离人类世界的目的的。学院无聊,贬了值,是一个转向庸俗卑微的商业的殿堂。她不是去听过知识的回声在奥秘的源头跳动吗?奥秘的源头!无聊极了,那些身着袍子的教授们提供在考场里能获得好收益的商品,还是些现成的东西,值不了它要的价钱。这一点他们都清楚。现在,除了在植物学实验室——奥秘之光还在这里闪烁——工作的时间,在学院的所有时间里她都认为是自己堕落到学起虚伪的生意之道来了。刚结束的这个学期她是在愤怒、呆板的状态中度过的。她情愿再出去自己挣钱过日子。比较起来,布林斯里街和哈比先生好像更真实一些。她极度仇恨的伊开斯顿中学比起这所学院枯躁无味的堕落算不了什么。但是,她并不打算回布林斯里街。她要拿到文学士学位,当一段时间中学教员。
大学的最后一年慢慢地过去了。考试和离开学院的日子不远了。幻灭的粉末还在摩擦着她的牙。下一次换地方结果是不是又一样?前面总是一道光辉灿烂的门,然后走到跟前,光辉灿烂的门总是通向另一座丑陋的院子,肮脏,活跃,又死气沉沉。前面总有一座小山,山尖在天空下闪闪发亮。然后,上去了从山顶往下看,只有另一道充满了乱七八糟的肮脏活动的污秽山谷。没关系!每一座山顶总有一点不同,每一道山谷不管怎么说也是新出现在眼前的。
考塞西和她在爸爸身边度过的童年;玛斯庄和玛斯庄附近的小教会学校,她的外祖母和舅舅;诺丁汉的中学和安东?斯克里宾斯基;安东?斯克里宾斯基和月光下的营火舞会;然后就是她一想起就伤心的日子,温妮弗雷德?英格,还有当小学教员以前的那几个月;然后是布林斯里街的恐怖,又到了比较平静的日子,玛斯,玛琪的哥哥,当她在幻想中召唤这个男人的时候,血管里还感觉得到他的影响;然后就是大学,还有多萝西?拉塞尔,她现在在法国,再往后就是又一次回到那个世界中!这些已经成了历史。每一个阶段她的差异都那么大。然而她始终是厄秀拉?布朗温。可是,这是什么意思,厄秀拉?布朗温?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只知道她常常摒弃、拒绝。一贯如此。她总是把嘴里的灰尘、砂子吐出来,她唾弃幻灭和虚假。她只能在不断地摒弃中坚强起来。她的行为似乎总是消极的。
明确地讲,她是隐蔽的,没有露出来,不能露出来,就像一粒埋在干灰里的种子。她生活的这个世界好像是灯光照亮的一个圈子。这个被人类最完整的意识所照亮的范围,她认为就是整个世界。这里的一切对她永远都是暴露着的。然而,在黑暗中,她一直都意识到光亮点,像野兽的眼睛,在闪烁、渗透、消失了。一阵惊恐之中,她的心头所承认的只是外部世界的黑暗。她生活于斯,周旋于斯的这个光亮的内圈,火车在奔驰,工厂生产出机制产品,植物和动物都在科学与知识的阳光下生长。突然,这个圈子在她眼里就像弧光灯下的区域,飞蛾和孩子们都在炫目的灯光庇护下玩耍。因为他们是在灯光下,根本不知道还有什么黑暗。但是,她可以隐约看见黑暗的移动,就在这范围之外。她看到在黑暗中闪光的野兽眼睛,它们望着营火边的虚荣和睡觉的人。她也感觉到了营地里不可思议的愚蠢的虚夸——“在我们的光亮和我们的秩序之外什么也没有。”
他们总是脸朝内对着将灭的启蒙意识之火——包括太阳星星,造物主和正义的体系,不顾周围旋转着的大片黑暗已经半隐半现地潜伏在边缘地带。而且,甚至没人敢扔一根燃烧着的木头到黑暗中去。因为,他要是这么做了,就会被其他人笑死。他们会大喊:“蠢东西,反社会的无赖,你为什么要弄鬼弄怪来打扰我们?没有黑暗。我们活动、生存于光亮之下,有了知识的永恒之光,我们就组成并包含了最内层的核心和知识的结果。蠢东西,无赖,你怎么敢以黑暗来贬低我们?”然而,黑暗就在旁边围着转,还有野兽灰暗的身影。另外还有的是天使漆黑的身影。
这光亮把更为熟悉的野兽身影隔在外面,也把天使们隔在外面。有一些曾经看过黑暗的人见到其中布满了一簇簇的鬣狗毛和狼毛。还有一些放弃了光亮底下的虚荣的人,被自己的自负折磨得要死的人,他们看到了狼和鬣狗眼中的闪亮。这是天使的剑光在门口闪亮,要进来,黑暗中的天使是高傲的可怕的不可否认的,犹如闪亮的毒牙。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厄秀拉二十二岁了。复活节快到了,厄秀拉又收到了斯克里宾斯基的信。他从南非给她写过一、两次信,那是在战争期间他刚到那儿的头几个月写的。以后又不时给她寄一张明信片,间隔的时间就更长了。他当了中尉,留在非洲。厄秀拉已经有两年多没有收到他的信了。
厄秀拉常常想起他。他就像那微微透亮的黎明,一个昏暗的长日之前呈现出黄色光芒的黎明。对他的回忆犹如想起早晨的初晖。这里就是白天的一片灰暗。啊,要是他一直是她身边真真切切的实体,她就看得见阳光,不受这些劳累、伤害,也不会陷入糟糕的白天。他会是她的天使。他控制着阳光,现在还控制着。他可以朝她打开自由和欢乐之门。不仅如此,要是他一直是她身边真切的实体,他就会是她投身于无边无际的幸福海洋之门。无穷无尽和自由是她心灵之乐园。啊,他会向她打开广阔的区域,打开辽阔无垠的自我实现、永远欢快的空间。她相信这一点,相信自己还爱着他。这爱是闪闪发亮的、完整无缺的,可以追溯到源头。眼前的事情看来都不成功,她就对自己说:“我以前是钟情于他的。”好像他一走,她生命中最鲜艳的花朵就枯萎了。现在她又收到了他的信。最主要的感受就是痛苦,再也没有愉快和本能的高兴了。可是这随了她的愿。她已决意把自己和他连在一起了。过去她梦幻中的兴奋被激起、唤醒了。他要来了,那个能用奇妙的嘴唇跨过空间把吻颤巍巍地送过来的男人要来了。他是回到她身边来吗?她不相信。
“我亲爱的厄秀拉:
我回到英国了,住几个月又要出去,这次是去印度。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我们在一起的日子。我还存着你的小照。从那时到现在你的样子一定变了,已经将近六年了。我已足足长了六岁——自从在考塞西认识你以后我经历了另一种生活。我不知道你想不想见我。下星期我要到德比,也会到诺丁汉,我们可以一起去喝茶。请你告诉我,好吗?我等着你的回音。安东?斯克里宾斯基这封信是厄秀拉从学院大厅的信件架上拿到的。她一边穿过大厅到卫生间一边拆开了信。周围的一切似乎都消失了,她站在空旷中。到哪儿去才能独处一隅?她跑上楼,穿过一条幽静小道进了参考书阅览室。她抓起一本书,坐下来,回味着这封信。心儿怦怦地跳,四肢在哆嗦。好像在梦中,她听到学院的一下钟声,很奇怪,接着又一声。下第一节课了。她急忙抓起一本笔记本,写了起来。
亲爱的安东:
我还保存着那只戒指。我很高兴再见到你。你可以来学院找我,或者我到城里的某个地方会你。请告诉我。你的诚挚的朋友……
她用颤抖的声音问图书馆员,能不能给她一个信封。馆员是她的朋友。她把信封上,写了收信人地址,连帽子也没有戴,就跑出去寄信。信丢进了邮筒,周围成了一个无边无际、暗淡寂静的世界了。她信步走回学院,走回她那黎明的第一线曙光似的世界。斯克里宾斯基是信寄出后第二个星期的一天下午来的。在这之前,她每天早晨一到学校就急忙跑到信件架去,课间也去看。有几次,她遮遮掩掩,飞快地把斯克里宾斯基的信从显眼的地方抓去,紧握在手里,快步走出大厅。她把信拿到植物学实验室去看,那儿有一个角落总是留给她的。几封信之后,他就要来了。他约定的是星期五下午。厄秀拉对着显微镜兴奋地工作着,只能集中一半的注意力,却干得仔细、迅速。承物玻璃片上放的是当天从伦敦送来的一种特殊的东西,教授还为此大惊小怪,兴奋不已。她把目光集中在显微镜的视场,看到这植—动物模模糊糊地摆在无边的亮光下,同时,她正为几天以前与弗兰克斯通博士的谈话而烦恼。弗兰克斯通博士是学院里的一位物理学女博士。
“不,真的,”弗兰克斯通博士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把一些特殊的奥秘归因于生命。你知道吗?我们对生命的了解甚至还不如对电的了解。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说生命特殊的理由。说它是不同的种类,说它与宇宙中的其他任何事物都截然不同,你认为是这样吗?生命存在于复杂的物理活动和化学活动之中,是由我们在自然科学中已知的活动的相同次序排列组成的,难道没有这种可能吗?我不明白,真的,为什么我们要想象生命有一种特殊的活动次序,而且只有生命……”谈话是以一种不肯定、不明确、若有所思的口气结束的。但是,目的,目的是什么?电没有灵魂,光和热没有灵魂。她自己是非人的力量吗?还是像其中的一个,是几种力的组合?厄秀拉一动不动地望着显微镜视场里的单细胞影子。它是活的。厄秀拉看见它动了,看见它纤毛活动的一点亮,看见它滑过光亮的视场时细胞核发出的微光。那么,什么是它的意愿?如果它是物理化学几种力的组合,是什么使这些力成为一体?又是为了什么目的要成为一体?
这些无数的物理化学的活动为什么要成节状模模糊糊地在她的显微镜下移动?使它们成节状并创造了她看到的这一物体的意愿是什么?它的意图又是什么?成为它自己?它的目的只是机械的、局限于它自身的吗?它的目的是成为它自己。可什么是自己?在她的脑子里,世界的强烈光线突然奇怪地闪烁着,就像显微镜下生物的细胞核。突然,她一下子进入了耀眼的知识之光。她不可能完全了解这是什么。她只是知道这不是有限的机械能量,也不是纯粹的自我保存、自作主张的目的。这是一个完美的结果、无限的形体。自我是基于无限的一体。成为自我是无限的一个至高的辉煌胜利。厄秀拉坐在那儿出神地望着显微镜,心神不定。她的脑子没空,忙着想这个新世界。斯克里宾斯基在新世界等着她——他会等着她的。她现在还不能走,因为她的脑子正忙着。她很快就要走的。一阵寂静攫住她,好像要昏死过去。远处,走廊下,传来了五点钟的报时声。她要走了。可是她还坐着不动。其他学生都把凳子往后一推,把显微镜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