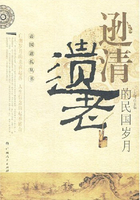第十章扩大的圈子 (1)
作为家中的长女,厄秀拉感到自己肩上的负担很沉重。在十一岁时她就得带着戈珍、特丽萨和凯瑟琳一起去上学了。弟弟威廉是个可爱、羸弱的孩子,才三岁,只好待在家中,大家总管他叫比利,免得同父亲的名字混淆(父亲的正式名字是威廉?布朗温。)。另一个女婴叫卡桑德拉。孩子们这时上的学校是离玛斯不远的教会学校。布朗温太太以为这里离家近,学校也不大,把孩子们送去那儿很安全。村子里的男孩子们给她们三姐妹都起了外号,管厄秀拉叫“厄脱拉”,管戈珍叫“古拉纳”(优秀跑步者),管特丽萨叫“蒂波特”(茶壶)。戈珍和厄秀拉是一对伙伴。
这位二姑娘身材颀长但不爱运动,总在没完没了地幻想什么,不想同现实有什么联系。她不是为现实而生的,她为自己的幻想而生。厄秀拉才是为现实而生的。所以戈珍把一切现实的东西都给了姐姐,对她表示信任。厄秀拉对她的伙伴妹妹很温存。想让戈珍有责任心可是白费心机。她就像海里的一条鱼在游荡,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之中,因为与他人不同而沾沾自喜。别人对她来说无所谓。她就是相信厄秀拉。这位长女要对其他的弟妹们负责,这种责任感令她苦恼。特别是那个身强力壮目光大胆的特丽萨,她特爱打架。“厄秀拉,比利?皮林斯拽我的头发。”“你说他什么来着?”“我什么也没说。”
于是布朗温家的女孩子就同那家闹一通儿。“不许你再拉我的头发,比利?皮林斯。”特丽萨跟姐妹们在一起,冲那长着雀斑的红发男孩说话时态度很傲慢。“我为什么不能?”比利?皮林斯反问。“就是不许,”特丽萨说。“你来这儿好了,蒂波特,看我敢不敢。”
特丽萨刚走开,比利?皮林斯就拉了一下她的一缕黑色鬈发,她气得扑向他。随后厄秀拉、戈珍和小凯蒂跑来助战。紧接着菲利浦斯家的克莱姆、瓦特和艾迪?安索尼也来参战。好一场对打。布朗温家的女孩子长得很壮,比许多男孩都壮实。如果不是穿着围裙,留着长发,她们会轻易取胜的。回家时,她们的头发被扯乱了,围裙也被扯破了。菲利浦家的男孩子撕了布朗温家女孩子的裙子,他们可高兴了。然后爆发了一场吵闹。布朗温太太决不能容忍这种事,不,决不容忍。她生来就自尊、冷酷,这一下全露了出来。牧师到学校来上课了。“很不幸,考塞西的男孩子对考塞西的女孩子一点都不礼貌。
说真实的吧,什么样的男孩子才打女孩子、踢打人家、撕人家的围裙呢?这种孩子该重重地受罚,该叫他胆小鬼,男孩子都是胆小鬼。”皮林斯兄弟心里有些惭愧但很生气,而布朗温家的女儿们特别是特丽萨却自以为很有美德。这场斗争一直进行着,其间也出现不寻常的和睦。和睦时厄秀拉就成了克莱姆?菲利浦斯的情人,戈珍是瓦特的情人,特丽萨是比利的情人,甚至小凯蒂也成了艾迪?安索尼的情人。他们结成了亲密的联盟。一有机会,布朗温家这群孩子和菲利浦斯家的孩子就往一块凑。可是无论是厄秀拉还是戈珍都不会同菲利浦斯家的男孩儿有什么真的亲昵之情。这种同盟和这种结交情人对她们来说不过是过家家儿罢了。布朗温太太又生气了。
“厄秀拉,告诉你,我可不许你跟那些男孩子一块儿压马路。现在你就停下来,其余的人也就不干了。”厄秀拉真不想当布朗温家的孩子头儿。她从来不能以个人身份露面,她总是厄秀拉—戈珍—特丽萨—凯瑟琳,后来又多了一个比利。当然她也不需要同菲利浦斯家的孩子在一起。她跟他们谈不来。后来,布朗温—皮林斯联盟终归破裂了,主要因为布朗温家过分傲气。布朗温家富有。他们在玛斯庄很吃得开。学校的教师对布朗温家的女孩子十分尊敬,牧师与她们平等相处。她们傲气十足,昂着头对什么都不屑一顾。“你才不那么高尚呢,厄脱拉?布朗温,你是一只难看的杯子,”克莱姆?菲利浦斯红着脸说。
“可我比你强多了,”厄秀拉回敬他。“瞧你那样儿,还比我强呢,难看的杯子,厄脱拉?布朗温。”他讽刺她,试图让别人都跟她作对。她真讨厌他们嘲弄她,对菲利浦斯家的人她冷眼相待。厄秀拉在家中很倨傲。布朗温家的女儿们都有一种盲目的自尊,举止上甚至带点贵族气。由于出身与教养的关系,她们只顾我行我素,不睬别人如何评价。厄秀拉从来就不认为别人会看不起她。她觉得不管谁认识她,懂得这一点就够了,她觉得世上的人都像她一样。如果她被迫对谁有成见她就会痛苦,永远也不会饶恕那个人。她这种人令许多小人发疯。几辈人中,布朗温家都会遇上想拆他们的台、损害他家形象的人。奇怪的是,家中的母亲总会意识到将要发生的事,总会提早告诫孩子们应变。
厄秀拉十二岁时,普通学校和学校中同村儿的伙伴那股下作气开始影响她了,为此安娜把她和戈珍一起送到诺丁汉的小学去读书。从此厄秀拉感到如释重负。她一直努力逃脱生活中渺小的环境——小人的嫉妒,小人的辨别能力和小人的下作气。菲利浦斯家比她家穷,人格下作,他们使了一些小手腕儿占些小便宜,这真让她心里难受。她想与自己同等的人在一起——当然不能埋没了自己。她的确希望克莱姆?菲利浦斯成为与她平等的人,可是不知怎么回事,不知是由于痛苦的命运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当他真正同她在一起时,他就令她头疼,她真想敲打着自己的脑门逃走。随后她发现逃脱是很容易的。一是脱离这里的整个环境,二是去诺丁汉上学,离开这座小小的学校、学校里思想贫乏的教师以及菲利蒲斯家的人。她曾经想过要爱他们,可他们不成器,对此她决不能原谅。她本能地惧怕那些小人,就像鹿惧怕狗一样,因为她这人很盲目,她不会算计别人。她偏偏认为人人都该像她一样。
她是以她自家人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的:父亲、母亲、外婆和舅舅们的标准。她敬爱的父亲非常朴实,可他强壮、黑暗的灵魂却扎根于深层,令她着迷又令她恐惧;她的母亲对金钱、习俗一概不往心里去,不知道什么叫担忧,对世界漠然以待,跟谁也不发生联系,孤芳自赏;她的外婆来自遥远的地方,心里装着远大的世界。由此可见,如果谁要同厄秀拉交朋友,他首先要符合这些标准才行。所以,她十二岁时,她就要冲破考塞西这狭窄的地方,这里的人都不够大气。考塞西之外,有广漠的世界,有她喜爱的强有力、真实而骄傲的人们。
去诺丁汉上学要坐火车,她必须早晨七点四十五分就离开家,下午五点半才能回来。她很高兴这样。家中的房子太小,挤满了人,满屋人动来动去,像暴风雨一样令人无法躲避。她讨厌让别人管着。家里确实乱极了。孩子们身体健壮,好骚动,做母亲的只要他们健康就行了,别的不管。对厄秀拉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变成了一场恶梦。后来,她看到鲁本斯(鲁本斯(1577—1640),法兰德斯派著名画家。)的一幅画,画上是一群裸体儿童,画名儿叫“丰饶”,看得她直发颤,只觉得这世界太可怕。她深知生活在一群孩子中,在丰饶的火热与混乱中,是什么滋味儿。她跟妈妈过不去,强烈地憎恨她,她在努力寻找某种精神上高贵的东西。
天气不好时,家里就成了精神病院。孩子们在雨中一会儿冲进来一会儿冲出去,跑到紫杉树下的水坑中去玩,在厨房的石板地上窜来窜去,气得清扫女工又是抱怨又是骂;孩子们蜂拥到沙发上乱闹,对着前厅中的钢琴又踢又踹,敲得钢琴发出“嗡嗡”的蜂鸣声;他们在炉前地毯上打滚儿,四脚朝天地躺着;两人扯住翻开一半的书把书扯成两半;他们恶魔般地偷偷上楼来找厄秀拉,在卧室门外窃窃私语,扒着门神秘地叫喊“厄秀拉!厄秀拉!”他们知道她是把自己锁起来读书呢。真没办法。关闭的门激起了他们的神秘感,她不得不打开门以打消他们的好奇心。可孩子们还是睁大眼睛缠着她激动地问些问题。母亲在孩子们中间手舞足蹈地叫:“闹闹好,总比生病强。”可成长起来的女孩子们都一个个地感到痛苦起来。厄秀拉现在这个年龄正是该放弃安徒生和格林童话去读《国王的田园诗》(英国诗人阿尔弗莱德?坦尼生(1809—1892)以英国古代传奇《亚瑟王和圆桌骑士》为题材写的诗集。)和其他浪漫爱情故事的时候。
“美丽的埃琳娜,可爱的埃琳娜,是阿斯特拉特城堡中的百合女,她身居高塔中的闺房里,守着兰斯洛特神圣的盾牌。”(《国王的田园诗》中的诗句,见前注。骑士兰斯洛特冒险来到城堡,城堡中的少女埃琳娜爱上了他,演出了一场悲剧。)她多么喜欢这样的诗句啊!她在卧室中凭窗眺望着城堡似的教堂,黑色的散发披在肩上,热情的脸上露出心旷神怡的表情,她觉得骑士兰斯洛特就要骑马而来了,他会向她招手,他身上腥红色的大披风就在上闪动。而她,哦,她,她会像那个埃琳娜一样孤独地高居在城堡中,擦亮那可怕的盾牌,给它织一个套儿,织得又精又细,默默地等他。就在这时,楼梯上传来脚步声,门外有人小声说话,然后门闩响了,比利激动地叫道:“锁着呢,门锁着呢。”接着孩子们就敲门,急切地叫:
“厄秀拉!我们的厄秀拉?唉,我们的厄秀拉?”没有回答。
“厄秀拉!我们的厄秀拉?”他们喊了起来,可还是没有回答。“妈妈,她不答应。”有人叫,“她死了。”
“滚,我才没死呢。你们想干什么?”厄秀拉生气地叫道。“开门,我们的厄秀拉。”抱怨声一片。一切全完了。她必须开门。她听到楼下的女人冲洗厨房地板时拉着水桶在石板地上蹭出的声音,孩子们在卧室中走来走去,问她:“你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把门锁上?”后来她发现了礼拜室的钥匙,于是她就到那儿去,捧着书坐在麻袋上。又一场梦开始了。她是老国王的独生女,会魔术。一天又一天,日复一日,她像幽灵一样默默地在古老的大厦中徘徊,或是在静静的游廊中漫游。可是悲哀向她袭来了:她的头发是黑色的。可她必须生着黄头发才行,必须是白皮肤。她因为自己长着黑发痛苦极了。
没关系,长大以后她可以染一下头发,或者在阳光下把头发颜色晒浅,直到它变黄。她还可以戴一顶威尼斯的白色针织帽。她在游廊上走来走去,蜥蜴舒适地爬在石头上,当她的身影笼罩住它们时它们也不动一下。寂静中,她听到了泉水在汩汩喷涌,玫瑰吐着浓郁的芬芳,艳丽的花朵一动也不动。她就这样怀着对美的憧憬徜徉着,穿过水池和池中的天鹅,到高雅的公园中去,在那儿,橡树下躺着一只花斑雌鹿,它身边蜷着它棕色的幼仔。啊,这只鹿是她的熟人了。它会跟她聊天,因为她是一位魔术师,它会对她讲故事,就像阳光在说话一样。有一天,她像往常一样离开礼拜室,门没锁。孩子们进屋来了,凯蒂划破了手指头大叫起来,比利把凿子砍出了一个大口子,毁了不少东西。屋里一片乱七八糟。母亲发了一通火就没事了。厄秀拉把门锁好,觉得一切都过去了。后来父亲皱着眉头问:“谁开的门?”他生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