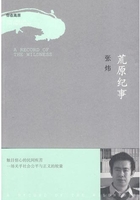第八章孩子 (2)
这孩子厌恶母亲那表面上的权威,她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他有时也会给她一些较残酷的打击。他让她在教堂里玩耍,他自己弹琴。她摆弄摆弄小凳子,翻翻唱诗本,或者玩玩靠垫儿。就像一只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一连好几个星期都是这样过的。可打杂女工渐渐生起气来,竟敢顶撞威尔,有一天竟像个妖怪一样冲他大闹起来。他在她面前退缩了,恨不得扭断她的脖子。他气冲冲地回到家中,对厄秀拉发起火来:“怎么回事,你这个讨厌的小猴子,你去教堂干吗要把什么都弄个乱七八糟?”他的声音很严厉,很刻毒,对孩子的态度很粗鲁。厄秀拉又气又怕,避开了他。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可怕?母亲反倒很平静,态度可是真好,问:“她干了些什么?”“干什么?她再也别到教堂去了,抓挠东西,弄了一地,弄坏了一些。”妻子慢慢转转眼睛,垂下眼皮说:
“她都弄坏了什么呢?”他不知道。“威肯森太太刚说了我一顿,说了一串儿她干的好事。”听他轻蔑气恼地提到“她”,厄秀拉胆小了。“让威肯森太太来这儿说说她都干了些什么,”安娜说,“我倒要听听。”母亲又说:“不是孩子干的事让你生气,是你不堪忍受听那老女人对你说这事。你让她骂了又不敢还嘴,就回来撒气来了。”他不说话了。
厄秀拉知道爸爸是错的。在外面,他做的事是错的。这孩子已经感到这个没人情味的世界是冷酷的,在这个世界里妈妈做的事是对路的。但她的心仍然为父亲呼喊,在父亲那黑暗的内心世界里,他是正确的。可他正生气,阴郁,粗暴,又沉默不语了。这孩子沉醉在生活中,安静,总有乐事儿。她对事情不注意,从不注意事情有什么变化和改观。今天她会在草丛中发现雏菊,明天她会发现白苹果花儿落了一地,她会在落花中跑来跑去找乐儿。当鸟儿来叼食樱桃时,爸爸就会从树上摘下樱桃扔下来,她周围,园子里尽是樱桃了,满地都是丰收果。外界的东西每天都存在着,可她记不得都有过些什么或将有些什么。
她总是她自己,外部世界不过是偶然现象罢了。甚至她母亲对她来说也是个偶然,她碰巧要忍受她。在这孩子的意识中,只有父亲才占有一个永恒的位置。当他回来时,她仍记得他是怎样出去的。当他出门以后,她懂得她必须等他回家来。相反,母亲出门回来后,不过是又出现了一次,她无法将母亲出门时的情景与现在的母亲联系起来。父亲的来去是这孩子牢记的一件事。他一回来,她心中就有什么东西被唤醒,那是一种渴望。她知道他什么时候心里不满,什么时候恼火或疲劳,她为此感到不安。当他在屋里时,这孩子就会感到满足,感到温暖,就像阳光下的一只小动物一样满足。当他不在时,她就会感到迷惘,感到被人遗忘了。
当他咒骂她时,她甚至更注意她,反倒不那么注意自己了。他是她的力量,她觉得他是自己的另一半。厄秀拉三岁那年,又一个小女儿出生了。从此戈珍和厄秀拉就常在一起了。戈珍是个安静的孩子,她可以一个人一玩就是几个小时,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她长着棕色的头发,皮肤很白。这孩子安静得出奇,几乎不好动。但她有着不可驯服的意志,一经拿定主意,就无法改变。一开始她跟随着厄秀拉,可她又挺有个性,所以,她们俩玩在一起是件奇怪的事。她们两个姐妹就像两个小动物,在一起玩耍,但谁也不真正注意谁。戈珍是妈妈的宠儿,但现在妈妈总宠爱着新生儿。这么多生命都依靠他了,真是个负担,这位年轻的小伙子都被压垮了。
他工作间里的工作完全靠意志勉强干,他的热情是用在教堂上的。他还有三个孩子要照顾,可这时他的身体又不大健康。因此他在家里很凶恶,爱发脾气,像个瘟神一样。他一这样,安娜就让他去做木雕或者去教堂。他和厄秀拉结成了奇怪的联盟。他们意识到了对方的存在,他知道这孩子总是站在他一边,可他主观上就不太看重这一点。她总支持他,他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不管怎么说,他的生命依靠她,甚至当她还是个小孩子时,他就依靠她的支持和赞同。安娜仍然继续沉醉在做母亲的热情中,她那么忙,杂务缠身,可总是沉醉在做母亲的热情之中。她似乎生活在她自己狂热的多产多育中,似乎照耀她的是热带的阳光。她脸上放着光,她的目光中溢满了忧郁,棕色的秀发松散地盖住耳朵,看上去很是丰盈旺盛。
没有责任和义务感令她不安。外界和社会生活对她来说真是一钱不值。他呢,二十六岁时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爸爸了,他的老婆实际上像田野里最经得摔打的花儿一样生活着,他就这样被责任重压着,拖拉着。就在这时厄秀拉力求和他在一起。她是同他一条心的,甚至当她还是个四岁的孩子时,当他发脾气、大喊大叫让全家人都生气时,她就跟他一条心。他大喊大叫让她吃了不少苦头,不过,大喊大叫的并不是真正的他。她想让这喊叫结束,她要恢复与他正常的联系。当他失意的时候,这孩子的心就回应着他某种需求的呼唤,这种回应是盲目的。她的心追随着他,似乎他与她之间有联系,似乎有一种爱她不能表达。她的心,她的爱,执著地追随着他。可她感到自己渺小,感到自己能力不足,她的心为这种孩子气的感觉所暗淡。她什么也做不了,她能力不足。她无法对他变得重要起来,从一开始意识到这一点她就心灰意冷了。
但她仍然像一根颤抖着的针直指向他。她关注他,被他的存在所唤醒,她全部的生命都被他驱使着。另一方面,她与母亲反目。她的父亲是清晨,唤醒了她的意识。如果不是因为她父亲,她会像其它几个孩子一样:戈珍、特丽萨及凯瑟琳,与鲜花、昆虫和玩具为伍,失去注意的具体目标,失去自己的存在。可她的父亲跟她太近了,从孩提时代起,他握紧她的那双手和他胸脯的力量就唤醒了她,让她几乎感到痛苦。她睁大了眼睛,但看不见,在她还不知怎样去看以前她就醒了,她醒得太早了,她父亲对她的呼唤也来得太早了。当她还是个小孩子时,父亲紧紧地把她拥在胸前,他那颗强大的心脏的跳动唤醒了她那仍处于沉睡中的心。他抱紧她,用身体紧贴着她,要从她这里获得爱、获得自己的完整,以此来唤醒她。他像一块磁铁吸引着她。她的回应挣扎着,恍惚获得了生命。在农村里,孩子们穿得不算讲究。小时候,厄秀拉身穿厚厚的红衣服,外面罩一件宽松的蓝袍子,一条红围巾扎在脑后,在木桩子堆里“嗒嗒”走来走去。她就这样追随着父亲,追到花园。家里人起得很早。他早晨六点钟就出去到花园里松土,八点半就上班。厄秀拉常常跟他在花园里玩,离他不远。
有一年复活节,她帮助他种土豆,这还是她头一回帮他干活呢。她的记忆里留下了这样一幅图画,这是她最早的记忆。一大早儿他们就出门了,外面正刮着冷风。他穿一条旧裤子,裤腿塞到靴子里。他没穿外衣,也没穿坎肩儿,只穿着衬衫,袖子在风中飘舞着。他红润的脸上表情专注,他似乎仍在睡眠中。一干起活儿来,他对别的事情就不管不问。一个瘦长的男子,看上去还是个年轻小伙子,丰厚的嘴唇上方留着一道黑髭,漂亮的棕色头发飘在额前,他就这样独自在黎明的微熹中干着农活。他那孤独的身影像魔咒一样吸引着这孩子。墨绿色的田野上袭来一阵寒风。厄秀拉跑过来看他把木桩插进松好的土中,跨过去在另一边也插上木桩,然后绷紧木桩之间的线。
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亮闪闪的铁锹扔了过来,在新翻出的松土上砍出了一道小沟。他把铁锹插进地里,伸直了腰。“想帮帮我吗?”他问。她的双目从毛织的小帽子下看着他。“好吧,”他说,“你可以替我把土豆放进去。你瞧,这样,芽儿直着摆,间隔这么大,看到了吗?”他迅速弯腰,把土豆摆进松软的沟里,这些小土豆一个个等距离地躺在冰冷的土地里,看上去怪可怜的。他递给她一只篮子盛土豆,然后他自己跨到另一头。她看着他弯着腰一边栽土豆一边朝她这边挪过来。她感到激动、新奇。她埋下一只土豆,摆了又摆,让它躺得自在些。有的芽子断了,这让她害怕了。责任感让她激动,像一根绳子拴住了她。她忍不住要看那条埋在翻过的新土下的线绳,心里有些怕。她的父亲弯着腰过来了,越来越近了。她怕极了,赶紧把土豆埋进土里。
他走近了。“别摆得太近了。”他说着弯下腰去拣出几个土豆,又把其余的重新摆好。她站在一旁,感到小孩子的无能为力,很是害怕。他是那样专注、自信,她也像他那样,可她做不来。她站在一旁看着,她的小蓝袍子在风中飘舞着,红围巾的一头也被风吹得呼啦啦响。他一直朝前动着,挖一锹,种下一只土豆,不停地干着。他只顾干活,不怎么注意她。他自己有一个世界。那里没有她。她在他的世界里站立着束手无策。他还在继续干他的活儿。她知道她帮不上忙。她感到有点失望,终于转身离开了他,她跑着离开了园子,尽快地跑,为的是忘记他和他的农活儿。
他失去了她的身影:红围巾里的小脸,飘忽的蓝袍儿。她跑到一处草丛和石缝间潺潺淌水的地方,她喜欢这里。他走过来对她说:“你帮不了什么忙。”这孩子无言地看着他。她的心因为失望而变得沉重,她沉默不语,可怜巴巴的。可他没注意,仍像原先一样。她愈是失望愈是玩耍。她怕干活,因为她不能像他一样干。她意识到了他们之间的隔阂。她知道她是无力的,大人们那副经心干活的样子对她来说是个迷。他会毁灭性地闯入孩子那敏感的心界。她的母亲宽宏大量,无所用心。孩子们整天地玩耍着。厄秀拉无忧无虑,如果她看到园子那边的篱笆上冒出了花蕾,如果她想用这些绿里带红的小花蕾充作面包和奶酪吃,想采来到茶会上玩,她就走过去采撷。
可是,也许就在第二天,她父亲对她翻了脸,大声吼叫,她就会失魂落魄:“我刚下了种子,谁在上面乱踩乱跳来着?我知道是你,小讨厌!你不会到别处走,干吗非在我下种的地方踩?你就是这样,不长心眼儿,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当他看到地上曲曲弯弯、深深浅浅的小脚印时,他大为震惊。这孩子更为惊恐,她那小小的心灵受到伤害了。这些脚印怎么会在那儿呀?她并未想过要留下什么脚印。她站在那里,惶恐不安起来。她的灵魂和意识似乎都离她去了。她变成了与世隔绝、毫无感知的小动物,她的灵魂变僵硬了,毫无反应。像冰霜一样,她不再忧虑。一看到她那张脸上清高、故作坦然的表情,他就气不打一处来。他想毁了她。
“我要毁掉你这倔犟的脸,”他咬紧牙关、挥着拳头说。这孩子一点也不改悔,漠然、一脸的冷淡表情,似乎除了她自己以外再也没别的东西存在。但是,她内心幽远的地方,啜泣撕碎了她的灵魂。他一走,她就会爬到前厅的沙发下面,静静地蜷缩着,在儿童那寂静、隐蔽的神秘世界中蜷缩着。一个小时左右以后,她爬出来,毫无精神地去玩。她要忘却,她把自己的灵魂与记忆切断,这样一来,痛苦和屈辱就变得不真实了。她只是要坚持自己的权力,现在世界上没别的什么,只有她自己。所以,很快她就开始相信外界对她有歹意。从很小的时候,她就感到,她可敬的父亲也是有歹意的人之一。于是小小年纪的她就学会了抵抗和抗拒外界的一切,她的心变硬了,生命变僵了。
对她自己的所作所为,她从来没有后悔过,而对于那些让她认错儿的人她从来都不原谅。如果他对她说:“厄秀拉,你为什么要在我细心整出的苗床上乱踩?”这就说到了她的疼处,她会想办法对付他的。她总被外界事物的不真实折磨着。土地就是给人走的嘛,她为什么要躲躲闪闪,就因为那块地方叫什么种床?土地就是给人走路用的,她的本能让她这么认为。他要是欺侮她,她就强硬。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只生活在自己那与世隔绝的世界中。她长大到六、七岁时,她与父亲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了,可总有破裂的危险。她总是犯倔脾气,躲入自己那与世隔绝的世界中去。这让他气得咬牙切齿,因为他仍需要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