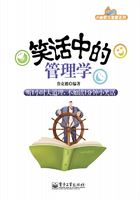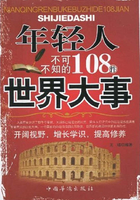第二章18
母亲靠着墙抬起头来,倾听他们低声谈论。达吉扬娜站起来向四周瞧了瞧,又坐下来。她那双绿色的眼睛很冷漠,脸上带着不高兴的表情,显然是瞧不起两个高谈阔论的男人。
“您可能吃过不少苦吧!”她忽然朝母亲转过身来,问道。
“是的。”母亲说。
“您讲得真精彩,我心里早就希望能听到您这种谈话。我心想,天哪!您讲的那些人可真好,那样的生活可真好,我哪怕是能够隔着门缝瞧上一眼,看看他们的生活也好。我们过的算是什么日子啊!简直像绵羊!就如我吧,认字,也会看书,想过很多问题,有时还会想得失眠。可有什么用呢?不想吧,这日子过得可真是冤枉,想也是白想。”
她说话时眼角挂着苦笑,有时说着说着就会像断了线似的突然停止。两个男人沉默不语。风悄悄吹打着玻璃窗,屋顶上的干草在沙沙地响着,烟囱里发出轻轻的嗡嗡声,狗在叫。雨点时不时敲几下窗户。灯火忽儿变暗,可不久又亮起来,也不再跳动。
“听完你这些话,我才明白人为什么要活着!说来也奇怪,听完你一席话,我觉得这些道理我都明白啊!可是从前我从未听人讲过这些,也没有想过这些事情……”
“达吉扬娜,该吃点东西了,熄掉灯!”
斯杰潘沉着脸慢慢地说,“人家看到了会怀疑我们家为什么一直点着灯。我们倒不要紧,可是我担心对客人不好……”
达吉扬娜站起身来走到炉灶后面去了。
“是啊!”彼得笑了笑,低声说,“现在可得小心点,老兄!等报纸散发出去……”
“我自己倒不要紧。就算抓我去也没什么妨碍!”
女主人走到桌前,说:
“走开点……”
斯杰潘站起身离开餐桌,看着妻子铺好桌布。他苦苦地笑了笑,说:
“我们这种人真贱,五戈比一堆,每堆还得一百人才有人买……”
母亲突然觉得他很可怜,就越发喜欢他了。说了那些话之后,她感觉轻松了许多,也摆脱了这一天压在她心头的恶劣心情。她自己心情舒服了,也希望大家都精神舒畅。
“主人呀,您这些话可不对啦!”她说,“那些吸血鬼贬低您,瞧不起您,您就不应该同意嘛。您自己应该看重自己,从内心看重自己,这样做不是为了敌人,而是为了朋友……”
“我们有什么朋友?”斯杰潘低声感叹道,“连一片面包都抢……”
“我认为民众是有朋友的……”
“有朋友,不过不在这里,就这样!”斯杰潘沉思地说。
“那你们应当在附近交朋友嘛。”
斯杰潘思考片刻,低声说:
“嗯,这话也对……”
“请坐下吃饭吧!”达吉扬娜说。
听了母亲刚才那些话,彼得更显得压抑,不知该如何说,但吃晚饭的时候他又活跃起来,急忙说:
“大妈,为了避开耳目,您得早些离开这里。您不要直接回城去,只要乘驿车再向前走一站路……”
“这何必呢?我可以赶车送她。”斯杰潘说。
“不行!万一有人问你,她是不是在你家住过?你就说住过。现在到哪里去了?我把她送走了!啊哈,是你送走的,那你就准备去做牢吧!明白了吗?我们为什么要急着去坐牢哟?啥事都有个先来后到,俗话说得好,时间一到,连皇上也难免死掉。这事简单,她住了一夜,天亮就雇马车走了!谁家没有借宿的人?这村里本来就人来人往的……”
“彼得,你怎么现在会这么胆小?”达吉扬娜嘲笑道。
“什么事都要学会啊,嫂子!”彼得拍了拍膝盖,高声说,“既要学会胆小,又必须学会胆大呢!还记得吧,因为这些报纸,地方自治局局长把瓦加诺夫整得死去活来。现在,你如果给瓦加诺夫一笔钱,劝他看一本书,他也不会干啦!你就信我好了,大妈,我一向办事机灵,这人人都知道的。这些书报传单,你有多少,我都能保证给您散发出去!当然啦,我们这里的农民认字不多,胆子小,可是这世道逼得他们必须睁开眼睛瞧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书给了他们最好的回答:就是这么一回事,仔细想想就明白了。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不识字的人反而比识字的人更明白道理。
特别是那些无所事事的人,虽识字,却不明白道理!这一带的乡村我都走遍了,见得多,情况还算好。但想要不碰壁,就必须动脑子,还得非常机灵。官府现在知道了,知道农民也不好惹。农民见了当官的很少笑,态度冷淡,总之,想不听官府的!前些天在斯莫里亚科沃,也就是离这不远的一个小村庄,来了几个征税的官员,农民给逼急了,拿起棍子要打人!县警察局长凶相毕露地说:‘你们这些狗娘养的!你们竟敢反对皇上啊!’当地有个叫斯皮瓦金的农民,对警察局长说:‘你和皇上都滚蛋!连最后一件衣服也要扒走了,还说什么皇上!……’您看,大妈,事情都到了这个地步。当然,那个斯皮瓦金被抓去坐牢,可人们忘不了他说的话,连小孩子也知道。这些话现在四方流传呢!”
他没吃东西,只顾低声讲着,那双黑眼睛活泼地闪动着,露出狡黠的神色,他好像从钱袋里倒钱币似的,毫无保留地把他观察到农民的无数事实匆忙地告诉母亲。
斯杰潘不断提醒他:
“你快吃点饭吧……”
彼得拿起一片面包和一个勺子,可又像爱歌唱的金丝鸟似的接着讲。吃完晚饭,他立即站起身来,说:
“喂,我该回家了!”
他走到母亲面前,握住她的手,不停地点着头说:
“再见吧,大妈!也许我们以后没有见面的机会,我得告诉你,这里一切都好!能遇到您,听您的讲话,这真是幸运!您的皮箱除了印刷品还有什么东西?还有一条羊毛头巾吧?妙极了,是羊毛头巾。斯杰潘,你要记住!他现在就去为您拿皮箱!走吧,斯杰潘!再见!祝您一切都好!……”
他们走后,屋里立刻静下来,只听得见蟑螂发出沙沙的声音。寒风吹打着屋顶,烟囱的风档发出咚咚声,细雨单调地敲着窗户。达吉扬娜从炕上和板床上取下几件衣服,铺在长凳上供母亲安歇。
“他真活跃!”母亲说。
女主人皱着眉看了她一眼,答道:
“他是叫得响,但没有人听他的。”
“您男人如何?”母亲问。
“他还好。是个好男人,也不喝酒,我们过得挺和谐。还算好!只是性格软弱……”
她挺起身,沉默半晌,又问道:
“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民众应起来暴动?当然应当!大家都这么认为,只是各想各的,闷在心里头。要让大家都说出自己的想法……应该有一个带头人,下定决心……”
她坐在长凳上,突然问道:
“您说说,连那些富小姐也做这种事,去找工人们,向他们宣传,难道他们不嫌脏,不怕累吗?”
她仔细地听了母亲的回答,然后深深叹了一口气,垂下眼帘,低下头,又说:
“我在书中读到过这样的话:‘昏昏噩噩的生活’。这句话我很理解,一看就明白!我很熟悉这种生活,有一些想法,可是不连贯,就像离开牧人的羊群,转来转去,没人也没法把它们聚拢来,这就是昏昏噩噩的生活。我真是想避开这种生活,当你领悟、有所明白的时候,你心里可就难受了!”
母亲深刻理解女主人的苦闷,望着她那双冷漠的绿色的眼睛和瘦削的脸,听着她的声音,母亲真想安慰安慰她,为她分解忧愁。
“亲爱的,你是知道该如何做啦……”
达吉扬娜小声地打断她的话:
“那也需会做呀。床已铺好了,您快睡吧!”
她说完走到炉灶旁,一声不响地站在那里,身子笔直,神色专注且严厉。母亲和衣躺在长凳上,她感到很疲惫,骨节酸痛,便轻哼几声。达吉扬娜熄了灯,小屋立刻一片黑暗。黑暗中又传来她平静的低语,听声音好像她要从这窒息而又黑暗的夜色中擦去什么。
“您睡之前不做祷告,我也觉得没有上帝,也没有所谓的奇迹。”
母亲不安地翻个身,面向着窗户。这时,窗外黑乎乎的,一片沉寂,隐隐约约的沙沙声和簌簌声不甘寂寞地打破了静谧。她像鸟语似的胆怯地说:
“有没有上帝我不知道。人信基督,我也相信他的话:‘爱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我相信他的话!……”
达吉扬娜什么也没说。在炉灶的黑色背景上,母亲看见她那模糊的背影。她直直地站在那里,纹丝不动。母亲难过地闭着眼睛。
忽然又传来她冷漠的声音:
“自从我孩子死了以后,我就不原谅上帝,也不原谅人们,永远不原谅!……”
母亲不安地欠起身子,她深深理解女主人的心里此时是多么的痛苦。
“您还很年轻,您还会有孩子的。”母亲安慰着她。
女主人迟疑了一下,低声地说:
“不,我身体被搞坏了,医生说,我以后不能生育了……”
地板上窜出一只耗子。不知是什么东西哗地一响,就如无形的雷电打破了屋内的沉寂。不久又静了下来,只听见秋雨抽打屋顶干草的簌簌声,仿佛有人在屋顶上悄悄地摸索着,纤纤的手指不停地打着哆嗦。雨点冷清地叩击地面,让人觉得秋夜在慢慢地流逝……
母亲刚要入睡时听见门外和走道里有脚步声。门悄悄打开了,传来轻轻的呼唤:
“达吉扬娜,您睡了吗?”
“没有。”
“她呢?”
“也许睡着了。”
灯光亮了,抖动几下后又灭了。屋里又是一团黑。斯杰潘走到母亲床前,拉了拉皮袄盖住她的脚。这亲切的举动使母亲非常感动,她又闭上了眼,偷偷笑了笑。斯杰潘一声不响地脱了衣服,爬上了炕。屋里又安静下来。
母亲聆听着在静谧中轻轻摇荡着的气息,她静静地躺着,雷宾流着血的面孔又呈现在她眼前的黑暗中……
炕上时不时悄悄地低语:
“你看,人家都是什么人,还干这种工作?这么大年纪,一辈子吃苦受累,本应该多休息 ,可现在还奔波。可你,年纪轻轻,又聪明,唉!斯杰潘呀……”
男人的声音圆润且低沉:
“干这种事之前必须好好考虑,否则不能干的……”
“你这些话我听多了……”
谈话声中断了,不久又传来斯杰潘的声音:
“我看不如这么办,先去找农民们单独谈一谈,如阿辽沙?马科夫,胆大泼辣,认字,被官府压迫过。谢尔盖?肖林也是个聪明的人。克尼亚杰夫为人正直,胆子又大。刚开始有这几人也差不多。得去看看她提起的那几个人。我打算带一把斧头去城,装做为人家劈柴,打短工。不过这事得小心。她说得正确,一个人是否有价值,这取决于他自己。今天被抓的那人就是好样的。就算把他押到上帝前面,他也一定不会屈服……那个尼基诺就没有价值,是吗?不过他也会良心发现,真是个奇迹!”
“当着你们打人,可你们却无动于衷……”
“你算了吧!我们没动手打他,你就应当说谢天谢地。真的!”
他讲了很久,时而低嗓门,母亲听不到他说什么,时而放开嗓子大叫,这时达吉扬娜马上拦住他:
“小声点,别吵醒她……”
母亲睡着了,沉沉的睡梦像一团浓浓的乌云压在她身上,笼罩着她,把她卷走了。
达吉扬娜叫醒母亲时,天还刚亮,小屋的窗外仍是一片昏暗。村里静静的,寒气逼人,教堂的钟声在村庄上空懒懒地飘着,渐渐消失。
“我把茶烧好了,你喝一点吧,要不然一起来就动身,太冷啦……”
斯杰潘一边梳理他那蓬乱的胡子,一边仔细询问了母亲在城里的住所。这时母亲感到他那张脸今天更显得好看了,喝茶时,斯杰潘笑道:
“真是巧遇啊!”
“什么?”他妻子问道。
“认识她真是很巧 !就这么自然……”
母亲思索片刻,满有信心地说:
“干这种事情,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临别时,斯杰潘夫妇比较拘束,没有说而对她路途中的安顿却考虑得较周全。
坐上马车后,母亲心想,斯杰潘一定会小心翼翼地进入工作,像田鼠似的不声不响,埋头苦做。他妻子会在一旁喋喋不休,时而不时地埋怨,她那双绿眼睛定为咄咄逼人;作为母亲,夭折孩子的思念会永远地围绕着她,那种狼一般的复仇心理会永远陪伴着她。
这时,雷宾又呈现在她眼前,她犹如看见他那流血的面孔和那双炽热的眼睛,就像听见了他的话。在那群恶兽面前没有帮助他,她感到心痛。在回城的路上,天色微暗,大胡子雷宾的身影一直浮现在母亲眼前。他身体结实,衬衫被撕破了,双手被绑着,头发很乱 ;他满腔怒火,坚信真理。此时,母亲想到胆怯地蜷缩在土地上的无数的村庄,人们极度期待着真理早一天到来,也有千千万万的人并不抱什么期盼,昏昏沉沉地生活着,默默无闻地劳动一生。
生活犹如一片重峦起伏的未曾开垦的旷野,在焦急地等待拓荒者,它默默地向那些爱好自由的善良人们许诺说:
“如给我播下理智和真理的种子,我将会加倍地偿还给你们!”
母亲回想着这次成功的出门,内心感到欣喜万分,她尽力克制自己,不好意思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