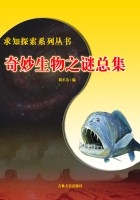重逢的喜悦过后,后续“部队”的人,除了麦克那布斯少校以外,巴加内尔也好,奥斯丁也好,威尔逊也好,穆拉迪也好,全都感到渴得不行。幸好,不远处就是瓜米尼河,大家直奔河边而去。早晨七点,众人来到了“拉马塔”前,只见院子前后左右躺着不少的死狼,可见昨夜战斗之激烈。
喝足了清凉的河水,在“拉马塔”里又饱餐了一顿。“南杜”的肋条肉非常可口,连壳烧烤的犰狳更是好吃。
“吃少了也对不起老天爷呀,”巴加内尔说道,“所以得吃到撑破肚皮。”
巴加内尔真的没少吃,但肚皮并未撑破,因为他喝了不少瓜米尼河清凉的水,觉得那水具有奇迹般的消化功能。
格里那凡爵士想到汉尼拔在卡布按兵不动所带来的后果,不想重蹈他的覆辙,便下令于十点上路。众人把皮桶装满了清凉的河水之后,便动身了。马儿们吃饱喝足休息够了之后,劲头儿十足,奋蹄前行。潮湿的土地开始肥沃了点,但依然不见人烟。十一月二日和三日,两天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记述的。到了三日晚上,大家经过两天来的长途跋涉,已经是人困马乏了,便在潘帕斯大草原的尽头,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边界上歇了下来。他们于十月十四日从塔尔卡瓦诺出发,已经走了二十二天,走了四百五十英里左右,也就是说,走完了三分之二的路程。
第二天早晨,他们跨越了阿根廷的草原区和平原区的分界线。塔卡夫希望在这一带能够碰上抓住哈利?格兰特船长及其两个同伴的那些印第安人的酋长。
阿根廷的十四个行省中,就数布宜诺斯艾利斯省最大,最富庶。该省位于东经六十四度和六十五度之间,与南部的印第安人居住区接壤。这里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禾本科草类以及高大得如树木一样的蔬菜遍地皆是。此处地势平坦,一直到坦狄尔山和塔巴尔康山,几乎都毫无起伏。
一行人自离开瓜米尼河之后,一直对这一带的气候深感满意。由于巴塔戈尼亚的凛冽寒风在天空高处搅动着气浪,使这儿的气温经常保持在摄氏十七度左右。众人经过酷热,来到这儿,自然感到非常舒适,一个个兴奋不已,神清气爽,精神抖擞,奋勇向前。尽管这儿条件是这样的好,但这儿却仿佛未曾有人住过,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这儿住的人全都搬走了。
南纬三十七度线在这一地区穿过许多沼泽和湖泊;湖水有咸有淡;湖岸树丛中可见鹪鹩、百灵鸟、红腹椋鸟以及能在空中停歇的“唐迦拉”在飞来飞去……荆棘丛中,“安奴比”鸟的悬窝像殖民地里的白种人的吊床一般;有着火红翅膀的朱鹭的窝则是一英尺多高的圆锥形建筑物,成百上千个窝聚在一起,俨如一座小城镇。一行人靠近时,朱鹭并不躲闪,照旧排着整齐的队列行进着,令巴加内尔大为失望。
“我早就想观赏一下朱鹭是怎么飞翔的了。”巴加内尔对少校说道。
“这并不难。”少校回答道。
“现在正是个好机会。”
“那就莫失良机,巴加内尔!”
“跟我来,少校。你,罗伯特,你也来。我需要你们作证。”
巴加内尔说着,便向那群朱鹭走去,身后跟着少校和小罗伯特。
走到射程之内,巴加内尔便往枪里塞上火药。他没有装子弹,他不愿看到这么漂亮的鸟儿鲜血淋漓。只听他砰地一声,朱鹭们一下子全都惊飞起来;巴加内尔举起望远镜,仔细地在进行观察。
“怎么样?”当朱鹭飞远看不见了时,巴加内尔问少校,“您看见它们飞了吗?”
“当然看见了,我又不是瞎子。”少校回答道。
“您觉得它们飞起来时像不像羽箭呀?”
“一点也不像。”
“根本没法相比。”小罗伯特也说。
“我也早就认为是不像的,”巴加内尔很高兴地说道,“可是,竟然有这么一个人,一个可以说是谦虚者中最骄傲的人,也就是我们那位大名鼎鼎的夏多布里昂,他却以羽箭来比喻朱鹭。唉!罗伯特,你看到没有,文学性比喻是最不足信的!你要记住,一辈子都别轻信比喻,不到万不得已,也别使用比喻。”
“您对自己的试验感到满意了吧?”少校问道。
“太满意了。”
“我也满意了,不过,该赶紧扬鞭催马了,就因为您的那位大名鼎鼎的夏多布里昂,我们耽误了一英里路的行程。”
当巴加内尔他们追上来时,格里那凡爵士正与塔卡夫在高谈阔论而又苦于语言不太能沟通,感到十分苦恼,塔卡夫不断地停下不说,看着远方地平线,满腔的惊讶,而格里那凡爵士见状,总想向塔卡夫问个究竟,但总也问不清楚。这时候,巴加内尔出现了,他当然是喜出望外了。
“快过来,快过来,巴加内尔!塔卡夫同我说话,我们相互沟通起来太困难了!”
于是,巴加内尔便与塔卡夫交谈了一会儿,然后,转向格里那凡爵士说:“塔卡夫看到一种非常非常奇特的现象,颇感惊讶。”
“什么现象?”
“他说,在这一带平原上,往日总会碰到许多印第安人成群结队地走过,或是赶着从牧场劫掠来的牲畜,或是赶到安第斯山区去卖他们的鼬绒毯子和皮条鞭子,但现在,不仅见不到印第安人,而且连他们走过的痕迹也看不见了。”
“塔卡夫没说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吗?”
“他也弄不清是什么原因,只是感到非常惊讶。”
“他原以为在这一带会遇到什么样的印第安人呢?”
“他原以为会遇到曾掠掳过外国人的那帮印第安人的,也就是卡夫古拉、卡特利厄尔或扬什特鲁兹等酋长手下的那帮印第安人。”
“他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这些酋长?”
“三十年前,这些酋长曾是手中握有巨大权力的酋长,后来被赶到山这边来了。从此,他们便驯服了,在印第安人所能忍受的驯服范围内驯服了。他们在潘帕斯大草原上和阿根廷平原地区游来荡去,专干盗匪的勾当。可现在却碰不到他们了,我也同塔卡夫一样,对此非常的惊讶。”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格里那凡爵士追问道。
“那我得问问他看。”巴加内尔回答道。
于是,他又去同塔卡夫交谈了一会儿,然后转向格里那凡爵士说道:
“他的意见我很赞同。他提议我们继续往东走,在这三十七度线上,有一座独立堡。到了那儿,我们就算是打听不到格兰特船长的消息,也能弄清楚为什么阿根廷平原上见不到印第安人的踪影了。”
“独立堡离这儿远吗?”格里那凡爵士接着又问道。
“不远,就在坦狄尔山里,离这儿大约有六十英里地。”
“什么时候可以走到?”
“后天晚上。”
格里那凡爵士因这一意外情况而心事重重。在潘帕斯地区竟然碰不到一个印第安人,这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事,通常,这一带的印第安人特别多,可现在却一个也看不见了。肯定是有什么特殊的情况迫使他们离开了这里。尤为严重的是,如果哈利?格兰特船长确定是落入这儿的一个印第安人部落手中,那么现在,他是被掳去北方了呢还是被带到了南方?这么一想,格里那凡爵士不免举棋不定,但又苦于没有其他良策,只好听从塔卡夫的提议了,先到独立堡再说。
将近下午四点左右,远处可以望见一个丘陵隐现在地平线上。那丘陵挺高,在这个平原地区,可算是一座山峦了。那就是塔巴尔康山,一行人在山脚下歇息、过夜。第二天再翻过这座山,非常的容易。沙土地似波浪般起伏,山坡并不太陡。与安第斯山脉的高低岩比较起来,这山坡对这一行人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马儿爬坡连速度都没有放慢。中午时分,他们过了塔巴尔康废堡,这儿是山南地区构筑的防御土着人来袭的那条碉堡链的第一环。但是,在这儿,仍旧没有见到印第安人的踪影,致使塔卡夫更加惊讶不已。正晌午时,有三个人骑着马,带着枪,观察了一番格里那凡爵士的这支人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不一会儿,一溜烟便不见了。格里那凡爵士感到大失所望。
“他们是高卓人。”巴塔戈尼亚人说道,他对土着人的这种称谓曾引起少校与巴加内尔的一番争吵。
“啊!是高卓人,”麦克那布斯应声道,“嘿!巴加内尔,今天北风止息了,您到底觉得这帮家伙怎么样呀?”
“我觉得他们的架势很像大盗。”巴加内尔回答道。
“我亲爱的大学者,‘像大盗’与‘是大盗’有多大的差别呀?”
“一步之差,我亲爱的少校!”
巴加内尔的回答把大伙儿给逗乐了,他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就印第安人的问题发表了一通高论:
“我记不清在哪本书上曾经看到,说是阿拉伯人的嘴带有凶恶之相,但眼光却显得十分温和。现在,我看美洲的土着人,情况却恰恰相反,他们总是眼露凶光。
”
即使是专业相面人也不比他形容印第安人更准确。
这时,大家遵照塔卡夫的意思,紧靠在一起向前走着。尽管此处看似荒无人烟,但还是小心为上,绝不可掉以轻心!然而,这种防备毕竟是多此一举。当天晚上,一行人在一个废弃的寨子里歇息,这个废弃的寨子原先是卡特利厄尔酋长平日里集合土着人队伍的地方。巴塔戈尼亚向导看不出这儿最近曾经有人住过的迹象。他仔细地检查了一番,仍一无所获,只发现此处久已无人住了。
翌日,一行人重新上路,与坦狄尔山毗邻的头几处“厄斯丹夏”已可看见,但塔卡夫决定不在此处停留,直奔独立堡而去,因为他特别想搞清楚,为什么这一带竟然会没有人烟。
自打越过高低岩之后,一路之上,树木日见稀少;可是,到了这儿,树木竟然又多了起来,多数是欧洲人来到美洲大陆之后种上的。其中有楝树、桃树、白杨、柳树、豆球花树等。这些树没人管,但长势很好。这些树通常都是围绕着“戈拉尔”,亦即很大的“牲畜栏”栽种的。“戈拉尔”周围钉有树桩,栏内饲养着成群的牛、马、羊;牲畜身上都烙有代表其主人的烙印;栏外有许多大狗守护着。在山脚下展开的稍稍带有盐质的土壤上,长着优质刍草,是牲畜的上等饲料。每一个“厄斯丹夏”都有一个总管和一个工头,每千头牲畜又有四个培翁负责。
这些人过着《圣经》中的那些大牧主般的生活;他们的牧畜头数可能要比遍地牛羊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牧主们的牲畜还要多;但是这儿的放牧人没有家庭生活,潘帕斯地区的“厄斯丹夏”的业主都是一些贩卖牲口的人,毫无《圣经》中的那些儿孙满堂的老祖宗的味道。
上面的这些情况是巴加内尔解释给他的同伴们听的。而且,他还就此发挥起他的有关人种学的高论来,对不同种族进行了饶有趣味的比较,连平时不动声色的少校听了也露出颇感兴趣的神情来。
与此同时,巴加内尔还有机会让他的同伴们欣赏了一次海市蜃楼的奇观。这种幻景在平坦的原野上并不鲜见,许多的“厄斯丹夏”,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座小岛一般;其周围的树木倒映在清水里,而这汪清水像是在逗引行路人,你进我退,总不可及。这幻象奇妙逼真,令人难辨真伪。
十一月六日,一行人数次遇到“厄斯丹夏”和一两个“杀腊德罗”――宰杀肥壮牲畜的地方。正如其名所示,“杀”了牲畜之后,便用盐把肉腌渍起来。这种血腥的宰杀活计始于春末。“杀腊德罗”派人去“厄斯丹夏”拉回需要宰杀的牲畜。他们先用“拉索”去套捕牲畜,套捕够数了便一起拉走。其套捕技术十分高超,令人惊叹。在屠宰场,一次就得杀上好几百头,杀了之后剥皮,切肉。但是,老牯牛不好杀,经常挣扎、反抗,遇此情况,屠夫就变成了斗牛士。这种活计相当危险,但屠夫们技术娴熟,得心应手,当然,手段毕竟是极其残忍的,“杀腊德罗”周围简直可以说是“阴森可怖”。臭气弥漫于空气中;院子里,屠夫们的吼叫声、狗吠声和牲畜的哀鸣声交织在一起;阿根廷平原上的鸷鸟――“乌鲁布”和“奥拉”成百上千地从方圆几十英里处飞来,从屠夫们的手中抢夺仍在颤动的牲畜肉。不过,当格里那凡爵士一行路过此处时,却是寂然无声,静悄悄的,因为大规模屠宰的季节尚未到来。
塔卡夫一个劲儿地在催促大家快马加鞭,他想在当晚赶到独立堡。众马在主人的鞭子的抽打之下,学着桃迦的样儿,在高深的禾本科草类中奔驰着。一路之上,也曾遇上几户农家,屋子周围都挖有深沟,垒起高垒;正屋上方有一阳台;农夫们全都携有武器,可以从阳台上射击平原上的盗匪。格里那凡爵士觉得在这儿也许能打听到一些消息,但是,考虑再三,还是到了坦狄尔村再说吧。于是,一行人沿途没有停息,他们涉过了洛惠索河,奔跑了好几英里之后,又越过了沙巴雷夫河。然后,马蹄便踏上了坦狄尔山的最初几重草坡。一小时之后,他们已经看见了坦狄尔村;它深藏在一个狭窄的山坳里,独立堡那重重城垛显现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