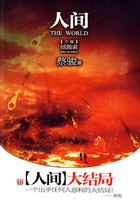“他们认为――但我不知道他们的这种‘认为’有多大根据――放火一烧,潘帕斯草原的草就会愈发的茂盛。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说,他们这是在用草灰肥田。可我却更倾向于认为,他们是在烧草灭虫。草原上有一种寄生虫,名为‘鲁虱’,对牲畜危害极大。放把火,可以烧死千千万万只‘鲁虱’。”
“可是,这么一来,城门失火,会殃及池鱼的,牲畜不也要跟着送命吗?”少校问道。
“那当然啰。不过,这儿牛羊极多,烧死一些也无伤大雅。”
“我担心的倒不是牛羊,”麦克那布斯又说道,“而是从潘帕斯草原穿过的旅行者。突然遭到大火包围,他们如何是好?”
“您怎么还怕这个!”巴加内尔惊讶地说,“要是真的遇上这种情况,那可是难得的好景象,颇值得观赏一番的。”
“我们的这个学者呀,研究起学问来,连死都不怕。”格里那凡爵士说。
“噢,我亲爱的爵士,我可没有那么傻。我读过库柏的游记。皮袜子告诉我们说:野火烧起来的时候,把自己周围的草拔光,弄出一块直径有几托瓦兹的空地来,就可以避开火势了。这办法简单可行。所以我并不担心大火烧过来,我反而希望能看到一场大火。”
巴加内尔希望观赏到的一场漫天大火并未到来;如果说他此时此刻已经被烧灼得够呛的话,那是因为太阳的强光所致。在这么热的地方,连马也喘息不停。根本就见不到一点的阴凉地儿,除非天上飘过一片浮云,遮住了太阳,投下一片阴影。这时候,骑马的人们便快马加鞭地追着这片云影,躲在下面奔驰着。但是,马儿跑不过飞云,不一会儿,太阳又露出了云端,洒下一片“火雨”来。
威尔逊先前还说不愁没水喝,他没想到这一天大家竟然渴得比饥饿还难受。他原以为路上会遇到溪流小河什么的,他也真是想得太美了。沿途不仅没有河水流淌,甚至连印第安人挖掘的池塘也都干涸了。巴加内尔看到干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便问塔卡夫何处可以找到水源,得赶紧想办法。
“必须走到盐湖才有。”那印第安人回答道。
“什么时候可以到盐湖?”
“明天晚上。”
通常,阿根廷人来到草原,都是临时掘井取水,一般往下掘几托瓦兹便可见到水了。可是,格里那凡爵士一行人没有携带掘井工具,无法取水,只好把所带的那一点点水,定量分配。
大家一口气又走了三十英里地。入夜时分,便歇了下来。大家都想好好地睡上一觉,恢复体力,可是蚊子成群结队地飞来,黑压压的。蚊虫成群飞来,表示风向有所改变。果然,风向转了九十度,由西风变成了北风。一般情况下,刮南风或西南风是不会有蚊虫飞过来的。
对这些恼人的事,少校倒还能泰然处之,但巴加内尔就不行了,他开始不耐烦起来。他恼透了那些可恶的蚊子,也恨自己没带药水来擦拭浑身被叮咬的伤痕。尽管少校竭力地在安慰他,但他第二天早晨爬起来时仍然是一脸的不高兴。
不过,天一亮,他还是跟着大家上路了,并没让人催促,因为当天必须赶到盐湖。马也累得不行,渴得要命,尽管骑马的人在尽量省点水给它们喝,也只是杯水车薪。这一天,天气干燥得更加的厉害,潘帕斯草原的北风与非洲大沙漠的那种令人生畏的热风一样,风起沙扬,如沙尘暴一般。
这一天,旅途中遇上了一个小插曲,打破了沉闷的气氛。走在前面的穆拉迪忽然勒住马,报告说有一些印第安人走了过来。对迎面而来的印第安人,格里那凡爵士与塔卡夫的看法不同,意见相左。爵士想到这些土着人的到来,可以让他从中打听到一点有关不列颠尼亚号失事的船员的情况;可塔卡夫却极不愿意在草原上遇上游牧的印第安人,他认为他们多为盗贼,避之为好。在塔卡夫的命令之下,一行人集中在一起,准备好武器,有备无患。
不一会儿,他们便看见一些印第安人迎面而来。人数大约在十个人左右,塔卡夫一看,心里踏实了。印第安人已经到离他们一百来步的地方,面庞看得清清楚楚。他们都是土着人,是一八三五年罗萨斯将军扫荡过的那个地区的部落人。这帮人,额头高高,向前突起,身材魁梧,皮肤棕黑,具有印第安人的健美。他们身披原驼布或臭鼬皮,身上除背着长枪而外,还带着刀子、弹弓、“跑拉”和“拉索”。他们善骑术,姿势优美,英姿勃发。
他们在一百来步远处停了下来,大呼小叫,指手画脚,像是在商讨点什么。格里那凡爵士迎上前去,但还没走上四米远,那帮土着人便勒转马头,一溜烟消失得无影无踪。
“熊包!”巴加内尔骂道。
“逃得这么快,绝不是什么好人!”麦克那布斯说。
“这些印第安人是什么种族的?”巴加内尔向塔卡夫问道。
“是一些高卓人。”
“高卓人!”巴加内尔转向他的同伴们说,“原来是一些高卓人呀!我们刚才也太大惊小怪的了。没什么好害怕的!”
“为什么呀?”少校问道。
“因为高卓人都是和善的庄户人。”
“您真的这么认为,巴加内尔?”
“那当然。这几个高卓人把我们当成了盗贼,所以才一溜烟地吓跑了。”
“我倒是认为他们不敢攻击我们。”格里那凡爵士说道,他本想不管他们是什么人,也要同他们谈谈,可他们却望风而逃,他感到很是懊恼。
“我也这么认为,”少校说,“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看高卓人并不是什么和善的庄户人,而是地地道道的盗匪。”
“您怎么能这么说!”巴加内尔反对道。
于是,巴加内尔便开始大谈起种族学的问题来,而且越说越激动,使得少校也按捺不住,不禁与之争论开来。
“我认为,您的说法不对,巴加内尔。”
“不对?”
“就是不对。连塔卡夫都把他们视为盗贼,我觉得塔卡夫这么说是有根据的。”
“塔卡夫这一次可就错了,”巴加内尔反驳道,语气之中不免带着这么点气愤,“高卓人不过是农民,牧民,其他什么都不是,我曾写过一本关于潘帕斯大草原的土着人的小书,颇受欢迎。”
“那您就更是错了,巴加内尔先生。”
“我更是错了,麦克那布斯先生?”
“就算作是您因粗心而导致的出错吧,”少校步步紧逼地说,“您的书要是再版的话,一定要更正一下。”
巴加内尔一听对方不仅在批评自己,而且是在嘲笑自己,脸色就变了,挂不住了,火气上来,难以抑制。
“您听清楚了,先生,我的书无需更正!”
“还是需要更正的!至少,这一次得更正更正。”麦克那布斯毫不相让,固执地反诘道。
“先生,我看您今天是专门在找碴儿呀。”巴加内尔说道。
“我也觉得今天按捺不住火气!”少校针锋相对地顶撞道。
不难看出,本不是什么大事,可争论已超出了范围,格里那凡爵士觉得应该予以干涉了。
“说实在的,”他说道,“你们两个,一个在故意挖苦,一个也火气太大,我对你们两个都感到惊讶。”
那个巴塔戈尼亚人听不懂他俩在争论些什么,但却看得出来他俩在争吵,于是,他微笑着冷静地说道:
“都怪北风不好。”
“北风有什么不好?这关北风什么事呀?”巴加内尔大声说道。
“没错,就是北风不好,”格里那凡爵士说,“正是北风惹您上火的!我听说,南美洲的北风最能刺激人们的神经。”
“圣巴特利克作证,爱德华,您说得太对了!”少校说着便放声大笑起来。
巴加内尔这一次可真的气坏了,他觉得格里那凡爵士的干预简直是在捣乱,便抓住爵士不依不饶了。
“哼!您这叫什么话呀,爵士?”他不肯善罢甘休地说,“我的神经受到刺激了?”
“是呀,巴加内尔,确实是北风刺激的呀。这种风让人在潘帕斯大草原没少犯错,正如山外风在罗马乡间刮起时一样。”
“犯罪!”巴加内尔气哼哼地说,“我像会犯罪的人吗?”
“我并没说您是罪犯呀。”
“您干脆就说我想杀害您得了!”
“哈哈!”格里那凡爵士忍不住放声大笑起来,说道,“我还真怕您把我给杀害了哩!幸好,这北风只刮了一天!”
其他人听了这话,便与爵士一起哈哈地大笑起来。
于是,巴加内尔双腿一夹,刺马飞奔,跑到前面,独自去冷静一下去了。一刻钟之后,他便把这事一股脑儿地抛得不见了踪影。
晚上八点,塔卡夫指着那些通往盐湖的干沟让大家看,告诉大家盐湖就要到了。又奔驰了一刻钟,众人便翻过盐湖堤岸,下到湖边,但不禁大失所望,只见湖底一片干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