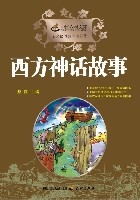我的喜怒哀乐生老病,都在西湖发生,除了死。我的终生职业是“修炼”,谁知道修炼是什么样的勾当,修炼下去,又有什么好处?谁知道?我最大的痛苦是不可以死。已经一千三百多年了,还得一直修炼下去,伊于胡底?
简捷、缠绵而骨子里富有筋道的文字,像道乍吃的新菜,唇间留下的不是香,比香重。
然后就如骏骥,奔波在李碧华奇谲鬼魅的笔下,驻足回首,已是千里异乡;《胭脂扣》《生死桥》《潘金莲前世今生》《秦俑》……一边看一边急,天下的好文章都给这个女人写尽了,还让别人怎样苟活?
更为“愤怒”的是,她的随笔也动人。《橘子不要哭》《樱桃青衣》《绿腰》《蝴蝶十大罪状》《泼墨》《逢魔时间》等。究竟也不过是泛泛“食色”二字,可是“经她一说,嗳——石破天惊,魂飞魄散”。
我不相信天才这回事。常常想起李碧华从寂寂无名写到天下谁人不识的浪漫长路。人见蝴蝶美,有谁关心它在茧中的郁闷挣扎?成名后,淡淡一句“为免饔飧不继,且具自虐倾向,同期做着多份职业,以榨取有限之脑汁维生”就带过了。
人以为她真淡定、真幽默,殊不知那条杀出血路必经的人仰马翻、胼手胝足……她样样不曾缺过。
世间哪有美女作家这回事,几个漫漫长夜熬将下来,神仙妃子也无奈黑眼圈、皱纹、浮斑若何。很多女作家都惨遭离异,因为她们沉溺于文字中很难看,面色灰败,衣衫不整而神情恍惚,夜半骤见之下,非心理素质极佳者无以承担。写作而不出点成就的女人,比窦娥还冤。
李碧华在这方面,特立独行,冰雪聪明。即使大红大紫,仍坚持不公开照片,身世、年龄、容貌不详。她曾道:“别那么好奇我的面貌,我是那种摆在人群里,不容易特别被认出来的样子,没什么好描述的。和外界的人和世保持适当的距离,对我来说是好的,不老记挂着自己的影响力,不去想有多少人正在看你写的文字,不至于动不动就把自己当成苦明灯,方可潇潇洒洒地写。”
她自拟的一份“档案”展示了她的潇洒、幽默和神秘。
艺名:李碧华
原名:李白
年龄:数字太大
胸围:数字太小
职业:门面——记者、编剧、专栏小说作者
底牌:夸张、虚构、捏造、渲染、无中生有、唯恐天下不乱
健康状况:迈向死亡,当然
最爱的动物:男人
最厌的动物:男人
愿望:不劳而获,财色兼收,醉生梦死;快乐美满人生:七成饱,三分醉,十足收成;过上等生活,付中等劳力,享下等情欲
遗憾:上述愿望终成泡影
似乎有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越是成功越是优秀的人士,越是不自圆其说。实在躲不过,也是以诙谐自嘲方式,反而欲盖弥彰,其人气指数,更上一层楼。李碧华曾在《女工的自白》一文中说:“不管怎样,社会中有人劳力有人劳心,就只是女工中一员。”
李碧华的“自醒”,让浅薄的美女作家们小巫见大巫了吧!李碧华认为,写小说是“先娱己,然后再娱人的享受”。因此她追求雅俗共赏,不仅写小说,而且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娱乐更多的人。如不是电影,李碧华不能如此名扬天下。她的小说,除了长篇小说《生死桥》,部部都是电影的宠儿。人、鬼、妖,生、死、血,前生、今世、来尘……那样铿锵激越、睚眦尽裂的爱恨情仇,不知怎的,只令人想起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李碧华在电影方面的成就,唯独琼瑶和她可以抗衡,但在我看来,琼瑶的影视作品是以数量取胜,但其艺术及文学内涵,无法和李碧华的作品相媲美。
我对李碧华的作品,并非“一见钟情”。她的书被冷落在书橱里好长时间,其缘由,竟是“看不下去”。她的作品文字上受旧话本影响太深。我猜她除《聊斋》之外,《阅微草堂笔记》之类必是烂熟。不然,当代志怪文字,舍她其谁。那个冬天的午后,借着懒懒的阳光,看了《纠缠》。这个故事总是散发着忧伤的气息,从一开始总让人哽咽着特别的难受,是一种难以向人倾诉的伤痛,似一根针就这么刺在左胸上,却流不出血。
2003年8月
时尚变奏曲
大约是二十年前,国内最流行的一首歌:“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得太快”。
那时手机尚未普及,满大街都是“BB”机,人民群众人手一机,见着熟人潇洒地说一句:“有事儿呼我!”如今最流行的是“微信”,即便是刚认识,只要看着顺眼就马上加微信,立马你就成了他或她的朋友圈。呼机早已沦为“屁屁机”。手机“大哥大”只能在电视剧里偶尔露露面。
比如安全套,过去需凭结婚证到计划生育部门领,现在可以到街上的二十四小时自动柜机买。过去叫“避孕套”,现在叫“安全套”,因为现在除了避孕作用外,还有预防性病、艾滋病的功效。
比如生孩子,过去需要父精母血去培养,现在则有“名人精子库”和“美女卵子库”。
比如算命,过去抽签占卜,属于手工操作,现在则已实现了电子计算。只要输入你的生辰八字,马上就可以用“586”的速度计算出你的前途命运。我去南方一个旅游景点,看见一个算卦小摊,只见广告上写着:“电脑算命——高新技术,保证准确”。
比如讨饭,过去是唱凤阳花鼓:“说凤阳,道凤阳,十年九旱去逃荒……”而今常见街上乞丐抱着吉他,深情地唱着任贤齐的“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假如你真的“心太软”,给他一个面包,他还会拒绝:“对不起,我不是要饭的。”现在的乞丐是要钱的。
比如开会,过去流行“交流会”“研讨会”“展览会”诸如此类,而如今许多会议都改叫“论坛”了,有的还要加上“高峰”二字。
比如公司,过去流行叫“皮包公司”,现在流行叫“手机公司”,凭一部二手手机就把你蒙得晕头转向。
比如经理,七十年代叫“厂长”,八十年代叫“总裁”,现在流行叫“CEO”或是“首席执行官”。即使是一位炒瓜子的,他的名片也印着:“王氏机构首席执行官”。
比如广告,过去流行“做女人挺好”,而现在流行男人也“挺好”!电视上看到“××肾宝”广告里的那位太太,还进一步强调指出:“他好,我也好”。
比如女人,过去在小说里一描写女人就是“水汪汪的大眼睛”“红扑扑的脸蛋”。现在小说里的女人则是“高挺的胸脯”“丰满的臀部”。比如男人,过去喜欢叫“靓仔”“帅哥”,现在改叫“伟哥”了。
比如爱情,过去讲究“一见钟情”,现在则流行“一键钟情”,就是“爱情速配”,连爱情也要实现数字化。
比如谈恋爱,过去流行走着谈,现在则流行躺着谈。也就是说,这“爱”由“谈”变成了“做”。
比如结婚,过去讲究“百年好合”,现在常见“一年签一次婚约”,或是“七年之痒”。
比如婚外恋,七十年代叫“通奸”,八十年代叫“第三者插足”,仍具有贬义色彩,而现在的“婚外恋”,为数不少的人说:“听上去很美”。
比如离婚,过去流行的离婚理由是“感情破裂”,现在流行的离婚理由是“性生活不和谐”。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一切都在变化,至于你是否喜欢,是否接受,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就像老歌里唱的,“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个世界变得太快”。
初稿写于2004年
2014年修改
《廊桥遗梦》的另一种读法
尽管导演为《廊桥遗梦》精心设计了一个子女因母亲遗留下来的日记,而知悉她的爱情故事最终受到感染回归真情的框架,但中国人还是更多地从这个故事中看到了“婚外情”三个字。
善始善终的爱情无人关心。经典爱情总是具有某种残缺美,从而获得正常婚姻所不可能有的戏剧性元素。一个成熟而富有修养的男人的初来乍到,正中了一个心怀小资情调的农庄中年女人的下怀。她志不得抒,无人交流,丈夫敦厚朴实,儿女尚幼,她不甘心一生就这样平庸无闻。然后有这样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可以与她一起听美国乡村音乐,拥她慢舞,给她拍照,还会称赞她美艳动人,最重要的是,丈夫和一双儿女都将几天不回家,于是,机会来了,而他呢,刚刚离了婚,浪迹天涯,身无羁绊,又有一技之长可恃。
许多人为这个爱情故事感动得来不及买纸巾时,似乎无意把自己比作老实丈夫,而更愿意视自己为金凯,婚姻中的外星人、第三者。这样,他们可以一边期待艳遇,一边不必为妻子的红杏出墙火冒三丈。其实,弗朗西斯卡“坚守婚姻”,而不选择与他人私奔,恰恰说明了婚外情是玩不起的,代价总是要付出的,要么是家人,要么是自己。
导演和书作者把男主人公的命运安排成日夜思念终生不再娶,纯粹是出于煽情的需要,一方面表明这份爱情的坚贞,另一方面说明女主人公的眼光不错,找到的是真心相爱的人。而现实中,像廊桥遗梦似的数天一艳遇的故事几乎都是另一结尾:男人以此增加了自己的阅历,并于事后某天,像唐璜一样,得意扬扬地跟狐朋狗友们吹嘘自己的猎艳史。
2009年3月23日
罗丹带来的打击
晚上早早关了电脑,洗了澡,换上干净柔软的睡衣,又冲了一杯美味咖啡,然后舒服卧在大沙发上,很郑重地迎接《罗丹和他的情人》。没想到,在那个秋风沉醉的夜晚,罗丹给我的是一次痛苦的打击。我几次想关掉DVD机,选择看别的电视节目,却又不能。一个神一样的伟大男人就这么悄然粉碎。如同亚瑟用铁锤敲碎泥偶一样,咚的一下,只一下。我一直认为这情节有经典意义。我年长了许多。
罗丹对于许多浪漫女人来说,是一个幻梦或神话,因为遥不可及的距离。那时我还在电视大学念书,一位老师送我一本葛赛尔的《罗丹艺术论》。我想象罗丹在法国幽静的山冈上的尖顶楼房里,目光如炬,一脸魅力十足的美髯,裸体模特在他周围自由舒展肢体,而他永远在寻找阳光与人体接触时滋滋蒸发的一种无形之美。他用兴奋的眼光,一个看透了命运的人所具有的那种兴奋的眼光,去注释自己的痛苦和创伤。一切都是美的,因为他不断在内在真实的光明中行走。葛赛尔说的这些话,深深感动了我。
电影仍在继续。看到罗丹对前来敲门的卡蜜儿说“我需要安静”并紧闭上门时,我心里发痛。我不能容忍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在所谓事业(或曰名誉地位)和爱情冲突面前如此自私怯懦。他不敢面对自己真实之所求。他的表情和话语冰冷如铁,在那一刻《永恒的春天》及《吻》的热情荡然无存。这冰冷扼杀了一个美丽女人对世界的信任和希望,才华也被冻成死血。
我甚至怀疑他创作的灵感仅来自一种表面的激情和冲动。或者是他回避他自己,那“内在真实的光明”其实是他臆造和幻想的,是他永远到达不了却一直向往的境界。我承认罗丹的复杂,它符合普通的真实的人性。但我不能不为之痛心。
也许我有较强烈的女权主义,这样会妨碍我对罗丹做出公正的认识和判断。公正?我对这个词向来怀疑。它就和真实一样,身上迷雾重重。
我想我不会再对什么人顶礼膜拜,也不必说抱歉。
2003年12月4日
莫尼克公主的情结
2012年夏天,柬埔寨前国王西哈努克逝世,引起众多五十岁以上的中国人浮想联翩,往事如昨。1970年3月,西哈努克遭下属朗诺的军事政变和驱逐,从此流亡中国。中国政府对西哈努克给予国家元首的高规格待遇。西哈努克的到来,给当时“文革”的单调生活,平添了一丝平民乐趣。长期居住中国,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经常到各地访问,所到之处万人空巷,载歌载舞,还要拍成纪录片《西哈努克亲王访问某某城市》。
百姓对当时电影院的内容自编了民谣:“样板戏,老三战,西哈努克到处转。”“老三战”指国产故事片《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然而最吸引观众眼球的还不是西哈努克,而是他的夫人莫尼克公主。
这位意大利和法国混血的极品美人,举止高贵、端庄典雅、仪态万方,中国百姓对她惊为天人。她不断更换的艳丽服饰,在一片灰蓝绿的衣着海洋里,如万绿丛中一点红。十三四岁的我,完全被她给震住了。在我的少年时期,不爱红装爱武装,艰苦朴素,是那时人们的价值观。漂亮与时髦,却被贬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遭众人鄙夷。因此,莫尼克公主空降到红色中国,无数中国人产生“莫尼克情结”,就不足为奇了。
多年后,莫尼克的情结,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也有描写。女作家林白的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战争》这样写道:“在多米的中学时代,最兴奋的日子就是包场电影的日子。此刻我凝望B镇,看到多米的眼睛里掠过的第一道霞光就是美丽的莫尼克公主。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了沈阳又访问桂林,美丽的莫尼克公主穿着一套又一套的漂亮衣服徜徉在飘荡着鲜花和歌声的地方,失去了祖国的公主浅浅地微笑着,她的微笑从那远不可及的天边穿越层层空气,掠过花朵和歌声,颤动着形成一道又一道波纹,一直来到多米的面前。”
作家王童的中篇小说《黑姆佛洛狄特通道》,莫尼克情结更是浓重:“他翻起一张《参考消息》,看到一则西哈努克同红色高棉的消息,这让他忆起了许多年前的柬埔寨,忆起了被推翻了政权的西哈努克亲王。然而,在他记忆的镜面里最明亮、最清晰的却是清丽柔媚的莫尼克公主:她有着一张令东方人倾慕的玉貌,特别是这玉貌上盛开着令东方人赞叹不已的腼腆的微笑,这微笑在那个荒漠般的年代里,如同一汪矿泉从沙丘里冒了出来,在洁净白皙的彼岸上,人们好像发现了个美的新大陆,产生了一种欣赏、羡慕和性混合在一起的冲动。在黄蓝灰绿的工农兵装束的禁锢中,莫尼克公主就像是希腊神话中的美丽女神,溶进了人们的意念中。他的一个同学在精神病发作的时候喊道:‘我要娶莫尼克公主!’”
莫尼克公主肯定不会想到,自己无意中给一个严酷乏味的异国,悄然地开了一扇小窗,让情窦初开的少年男女管窥到一个神秘陌生的美的世界,启发了他们对美的渴望与追求。
其实,莫尼克不仅美貌出众,并有近乎完美的品格,稳重矜持的举止,优雅高贵的气质,温柔善良的脾性,有经历大场面所需的贵夫人风采,凡是莫尼克所到之处,必满堂生辉,而这些是西哈努克以前的妻子和情人所欠缺的。菲律宾前总统马卡帕加尔曾对西哈努克说:“你妻子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漂亮和最难以抵抗的女人,她给柬埔寨带来了荣誉。”
莫尼克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为西哈努克、为柬埔寨赢得了世界。有的国家的领袖仅仅是为了欣赏莫尼克的美貌,而邀请西哈努克夫妇去友好访问;有的国家首脑也只是为了一睹莫尼克的风采而频繁造访柬埔寨。她的确是一个令人无法抗拒的外交秘密武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莫尼克的美貌已经享誉世界。一次,在联合国总部,赫鲁晓夫遇到了西哈努克,他很想欣赏莫尼克的风华绝代。于是,他向西哈努克发出邀请,希望他能访问莫斯科,并当着记者们说,如果他不带他的夫人莫尼克的话,莫斯科将不予接待。很快,这次访问便成行了。访问目的是谈判苏联援建柬埔寨的一个水电站,可在谈判过程中,苏方领导人对莫尼克的兴趣,大有喧宾夺主的架势,谈判本身反倒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