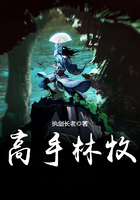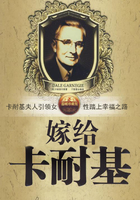“瑞士?那,那在上海那边吧。我问你,他给你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呀?”
“可不!给我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呗!后来我一直包得严严的。”
韩玉梅拿起它,戴在右手腕上,伸到昏黄的灯光下转动着,自我欣赏起来,她的手腕白嫩白嫩的,表带闪亮闪亮的,倒也好看。他看着她那副傻乎乎的样子,心里已经明白究竟是她“勾引干部”,还是败类干部勾引她了。但他又不忍心破坏她的兴致和幻想,只是不觉地叹了口气。
“这个……你自己留下吧,别卖了。以后呢,不出一个月,队里保险给你搞些粮食来,你要相信集体哩,集体总能帮你渡过困难。你呢,也别……跟人胡来了。再找个婆家,正正经经过日子,你看,行不行?”
“那……当然好。”韩玉梅摘下手表,却又无趣地说,“只怕……现时没人要我。”
“咋会没人要你?你这么水灵,谁看了不喜欢?找个外乡人。找来了,我就给他安户口,分粮食,怕啥?你的历史,还不是由我说了算!”的确,庄户人的命运就在他嘴皮子上翻着哩。
韩玉梅想了想,仰起粉嫩的脸蛋,噙着一泡泪水深情地望着他,对他的提议不置可否,却带着呜咽声说:
“书记,我就知道你是个大好人。我老爹在世的时候常这么说。我……我的心里一直想着……”
他忽地又觉得不能自持起来,赶紧摆了摆手,下了炕。
“算了吧,这些话都别说了,乡里乡亲的,你歇着吧。”
他刚要抬脚,陡然,韩玉梅叫他意想不到地扑过来死死地抱住他,一头扎进他的怀里,眼泪鼻涕全蹭在他袄襟上,像发了疯一样哽咽着喊道:
“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我心里早就想你哩!你的啥都在我眼睛里。你是个好人,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你跟那些鬼不一样……你给我红糖的时候我以为你会来哩,结果你不来……谁他妈的要跟那个罗麻子!我想你、想你、想你……”说着,韩玉梅又用拳头不停地在他肩膀和胸脯上乱捶。
他完全惊呆了。他活了三十多岁还从来没有享受过女人的爱情,而这爱情表现得如此突然、粗犷、奔放、热烈,如同火山爆发一般,燃烧的熔岩挟带着大量炽热的泥石流,能把一切草木顽石都熔化;又像黄河决了堤:泥浆迸溅,洪水横溢,咆哮翻滚,势不可挡,他低下头,看到一团青丝般的乱发在他眼前颤抖;在肮脏的衣领里,又看到她如雪似玉的肌肤。但他好像失音了一般,好像麻木了一般,既说不出话,也没有力量推开她。
“我知道你跟我婶过得不快活。我老想安慰安慰你。你太苦了,尽为大家伙儿操心。我能叫你快活,我啥也不要你的。真的,我啥也不要你的。我不要脸,可我挣下粮食来着。隔三下五的,晚上你就过来吃一顿饱饭。我再不跟人……就跟你……我也不嫁人。咱就这样一辈子。我要你快活……”
他的鼻子酸楚起来,眼睛不知不觉濡湿了。是的,他的家庭生活过得不快活,庄子上的人谁也不知道,这个细心而多情的女人却看出来了。
解放后,他从内蒙古回到老家,老妈死了,按庄户人的习惯,首先就要解决终身大事——“男儿无妻不成家”。那根本没有像现在他二儿子要求的啥“爱情”,找个媒人一说,男女双方的岁数、门第都相当,就娶过来呗。他女人娘家是放羊的羊倌,穷苦人出身,而过了门,才知道是个懒婆娘,一天到晚圪蹴在炕上,病恹恹的样子。可说她有病吧,还挺能吃,吃还要吃好的。生了娃娃,女人还不愿意做鞋做衣服,他只好求东家媳妇纳双底子,求西家大婶絮条棉裤,弄得他欠了一庄子的人情。庄户人,对女人的评判标准就是针线锅灶、鸡羊猪鸭,可他女人啥也不干,倒比过去王海家的地主婆还气派。他要不收拾房子,过不了三天家里就跟猪圈一样。他小脚的寡妇妈是个勤快人,后来别看他当的是地方军阀的兵,那个专给省政府看大门的警卫连对内务要求得还很严,所以他自小到大养成了一个爱整洁的习惯。这一来,屋里屋外仍然全得靠他一个人。他经常把娃娃打发出去,关起门用大巴掌扇她。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女人仍然故我,就是声势浩大的“大跃进”,也没把他女人“跃进”得勤快一点。想起来,他常常背着人掉泪,真像戏里唱的:“妻不贤,子不孝,无法可施。”他有浑身的本事,要有个《吕蒙正赶斋》里那样的“贤内助”,就如虎添翼了。可是,碰到这样的女人,有时半夜开完会回来还得自己点火做饭。他是个爱面子的男子汉,又当了支部书记,十来个庄子的头头,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望,只能忍气吞声地受窝囊气,胳膊折了往袖子里揣。
“咋样?别走了,啊,别走了,我不让你走……”韩玉梅摇晃着他,在他怀里扬起脸,一股热气喷在他脖子上。使他痒得心神摇荡。“我就跟你……再不跟别人……你说啥我听啥。”
“别、别……”
过了一会儿,他像从梦中刚醒过来,长长地吁了口气,微微推开她。“你现时正困难哩,咱不能……以后生活好了,咱们再……现时,不行,我心里有事。真的,我心里有事,等以后生活好了……”
韩玉梅好像也理解了,偎在他胸脯上,渐渐沉静下来,细嫩的手温柔地抚摸着他粗糙的脸膛,喃喃地说:
“我懂。你正作难哩……我改,我以后再不了,只要你……可,以后……咱们可一定……”
他点了点头,阔大的手掌揉搓着她柔软的、蓬松的头发,在一时冲动之下,又笨拙地亲了亲她的脸蛋。随即,轻轻推开她,毅然决然地跨出房门。
从韩玉梅家出来,他登登登地跑到井沿上,搬起一块大石头,一下子把冰砸得粉碎,抓起一把冰渣子填进嘴里,嚼得嘎崩嘎崩乱响。好半天,他胸中那股如火的情欲才慢慢平息下去。然后,他抹了抹嘴唇,像一匹被骗了的马一样,无精打采地走回家。
他女人给他开开门,不知怎么难得地殷勤起来,问他:“回来啦,饿么?我可是饿了……”
他瞪起冒火的鹰眼,出手一巴掌把女人打到墙角。
“你饿,吃屎去!”
旋即,他一个箭步冲到炕边,一蹿身上了炕,拉过被子蒙头便睡,连鞋也没脱。他女人莫名其妙地吃了颗窝心九,在地上茫然地站了一会儿,才悄悄地爬上炕,饿着肚子也不敢言喘了。
其实,他一夜也没合眼。
第二天天亮,他喝了碗照得见人影影子的菜汤,一个人跑到河边的防洪坝上去了。
“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尤小舟就是在这片河滩上唱歌的,身后,就是那天他趴着的土坡。“爬地虎”已经枯败了,一簇簇扎得挺挺的,显得更瘦小而又更尖利了。今晨没有风,不但黄河是冻结的,世界的一切,好像连空气也凝固住了似的。摇篮不摇了。歌词仿佛变成了他不认识的、毫无意义的字,要叫他煞费脑筋去思索它。他就这样坐着,想着,坐着,想着……
冬天日短,好大一阵子,太阳才费劲地从东岸沙坡上升上来,有气无力地蹲在沙坡顶上喘息。坡顶上横卧着一条干瘪的、疲倦的乌云。然而天空却是晴朗的,随着太阳挣扎着冉冉上升,乌云渐渐稀薄透亮,终于像一股烟似地化为乌有了。于是,黄河半透明的冰层和上面被风刮脏的残雪,像害肺痨的女人的面孔,泛出了病态的红晕,天气稍微暖和了一点。他在身边扒开一小片冰层,用手指头拨拉拨拉“爬地虎”的宿根,发现茎节上已经开始长出了点点像火柴头那么大的嫩芽。春天快来了,他拍拍巴掌上的土,对自己从贺立德那儿回来的路上设想的办法有了把握。
但是,关键还是需要一个人去蹲劳改。
这个差交不了,那就全盘落空。
就在这时,独眼郝三赶着一群乏羊到河滩上放牧来了。
“天贵,你知道么?天还没有亮,‘黄毛鬼’一个人背着铺盖过了河,八成又跑内蒙古了。”
他们是自小打着耍的伙伴,尽管他早已当了“官”,独眼郝三还叫他的大名。郝三用一根烂绳头拦腰系着破棉祆,啪哒啪哒地趿拉着一双露脚趾头的雨靴,过来在他旁边蹲下。郝三比他大不了几岁,但面孔黧黑,皱纹纵横,一张小脸只有巴掌宽,小脸上嵌着难看的独眼,所以看起来要比他老得多。
“我咋不知道,是我叫他走的。”他怏怏地说。
“你叫走的?为啥?你又不是没去过,内蒙古那边。一出几千里不见人,可不比咱们这儿哩。”
“管它比咱们这儿好。比咱们这儿孬!先躲过一关再说。要不,他就得蹲劳改哩。”他视而不见地望着在河滩上啃枯草的羊,不觉地把实话泄露了。
“蹲劳改?为啥?哧!就为偷那一把把粮食?这怕啥?叫我,就不怕!”
“你当然不怕,吃饱了,连屋里的小板凳都不饿。他可是一大家子人哩。”
“阿——哈咦!”独眼郝三大张开嘴,两臂伸得展展地,懒懒地打了个大哈欠,那只独眼也流出困乏的泪水。
“要说我呀,这日子,还真不如蹲劳改哩。去年劳改队来河边加防洪坝,嘟——吹哨吃饭,嘟——吹哨又吃饭。我他妈回去还得自己做饭,忙得烟熏火燎,饭还吃不饱……唉!”郝三放羊,吃饭总赶不上食堂敲钟。在羊圈忙到黑灯瞎火回家,又只有一只眼睛,做饭是他最头疼的事。
“哦!”听了郝三的抱怨,他心中古怪地一动,转过脸,认真地用锐利的目光打量着郝三,好像他过去不认识这个人一般……
要说独眼郝三呢,也真够可怜的。他刚生下来,爹就被地方军阀抓去当了兵。在兵营里受了一年多罪,想家想得杠子馍都吃不下,偷偷跑了回来。他爹哪有魏天贵机灵,那是个窝囊人,前脚进门,逮他的班长跟着他的后脚就到了。抓回营部,也没揭他的背花,也没关他禁闭,而是把他脱得赤条条的,五花大绑着撂在河滩上喂蚊子。卫兵在远远的地方站着,拢起一堆烟火看着他。他妈——就是郝三的奶奶,趴在儿子身边嚎天嚎地地替他赶蚊子。可是赶去一层又扑来一层,上下一抹一身淋漓的鲜血,蚊子的尸体能搓成条。这样,让蚊子叮了两天,叮死了。葬在庄子西边的高岗上以后,庄子上有人却跟她说:
“你赶啥呀!那头一层蚊子吃饭了就不飞啦,跟穿了件衣裳一样,罩在上头,第二层蚊子挤都挤不进去啦。你一赶,好,就跟那卫兵站岗一样,轮换着班来……那还有不叮死的!”
他奶奶听了很以为然,觉得儿子是死在自己手上的,竟一头栽进黄河。
郝三的妈,在当时也是这偏僻的河滩上的一只凤凰。原来她就守不住空房,曾在同一晚上约好两三个人,闹出不少笑话,成为庄子上茶余饭后的谈资,丈夫和婆婆都死后,碰上个从三盛公来这一带收羊皮的内蒙古人——听说那尕子长得又白净又精神,还唱得一口好“二人台”——没有认识两天,就撇下个不到两岁的娃娃跟那人跑了。
幸好,郝三已经断了奶,由他大伯收养下来。他大伯是个瘸子——这才没有被抓去当兵——一个人生活也够艰难的。饿了,大伯从炕洞里扒出个半生不熟的土豆撂给他;拉了,大伯从地上抓把土朝炕上一撒。日积月累,郝三等于在粪堆上睡着。大伯下地干活的时候,老是用根烂麻绳把他拴在炕上。有一天,他挣脱了烂麻绳想下地,却一个倒栽葱摔了下来,脸正好扑在炕洞旁边的掏灰筢子上。他大伯回来一看,他满脸是血,找了半天也没找见伤口在哪里。后来发现他一只眼窝瘪瘪的,才烧了些棉花灰捂住他的眼睛。
如此,他成了独眼郝三。
这样的娃娃,当然从小就受人欺负。打驴仗的时候,要是娃娃多毛驴少,独眼郝三就当驴让别的娃娃骑;柳拐子打飞了,要叫郝三用那只独眼去寻。可是,他魏天贵自小就照顾郝三,从没把他当驴骑过,还经常塞给他一点锅盔。别的娃娃打他,魏天贵总要替他报复,找个碴子也得揍那娃娃一顿。所以,郝三一直像一条忠实的狗一样跟着魏天贵。后来大了,魏天贵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苦恼,譬如对自己女人的不满等等,也会对他发发牢骚。他成了魏天贵的“布衣之交”。
既然是残废,就有他特殊的幸与不幸,幸运的是没受过当兵的苦,不幸的是娶不上老婆,解放以后还是条光棍……
“嘿,”他阴沉他说,“你的话也对。你的日子还真不如蹲劳改哩。”
“蹲劳改怕啥?三个饱一个倒,听说白穿衣服,一月还有几块钱零花哩,不就是干活嘛,我在外面不干活呀……”独眼郝三对蹲劳改很有兴趣,说得嘴角都冒出白沫。
“那你咋不去呢?”他冷冷地问。好像蹲劳改跟赶集一样平常。
“唉!蹲劳改还得有条件:要犯法,可我……”郝三眨眨独眼,沮丧起来。
“要犯法还不容易。”他脸上露出一丝阴险的微笑,指着那一群正在啃草的羊,“你把那羊捅倒几只。”
“哎哟,我的大书记咧!”独眼郝三往后一仰,两脚朝天地躺在防洪坝上,笑得全身打颤。“哈……你真能摆弄人咧……”
“你听着!”他猛地翻起身,揪着郝三的烂衣领,一把把郝三拽起来,咬着牙巴骨,下嘴唇可怕地向上蹶着。
“你怕,我不怕!我把那羊捅倒几只,你去蹲劳改!咱们俩一起让庄子上的人吃饱肚子,咋样?……”
他一口气把事情的原委和他的计谋和盘端给郝三。
“咦,没听说过,蹲劳改还派任务……”郝三听了以后,歪着脑袋,一边怔怔地寻思,一边嘀咕。
“行啦!那事是你寻思不透的,你干不干吧?”
郝三翻翻独眼,迟疑地看看他。真叫去蹲劳改,郝三又有点顾虑了。
“你要不去,谁去?你替我想想。”他动员郝三,“你去蹲个几年,全大队四百多号社员,一千多口人还能混口饱饭。回来了,你还是个你,有啥不好?”
“那,我得蹲几年?”
他望了望那群羊,算计着庄子上的户口,“顶多蹲四年,咱打得宽宽的:五只羊一年。咱们捅它二十只。”
“唔,四年,那还差不多。”郝三考虑了一会儿,表示同意。“舍不得娃娃打不了狼,你就领着大伙儿干吧。可你得分给我一条后腿,让我临走的时候吃顿好肉。”
“行!”他一拍郝三的肩膀,霍地站起来,“带刀子没有?”
那条古道又弯向河沿。驴车慢慢走进了一段两边长着茂密的芦苇的地带。岸边的涡流轻轻地激荡着细嫩的苇草,发出柔和的沙沙声。河中间,浪涛拍击着浪涛,传来清脆的啪啪声。黄河水永不停歇,永不沉默,但她从来没有泄露过自己子孙的秘密,譬如,她决不会泄露这两个庄户人在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年元月的某一天,在她几乎和地球一样古老的岸边,在一座人迹不到的悬崖下面,干的这件不可告人的勾当。
“啊嚯……啊嚯……”
两个人一致了以后,兴高采烈地把那群羊从尤小舟唱歌的河滩赶到一处背人的悬崖下面。他接过郝三的刀子,一刀一只,一刀一只……羊本来就没一点反抗的力气,他又是当过羊把式的,练就了一套疱了解羊的本事,二十只羊一眨眼就捅倒了。
两人先痛痛快快地趴在羊脖子的创口上喝了一顿羊血,才嘻嘻哈哈地回家。到了家,他先打发社员去把羊背回来,皮扒了,肉分给社员,肉下到锅里以后,他才跑到县上去报案。
第二天清晨,公安局派的民警就来了。郝三让人押着走到庄子头上,向他眨眨那只独眼:
“喂,别的没啥,房子你可替我看好了。过了四年,我还回来哩。”
看见郝三手上带着铐子,他突然动了感情,悄悄地叫了郝三一声“三哥”:
“你放心吧,三哥!”
郝三一辈子也没听人叫他一声“三哥”,听了后,立刻精神大振,挺起了胸脯,迈开了大步,回头说了句:
“你也放心,天贵,我死也不说!”
啊!星空啊星空。独眼郝三那颗微弱的星光,这么一闪就熄灭了。而在它熄火之前,却还有一阵回光返照……
出乎他意料的是,他把独眼郝三的“罪行”向县委书记贺立德汇报完以后,贺立德竟毫不怀疑,也不责怪他,而是神情庄重地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一只拳头在另一只已掌上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