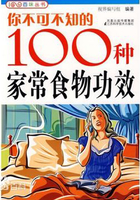第六卷5 (2)
菲洛特桑今晚更加闪烁其词。他不想明明白白地承认说,他让淑又回来,本质上与让她走所感到的忏悔毫无关系,而主要是一种人的本能面对习俗在极力逃避的表现。他说:“不错——我会那样做的。我现在对女人更加了解了。就一个在其它问题上有着我这些观点的人而言,不管让她走有多么公正,他都是几乎不合乎逻辑的。”
吉林厄姆看着他,心中感到疑惑,不知道是否会发生这样的事:世人对他的嘲笑和他自身的肉欲导致了他的这种反叛精神,这种精神不知是否会使菲洛特桑变得正统起来,从而残酷地对待她——这种残酷的程度,不知是否会超过他过去不拘礼节、刚愎任性的给予她的仁慈。
“我发觉凭冲动办事是不行的,”菲洛特桑又说道,每一分钟都越来越感到必须要依照自己的立场观点行事。“我过去面对教会的教义极力逃避,但我那样做并没有蓄意中伤的意思。女人对你的影响是很奇特的,她们诱使你去滥用仁慈。不过,我现在对自己认识得更加清楚了。明智地严厉一点,也许……”
“不错。不过你只能渐渐地勒紧缰绳,不要一开始就用力过猛。到了最终她便会服服贴贴的。”
这种告诫是没有必要的,尽管菲洛特桑嘴上没说。“在我同意放她走这件事上,我和沙斯托那位牧师发生了争执;之后我离开了那里,但当时他说的话我现在还记得。‘要想重新恢复你和她的地位,你惟一能做的就是承认你的错误,承认自己没有采取明智而强硬的手段将她约束住,然后如果她愿意的话把她重新娶回来,并在以后不要再动摇不定了。’不过我当时真是极其不受管束,对于他的话不屑一顾。可是离了婚后她竟然又想到重新回到我身边,这倒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埃德琳太太小屋子栅栏门咔嗒了一声,然后就有一个人朝着学校这边走来。菲洛特桑说了声“晚安”。
“唔,是菲洛特桑先生吗,”埃德琳太太说,“我正要来找你的。我刚才一直在楼上和她在一起,帮她打开行李。我敢向你保证,先生,我认为你们不该那样做!”
“什么——是结婚的事吗?”
“是呀。她是在强迫自己和你结婚,可怜又可爱的小东西。可你一点也不知道她现在是多么痛苦。我向来就不是很赞成也不是很反对宗教,不过我认为让她做这种事是错误的,你应该劝她不要这样。当然,你把她娶回来大家会说你这人太善良、太宽大仁慈了,但是我不这么认为。”
“那是她的意思,我只是同意罢了,”菲洛特桑严肃沉静地说,埃德琳太太的反对使他变得莫名地固执起来。“过去犯下的一个大错现在要纠正过来了。”
“我可不这么认为。如果她是谁的太太,那么她只是那个男人的太太。她为他生了三个孩子,他亲亲切切地爱着她,所以再极力劝她这样做真是一件邪恶可耻的事。她真是一个可怜的、老打颤的小东西!现在没有一个人站在她一边。惟一会成为她朋友的人,这个固执的东西又不准他接近她。我真弄不明白是啥东西首先使她产生了这种心情的!”
“我也说不清楚,不过当然不是我啦。就她而言,她完全是心甘情愿的。我现在也只能说这些了。”菲洛特桑生硬呆板地说。“你现在也反对起我来了,埃德琳太太,这可不恰当呀!”
“好啦,我早就知道我的话会冒犯你的,不过我不在乎。真的就是真的。”
“你并没有冒犯我,埃德琳太太。尽管如此,你一直是我很好的邻居。不过总得让我知道,怎样对我和淑珊娜才是最好的办法呀。这么说我想你不会和我们一起去教堂参加婚礼了?”
“不去,去了才该死呢……我真弄不明白这年头儿要怎么样了!现在这会儿,婚姻变得越来越严肃起来,一个人要结婚真会感到害怕。我们那个时候对婚姻可是比较随便的,但我并不觉得那有什么更糟的!我和我那个可怜的男人结婚时,请了整整一个礼拜的客,把教区的酒都喝光啦,后来不得不向别人借了两先令半硬币,才开始过起日子来!”
当埃德琳太太回她屋子去后,菲洛特桑忧郁地说:“我也不知道自己该不该这样做——无论如何也不该这么仓促。”
“为什么呢?”
“如果她真是违背本心强迫自己这样做——仅仅是由于对义务或宗教有了新的感想——那我也许应该让她稍微等一等再说。”
“既然你已走到这一步了,你就不应该打退堂鼓。我就是这么看的。”
“我现在是不能推迟了,这倒是真的。不过当她看见那张结婚证发出了轻微的叫声时,我是感到疑虑不定的。”
“瞧,别再疑虑不安了吧,老朋友。我明天早晨就要作她的主婚人了,你也要娶她了。我总是感到后悔当时没有更多地阻止你放她走,现在我们已走到这一步,如果我不帮助你把这件事纠正过来,我是不会甘心的。”
菲洛特桑点了点头,看见自己朋友多么坚定可靠,他也更加坦率起来。“毫无疑问,等我所做的事被人们知道以后,很多人都会认为我是一个软心肠的傻瓜。可是他们对于淑并不像我这样了解。尽管她这人非常难以捉摸,从根本上说她的本性是诚实正直的,我并不认为她曾做过违背良心的事。她和福勒共同生活过的事实丝毫不能代表什么。当她离开我向他奔去的时候,她认为并没有超出自己的权利范围。而现在她的看法不同了。”
第二天早晨,这两个朋友一致默认了(尽管他们各自的观点立场不同),让那个女人在圣坛上作自我牺牲——就在她自以为是原则的圣坛上。八点过几分钟,菲洛特桑就到寡妇埃德琳的家去接淑了。前一两天低地里的浓雾已经弥漫到了这个地方,草地上的树丛大抱大抱地积满了不少的雾,然后把它变成大颗大颗的露珠,像阵雨似地滴落下来。新娘已戴上帽子在那儿等着,一切都准备就绪。在这个灰色的晨光里,她看起来太像她名字所意味着的百合花了——她有生以来还从没这么像过。她深受苦难,愤世嫉俗,满怀悔恨,紧张的神经也使得她的身体深受其害;她的形体看起来比过去更加瘦小了,虽然淑在最健壮的时候也未曾是个魁梧的女人。
“你真快,”小学教师说,宽宏大量地握住她的手。但是他克制住自己的冲动不去吻她,因为他还记得昨天她被惊吓的事,这事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使他郁郁不乐。
吉林厄姆也来到了他们身边,然后他们就离开了埃德琳寡妇的家,老太太仍然坚决不去参加婚礼。
“教堂在哪里?”淑问。自从旧教堂被拆除后她就再没来这里住过,再加上由于自己现在心事重重的,所以新教堂也忘记了。
“在前面,”菲洛特桑说,跟着浓雾中便隐隐地呈现了教堂那高大庄严的尘塔。牧师已经进教堂去了,待他们进去时他高兴地说:“我们几乎得点上蜡烛了。”
“你真的——希望我嫁给你吗,理查德?”淑气喘吁吁地耳语道。
“当然,亲爱的:这个希望超过了世上的一切。”
淑不再说什么了。而他有两三次都感到,他以前将她放走时的那种人性的本能,现在并没有坚持到底。
他们伫立在那儿,一共五人:牧师、执事、他们两个和吉林厄姆。跟着他们那神圣的婚礼便再一次举行。在教堂的中殿里有两三个村民,当牧师念到“上帝所配的”时,村民中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的确是上帝所配的呀!”
这真像是他们先前自身的幽灵,在同样的情景下重复着婚礼一般,只不过第一次婚礼是多年以前在梅尔彻斯特举行的。当他们在结婚薄上签了字之后,牧师就祝贺这对夫妇,说他们的行为又高尚、又正直、又仁慈。“结局好则一切均好,”他微笑着说,“你们已‘从烈火中得救’,我祝你们俩终身幸福。”
他们沿着几乎空无一人的教堂走出去,然后回到校舍去了。吉林厄姆想那晚就回家,便早早地离开。走时他也向这对夫妇表示了祝贺。“瞧,”他和菲洛特桑分手时说,菲洛特桑单独送了他一段路,“这下我可以给你们当地的人讲述一个美好圆满的故事了。他们一定会称赞你们说‘做得好’。”
这位小学教师回来时淑正装着做什么家务,好像她原来就住在这儿似的。可是他一走近前来她便显得有些胆怯;一看见这种情况他心里又产生了内疚。
“亲爱的,我当然不会来打扰你,咱们还是和从前一样各过各的,”他严肃地说,“咱们这样做只是在社会上对自己有利而已,这就说明咱们的行为是对的——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原因。”
淑这下脸上才露出了一点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