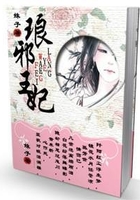第一章五十六
他们的谈话被监狱长打断了,他站起来宣布探视时间结束,应该分手了。涅赫柳多夫站起来,和薇拉?叶夫列莫夫娜告辞,向门口走去,随后在门口停下来,观察周围发生的事。
“先生们,到时候了,到时候了!”监狱长说,他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坐下。
监狱长的要求只是在停留在房间的犯人和探监人中间引起了一阵特别的喧嚷,谁也不想离开。有些人站起来,站着说话。一些人开始告辞,掉了眼泪。特别感人的是那位母亲和患痨病的儿子。年轻人一直在摸弄那张纸,他的面部表情变得越来越气愤,他做出极大努力来克制自己不受母亲情绪的感染。母亲听到要分手了,就伏在他的肩头痛哭,鼻子发出哧哧响声。长着羔羊般眼睛的姑娘(涅赫柳多夫不由自主地注视着她),站在那个痛哭的母亲面前,说着什么话安慰她。戴蓝眼镜的老人站在那里,握着女儿的手,对她说的话直点头。那对热恋的年轻人也站了起来,手拉着手,彼此相视无言。
“瞧这一对儿倒是挺快活!”穿短夹克的年轻人站在涅赫柳多夫身边,像他一样瞧着这些告别的人,单指那一对热恋中的情侣说。
那热恋中的一对儿,穿古塔胶短上衣的年轻人和淡褐色头发的姑娘,感觉到了涅赫柳多夫和那个年轻人的目光,便把拉在一起的手伸出来,向后仰头,嘻笑着开始转圈。
“今天晚上,他们在这里,在监狱里结婚,她跟随他去西伯利亚。”那个年轻人说。
“他是什么人?”
“苦役犯。让他们快活一下吧,不然,听到这里的声音太让人难受了。”穿夹克的年轻人听着患痨病男子的母亲的痛哭声说道。
“先生们,请,请吧!不要逼我采取严厉的措施!”监狱长说,同样的话重复了好几遍。“请吧,请快点!”他犹豫不决地轻声说,“这是怎么回事,早就到时间了。要知道,这样不行。我说最后一遍!”他无精打采地说,一会儿抽自己的马里兰香烟,一会儿又把它熄灭。
很明显,不管那些容许人们做危害他人的事而久不为此承担责任的理由多么高明,多么古老,多么习以为常,监狱长却不能不意识到,他毕竟是造成这个房间所表现出来的痛苦的罪人之一,他显然非常难过。
最后,犯人和探监的人开始分手了。犯人走里边的门,探监的人走外边的门。男人们,穿古塔胶短上衣的和患痨病的,还有黑皮肤、头发蓬乱的走了出去,玛丽娅?巴夫洛夫娜和那个在监狱里诞生的小孩也走了。
探监的人也开始走出去。那个戴蓝眼镜、步子沉重的老人走了,涅赫柳多夫也跟在他后面走了。
“是啊,这些制度令人吃惊!”那个爱说话的年轻人好像继续他被打断的谈话,和涅赫柳多夫一起下楼时说道,“还得谢谢那个上尉,他是个好人,不死守规章。大家把话说个痛快,心里也就舒服点了。”
“难道在别的监狱里没有这样的探视吗?”
“唉呀,没有这样的情况。愿不愿意都得一个个见面,还要隔着铁丝网。”
当涅赫柳多夫和梅登莱夫(那个爱说话的年轻人这样介绍自己)来到前室的时候,监狱长面带倦容朝他们走过来。
“如果您想见马斯洛娃,那么,请明天来吧。”他说,显然希望向涅赫柳多夫献殷勤。
“很好。”涅赫柳多夫说完,匆匆走了出去。
显然,梅尼绍夫无罪而遭受痛苦是可怕的——这痛苦与其说是肉体上的,不如说他看到那些无缘无故折磨他的人如此残酷,势必感到困惑,不再相信善良和上帝。可怕的是,上百个根本无罪的人,仅仅因为证明文件上写得不对就让他们遭受羞辱和折磨;可怕的是,这些折磨自己兄弟的昏头昏脑的看守,竟相信他们在做一件重要的事。然而,他觉得最可怕的是,这个年老体衰、性格善良的监狱长却不得不拆散母亲和儿子,父亲和女儿——而他们却是像他本人和他的子女一样的人。
“这是为什么?”涅赫柳多夫问,这时他非常强烈地感受到一种他每到监狱就体验到的从精神上转变成生理上的恶心感觉,却找不到问题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