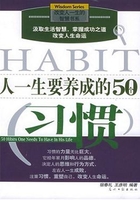尽管如此,进化论哲学仍然把一般物质上获得成功的解释方法,毫不犹疑地扩展到有生命的事物上。进化论哲学首先告诉我们,知性是进化的局部成果之一,是一道光,也许只是偶然性的一道光,却照亮了生物经过狭隘信道的情景,而这信道是专为生物活动而开辟的。然后,进化论哲学突然忘了刚才说过的话,把地下道使用的提灯扩大成可以照耀世界的“太阳”。进化论哲学勇敢地携带着“概念性思考”的武器,意图从观念上重建万物,包括生物在内。可是,它在途中遭遇了许多难缠的问题,知道自己的逻辑已陷入种种奇异的矛盾,只得赶紧放弃原有的野心,说:“我们要重建的不再是实体(r6alit6)本身,而是实体的模拟,甚至只是实体的象征形象。事物的本质我们无法掌握,今后也势必如此。我们只在相对关系中绕动,绝对者不属于我们的领域。我们只好在‘不可知’之前停步了。”过分夸耀人类的知性之后,现在却又太谦虚了。如果生物的知性形式是根据身体及其物质环境间的交互作用与反作用才慢慢形成,大概无法向我们提示构成身体的本质。行动不可能在非实体中产生。若就为思辨或梦想而生的精神而论,我承认这种精神一直都停留在实体之外。这种精神也许会歪曲实体,或使实体变形;也许会像我们凭借想象从流云中截取人和动物的形象一样,创造实体。如果有一种知性注意到从这实体中产生的作用及继之而起的反作用,并一面摆弄对象,一面不断接受这对象的流动印象,那便是可触及绝对者的知性。如果哲学不提示我们,思辨会碰到什么矛盾,会走进什么死胡同,我们大概不会想到:认知竟然会怀疑这种绝对价值。这些难题和矛盾所以会发生,主要是因为我们把习惯性的思考形式用于知识活动所不能达到的对象,从而也用于思考范畴无法创出的对象。知性认识假若与无生命物质的一种面貌发生关连,一定会向我们提示忠于这物质的印刷品,因为知性认识已根据这特定对象制版。知性认识忘我地把生命——亦即制作印刷品的印刷工人——重现出来,不会坠入相对中。
这么说来,是不是必须放弃探索生命的本性呢?是否应该心甘情愿接受知性赐予的机械论生命观呢?这种生命观无论如何是人工的、符号的,因为这种生命观将生命的整体活动缩小成人类活动的一种形式,而这人类活动的形式只是部分生命的局部表现、生命作用的结果或残渣之一而已。
如果为了创出纯粹的知性,亦即为了培养几何学者,生命耗尽了它所涵盖的内心潜力,我们也许必须心甘情愿接受机械论的生命观。可是,追溯人类的进化路线并非只有一条。其它不同的意识形态经过不同的路途已逐渐发展起来。这些意识形态一如人之知性,不能使自己免于外在的束缚,或夺回自己,却能表现出进化运动的内在本质。如果将这些意识形态汇集为一,再与知性融合,难道不能获得与生命同样辽阔的意识?这种意识,难道不能抵抗自己背后所感受的生命冲力,再突然回顾而展望生命的全景?即使是瞬间也好。
有人可能会这么说:“因为这样展望,我们并不能超脱自己的知性,因为我们到底还是凭借知性,经由知性来观看其它的意识形态。”如果我们只是纯粹的知识人,我们的概念性逻辑思考四周没有一抹微云,这说法也许正确。可是,其中却有云影飘荡,而这云影是由那辉耀核心的同样素材形成;这辉耀的核心,我们称之为知性。云影中也含有补充知性的能力,只要我们闭锁在自我中,就可以朦胧地感觉出来0这些能力一旦在自然进化中发挥作用,大概就能清楚分辨,因此,这些能力也许会发觉要沿着生命的方向加强并扩大自己,必须多么努力。
总之,认识论和生命论似乎不能分离。生命论如果不伴随认识批判,就不能不全盘接受知性任意使用的概念。这种生命论会把既存范围看成稳固不动之物。不论喜欢与否,强把事实纳入这些范围,便会产生了方便的符号主义。这对实证科学也许必要,但无法直接观看对象。另一方面,认识论无法使知性回归生命进化的原有场所,所以无法告诉我们,认识的范围如何形成,要怎样才能扩大或超越这范围。生命论和认识论这两种探索方法必须互相结合,必须经由循环过程,不断互相往前推展。
这两种探索方法如果互相契合,一定能够用与经验更密切结合的确实方法,解决哲学所提及的重要问题。如果两者的共同意图能顺利进行,一定会让我们亲眼看到知性形成的现场,从而也会看到物质在知性所描绘的轮廓中如何产生。这两种探索方法会把自然与精神挖掘到根深之处;同时展示出真正的进化论,以替代斯宾塞的假进化论。斯宾塞的进化论是把目前已经进化的实体分割成同样进化的碎片,然后再用这些碎片重构实体,因而预先肯定了所有必须加以解释的事物。真正的进化论则须依据实体发生与成长的过程加以追踪。
可是,这种哲学非一蹴可及,所谓哲学体系类皆天才的成品,而且有所取舍,以提示一个整体形象。但这种哲学却不同,必须在思想家中加进观察家,互相补充、修正,并且经过集团性的渐进努力,方有所成。因此,这篇论文无意于解决所有极其重要的问题,只能确定解决的方法,并在若干本质点上提示这方法运用的可能性。
本文的构想是由主题决定的。在第一章里,我们尝试让进化过程穿上借知性缝裂的两套旧衣——机械论与目的论。由此可知,这两套衣服都不合身,如果重新裁制,以改变其体裁,又会比另一套宽大。在(第二章)里,为了超越知性的见解,我们除了抵达人类知性的进化路线之外,还想尽力去重现一些生命所走的重要进化路线。于是知性被带回到自己的成因。接着而来的课题就是掌握这成因,以追踪其运动轨迹。在第三章中,尽管不周全,我们仍然努力为之。在最后的第四章,应该提示一种现象,那就是:我们的知性也须经过一种训练,才能作为超越知性的哲学基础,因此必须展望一下各种体系的历史,并分析人类知性开始思索普遍实体以来所展现的两大错觉。
1生命的进化——机械论与目的论
持续
在存有中,我们最确定又最熟识的显然就是我们的“存有”。我们对其它事物所怀抱的观念也许会被认为是外在的、肤浅的;反之,我们却从内在深入地知觉自己。这时,我们确认什么呢?在这难得的情况下,“存有”这个词究竟何所指?在此必须先简单回忆一下以前发表的论文结语。
我确认,我会从一种状态转移到另一种状态;会时而觉得寒冷,时而觉得炎热;会忽喜忽悲;会忽而工作,忽而休息;时而注视四周,时而思考其它事物。感觉、感情、欲望、表象,这种种样态分有了我的“存有”,并将存有逐一染上色彩。总之,我时时变易。可是,仅这样说并不充分。变易比起初所思还要根本。
其实,我仿佛是说,我的各种状态都自成格局。不错,我说:我常变易;而且在我看来,这种变易含蕴在从某一状态到另一状态的转移中。如果只取某一状态来看,这状态似乎恒常不变。若稍微仔细观察,就可知道,无论情感、表象或欲望,莫不瞬息自变。如果这一心态停止不变,其持续(durte)之流也可能会停顿。兹以最安定的内在状态——不动对象的视觉来说,这对象恒常处于同一状态;我又从同一方向、同一角度、同一光线下观看,这对象似乎不变。其实不然,我现在所看的事象跟刚才所看的事象毕竟不同,因为事象瞬息即过。我有记忆,常把过去一些现象带进现在。我的心态一直循着时间之路前进,并因累积的持续日益扩展,一如以自己为中心来推雪人一般,感觉、情感、欲望这些较深奥的内在状态更是如此,因为它们不会像单纯的视觉那样,与不变的外物相对应。不过,起先我们不会注意这时时刻刻的变易,直至变易逐渐增加,为身体带来新局面,把注意力引到新方向,才比较容易注意到这种变易。就在这刹那,人才发觉自己的状态已经变了。其实,人不断地变,状态本身本来就是变动的。
总之,从一状态到另一状态的变动跟同一状态的持续,彼此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异。“同一”状态若比我们想象更富于变化,则从某一状态到另一状态的转移,竟意外地与同一状态的延续相类似。变易是连续性的。可是,我们对自己心态的不断变易往往并不注意,直到变易极其显著,引起注意,我们才觉得新的状态跟前一状态有关连。我们也常以为这新的状态恒常不变,就这样持续下去。因此,我们的心理生命乍看似乎并不连续,因为我们的注意力是经由一连串的非连续性作用才推向这个心理生命。换言之,在只有一条平缓坡道的地方,我们常经由注意作用的折屈,才以为看到了阶梯。我们的心理生命的确充满了不能预期的事物。无数事象喷涌而出,似乎跟前出者完全不同,又跟后来者毫不连接。其实,这些事象所展现的非连续性,是在这背后的连续上浮现的,都画在背景上;隔离这些事象的间隙也来自这背景,就像交响乐中隔段时间敲起的大鼓,因为这些鼓声比较能引起我们关心,我们的注意力才投向它们。不过,每一鼓声都得到涵盖我们整个心的流动体支持,而这些鼓声则是动带上最明亮的点。这动带包含了感觉、思考与欲望,亦即包含我们在某特定瞬间所认定的一切事物,整条动带构成了我们原有的状态。如果这样界说状态,那么,所谓状态就不能说是彼此分开的要素。其实,状态彼此互相连续,构成了一条无边无际的长流。
可是,我们的注意力却把这些状态加以人为的区分,以致不得不用人为的绳索把它们串接起来。因此,我们的注意力假定了一个无形、无差别、不动的自我,把各种心态看成独立的个体,而这些心态都在自我上联成一串,没有界限的颜色互相渗透、流动,但我们的注意力却把这些看成清楚分别的固定色彩,视之为色彩缤纷的珍珠项链。接着又假定有一条固定的绳子,把这些珍珠连在一起。如果这无色基体不断涂上色彩,这基体依然不确定,对我们来说,等于不存在一样。其实,我们所知觉的只是涂上色彩的东西,亦即各种心态。事实上,这“基本”并非实体,对我们的意识而言,只是符号而已。虽然有流动的连续,我们的注意力却把各种状态并列,而且因为这符号,才让意识不断记起这种运作的人为性格。如果我们的存有是由分离的各种状态组成,而不为所有东西所动的“自我”必须把这些状态综合起来,对我们来说,持续可能不存在。因为不变的自我不会绵延持续。一种心态若不为下一心态所取代,就会自我认同,不能绵延持续。以此观之,把这些状态在“自我”的基体上排成一列,真是白费气力。这些在某固体上联成一串的固体,决不会创出流动的持续。如此获得的只是内在生命的人为模造品,是静态的等价物;真正的时间便从等价物中消逝,而更适合逻辑与语言的要求。可是,在这些记号覆盖下流动的心理生命,已简明地显示,时间才是它的基体。
而且,没有一个实质的基体这么有持久力,因为我们的持续并非一个刹那为另一刹那所取代,若然则除现在之外别无其它。总之,过去不会延长到现在,进化也没有具体的持续。所谓持续乃过去的连续进展,而过去则是紧咬着未来前进,并且逐渐膨胀。过去不断扩张,保存至无限。就像我们以往曾经尝试证明那样,所谓记忆并不是把回忆整理放进抽屉,或记在账簿上的能力。记忆里没有抽屉和账簿,确实地说,甚至连能力也没有。若有能力,那就会在需要或可能的时候断续工作,但过去的累积不会中断。其实,过去会自动自力地保存下去。过去在所有刹那都以整体跟从我们。我们幼时的感受、思考和希望都蕴涵其中,随即延展到现在,而欲与现在合而为一,乃向不想接受自己的意识之门拥过去。大脑的结构已经完成,所以把过去几乎全部推进潜意识里,只照映出现时的处境,或辅助正在准备中的行动,换言之,只提供有用的工作,让它通过意识;充其量只让一些多余的回忆从半掩的门扉中潜入。这是潜意识的使者,来告诉我们那些我们没有发觉的潜入之物。不过,即使对过去没有清楚的概念,我们仍然会模糊感觉,我们的过去已留在现在之中。如果我们不是出生以来历史的凝聚,那末,我们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性格又是什么?岂止如此,甚至可以从出生以前算起,因为我们带有出生以前的禀赋。当然,思考时,我们只用了自己过去的一小部分。可是,在我们需求、意欲或行动时,却用了我们过去的全部,其中还包含天生的心理趋向。以此观之,成为表象的只是我们过去的一小部分,但是我们的过去会利用自己的推进力,以趋向这种形式,毫不保留地出现在我们面前。
过去如此保存之后,意识不可能再度通过同一状态。不管环境多么相同,环境中的人却不再是同一个人,因为环境在这人的新历史点上攫住了他。我们的人格是蓄积经验,在每一刹那间形成的,所以不断变化。人格是变易的,每一状态表面看来似乎相同,然而在其深处则不许重复,所以我们的持续是不能逆转的。即使是持续的绝小部分,也不能重新加以体验,否则我们将废弃其后发生的所有记忆。严密地说,我们即使能够从知性中除去记忆,也无法从意志中加以消除。
因此,我们的人格不断成长,肥大,成熟。人格的每一刹那都有新物添加于旧物之上。尤有进者,每一刹那都是全新的,也是不能预测的。现在的状态可以用内有之物和从外向内发挥作用之物来解释,即使分析我现在的状态,想必也找不到其它要素。纵有超人之智也无法预见单一不可分的形式,这种形式常将具体的组织赋予完全抽象的要素。所谓预见是指把过去知觉者投影于未来,或者依不同的顺序重新收集已知觉的要素,以待将来表现。可是,不曾被知觉的单一,必然不能预见,如果以流动的历史瞬间来观看我们的每一状态,结果正是如此。我们的每一状态都是单一,而且不能被知觉的,因为所有已经被知觉的东西和现在附加的东西都被凝聚在状态的不可分性之中。我们的每一状态都是独创历史中的独创刹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