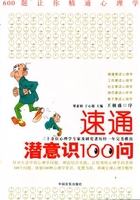看到这里,柏纳不得不暂停。他的眼睛模糊了。他喘着气,就像他对日记的渴切使他忘了呼吸。他打开窗户,在重新潜下去之前吸满空气。他跟奥利维的友情无疑是深厚的,他没有比奥利维更好的朋友,现在,在他已不能再爱他父母之后,世界上也已没有他更爱的人了,真的,他对这种情感的执著也几乎到了过分的程度,但是奥利维和他对于友情的看法并不尽同。柏纳一边读下去一边既惊奇又赞叹,同时又免不了微微的痛苦——他自以为认识得如此清楚的这个朋友竟可以是这样多面的。奥利维从没有告诉过他日记中所载的这些。他儿乎全不知道阿芒与萨拉的存在。奥利维对他们的样子跟对他的样子是多么不同啊!在萨拉的屋子中,在那床上,柏纳能认得出他的这个朋友来吗?他猛烈的读下去固然是由于强烈的好奇,但里面也搀和着一种奇怪的不舒服的感觉——厌恶或愠怒的感觉。不久以前,当他看到奥利维与艾杜瓦臂挽臂的时候,他感到过这种愠怒——愠怒于自己被排除在外。这种愠怒可以把人带上很远的路,叫人做出许多蠢事来——就像所有愠怒一样。
好啦,我们可以继续了。我这里说的这些话都只是为了在日记中间透透气。现在柏纳已经透过了,我们再回来吧。他又钻进去了。
艾杜瓦日记:初访拉?柏厚
能寄望于老人者甚少。
11月8日——老拉?柏厚夫妇又搬家了。他们的新公寓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去过,那是在福堡?圣昂诺街的一个半楼,坐落在跟浩斯曼大道还没有交界的地方,是个相当隐蔽的住所。我按门铃。拉?柏厚开门。他穿着衬衫,头上戴着像似白白黄黄的睡帽,最后我才看清是一只旧长袜(当然是拉?柏厚太太的),打了一个结,以致袜脚垂在他的面颊边像一个穗子。他拿着一根弯曲了的拨火棍。显然他正在做家事,看到我似乎相当不好意思。
“那么我等下再来好吗?”我问。
“不——不用了……进来吧。”他把我推到一间又长又窄的屋子,两扇窗子对着街,正好跟街灯一样高。“我正在等一个学生,”(那时六点)他说,“可是她打电报来说她不能来。看到你我真是太高兴了。”
他把拨火棍放在一张小桌子上,就像他想为现在这个样子道歉似的说?
“拉?柏厚太太的女仆让炉子灭了。她只有早晨才来,我不得不自己掏一掏灰。”
“我可以帮你生火吗?”
“不用不用,脏得很……对不起失陪一下,我过去把外套穿起来好吗?”
他拖着脚步走出去,几乎立刻又走回来,穿上了一件羊驼毛的外套,扣子已经脱落了,胳膊肘都有破洞,整个已经破旧不堪,让你觉得送给乞丐也拿不出手。他坐下来。
“你看我变了吧,是不是?”
我想否认却找不出任何话来,他那受尽折磨的表情让我感到非常痛苦,他的脸曾经是?那么好的。他接着说:
“没错,我最近老得很快。我开始记忆力衰退。当我弹奏巴哈的赋格曲的时候,非得看乐谱不行……”
“有很多年轻人如果能有你这样的记忆力还会高兴得不得了呢。”
他耸耸肩回答:“哦,不只是我记忆力的问题,臂如说,我还以为我走路走得很快,可是街上每个人都赶过我去。”
“哦我说,“现在的人走路都快多了。”
“不错,是这样吗?我教的课也是一样——学生们都觉得我教得慢,在拖住他们,他们要走得比我快。我越来越没有学生啦……现在人人都求快。”
然后他用我几乎听不到的低声说:“我几乎一个都没有了。”
我觉得他是那样的沮丧,以至不敢问下去。
“拉?柏厚太太是不会了解的。她说我做得不对一我没有想办法留住他们,更没有想办法招新学生。”
“你刚刚在等的那个学生呢?”我笨拙的问。
“哦,她!我在教她准备考音乐学校。她天天到这里来练习。”
“这是说你并没有收她的钱?”
“拉?柏厚太太总是为了这个责备我。她不明白这是我惟一还觉得喜欢的课程,对,我惟一想教的课程……最近我想了很多,哎!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书里都很少谈到老年人呢?我猜是因为老年人没有那个能力写自己的事,而年轻人对他们也不感兴趣。没有人对老人关心的……可是老人也有很多可怪的事可以让作家们去说。譬如,我这过去的一生里有些行为到现在我才开始了解。对,现在我才开始了解它们的意义和我当时做的时候所以为的意义完全不同……我现在才开始了解,我整个这一生都是个受愚弄的人。拉?柏厚太太愚弄我;我的儿子愚弄找;人人愚弄我;高特愚弄我……”
夜色四合。我已经分辨不清我的老师的五官了,但街灯突然亮起,照见他的脸闪着泪光。一开始我困惑地看着他太阳穴上的一个奇怪的斑痕,像一个小洞,但他动了一下,那斑痕的位置改变了,我才看出那是栏杆的结头投上来的影子。我把手放在他枯瘦的胳膊上,他打了个颤。
“你会着凉我说。“真的,我们把火生起来好吗?来吧“不用不用,人应该坚忍。”
“什么?斯多噶主义?”
“不错,有一点。就是因为我喉咙弱我才从来不围围巾。我一向都是跟自己奋斗。”
“在人可以胜利的时候这当然不错,但在人的身体脆弱的时候……”
“那才是真正的胜利。”
他把我的手脱开,说下去:“我原来怕你不来就走了。”
“走到哪里去?”我问。
“我不知道。你到处旅行。我有些话要告诉你……我料想自己不久也要走了。”
“什么!你也想旅行?”我拙笨的回答,装出不懂他的话的意思,尽管他语音的严肃再明显不过。他摇头。
“你很清楚我的意思……真的,真的。我知道时间快了。我赚的钱开始不足以维生,我忍受不了这个。有一个地步是我不允许自己超过的。”
他说话的语气让我惊惧。
“你认为这不对吗?我从不了解为什么宗教禁止这种事。我最近想了很多。年轻的时候,我过的生活非常严苛,每次我拒绝了街上的拉客,我都庆贺自己性格的坚强。我不了解,在我自以为将自己解脱了的时候,事实上我正越来越变成了我的骄傲的奴隶。每当我战胜自己一次,就是把我牢狱的钥匙又转动了一下。这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说高特愚弄了我。他让我以我的骄傲为美德。他在嘲笑我。他以此为乐。他把诱惑送到我们面前,而他明明知道我们是不能抗拒的;但是当我们杭拒的时候,他却更肆行报复。为什么他这么恨我们呢?为什么……瞎,我在用这些老人的问题烦你了。”
他像个郁郁不乐的小孩子一样,捧住头,沉默下来,沉默得如此之长,以至我怀疑他是不是忘了我在旁边。我一动不动的坐在他面前,生怕打断了他的静默。街上的声音虽然如此近,小屋里的安静却让我感到特别,而尽管街灯把它怪异的光从下面投到我们身上,像戏台上的脚灯一般,窗子两边的暗影却似乎在扩张,而我们四周的黑在增厚,就像冬天
静潭的水越结越厚终于变得动弹不得——直到我的心也结成了冰。最后,为了摆脱那夹
住我的钳子,我大声呼吸,并为告辞做个预示,也为了打破那寂静的迷咒,我出于礼貌的问:
“拉柏厚太太好吗?”
老人似乎从梦中醒来。他重复一遍:
“拉?柏厚太太……”是问句,就像那些字只是声音,对他来说完全丧失了意义,然后他突然俯身向我:
“拉?柏厚太太的状况非常可怕……是我最痛苦的事。”
“什么样的状况?”我问。
“噢,什么样也不是,”他说着,耸肩,就像无可解释似的。“她心眼完全不清楚了。她不知道卜一步该怎么样。”
我早就猜测到这对老夫妇很不相契,但从没有想要知道什么确定的内容。
“我可怜的朋友,”我悲悯的说,“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想了一下,就像不了解我的意思似的。
“噢,很久了……从我认识她以后一直是这样。”然后,又几乎立刻更正:“不,实际上是由于我儿子的教养问题才出了差错。”
我做了个吃惊的样子,因为我一向以为拉?柏厚没有孩子。他把原先用手捧着的头抬起来,安静的说:
“我从没有向你提到过我的儿子吗,呃?好吧,我统统告诉你。你现在一定要统统知道。再没有别人是我可以告诉的了……没错,是为了我儿子的教养。你明白,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结婚的头几年过得很快活。当我娶拉?柏厚太太的时候,我非常纯洁。我用纯粹的心爱她……对,这就是正好的字眼。而且我也绝不承认她有任何缺瑕。但是我们对孩子的教养却有不同的想法。每次我要责备我儿子的时候,拉·柏厚太太都站在他那一边反对我,照她的意思,孩子爱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她教他扯谎……在他刚刚20岁的
时候,他就有了情妇。她是我的学生——个俄罗斯女孩,极有音乐天赋,我非常珍惜。
拉?柏厚太太统统知道,但当然,他们照例事事瞒我。而我也当然不知道她要有孩子了。一点也不知道——我对你说,我从没有料想到。有一天——那天天气很好——有人来通知我说我的学生不舒服,不能来上课。我说我去看她,可是那人却说她已经换了衣服——要出门旅行…—只有到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她到波兰去做月子。我儿子到那里去跟她一起住……他们一起住了几年,没娶她他就死了。”
“呃——她呢?你后来看过她吗?”
他似乎在用头撞什么东西:
“我不能原谅她对我的瞒骗。拉?柏厚太太现在还和她通信。当我知道她很贫困的时候,我为了孩子给她送了一些钱去。但拉?柏厚太太不知道。她自己……也不知道钱是我的。”
“你的孙子呢?”
一阵奇异的微笑从他脸上闪现,他站起来。
“等一下。我拿他的相片给你看。”他又拖着脚步走出去,头斜伸在前面。当他回来的时候,手颤抖着在一个大信件夹里找相片。他把相片拿给我,向前弯着腰,小声地说:
“我从拉?柏厚太太那里拿来的,她不知道。她以为弄丢了。”
“他多大了?”我问。
“13岁。看起来还大一点,是不是?他单薄得很。”
他眼里又充满了泪,他伸手要相片,像急着要尽快把它拿回去似的。我倾身向前在街灯的幽光中看它,我觉得那孩子像他,在那孩子脸上我认出老拉?柏厚又高又突出的前额和梦幻般的眼睛。我以为我这样说会让他高兴,他却提出异议:
“不不;他像的是我弟弟——我故去了的……”
那孩子奇异的穿着俄罗斯式的镶边宽大短外套。
“他住在哪里?”
“我怎么知道?”拉?柏厚叫道,声音是绝望的。“他们什么都瞒住我,我告诉你。”他把相片拿过去,又看了一会儿,然后放回信夹里,又把信夹塞进口袋。
“当他的母亲来巴黎的时候,她只见拉?柏厚太太,如果我问到她,她总是说:‘你最好问她自己去。’她说是这样——,但她心里恨我去看她。她一向就嫉妒。她一向就处心积虑要把我任何放在心上的东西抢走……小柏利在波兰——我想是华沙吧——受教育。但是他常常跟他母亲旅行。”接着,在激动中,他说:“喚,你会相信人能够爱他从没有见过的人吗?哎,这个孩子是我在世界上最放在心里的人了……可是他却不知道!”
他的话被强烈的啜泣打断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投进——几乎是跌进——我的手臂里。为了让他得到一些安慰,我什么都愿意做——但我又能做什么呢?我站起来,因为我感觉到他那可怜枯萎的身子要溜到地上去了,我甚至觉得他要跪下去了。我扶他起来,抱着他,像孩子一样摇他。他又镇静下来。拉?柏厚太太在邻间叫他。
“她要来了……你不想见她吧,是不是?再说,她也聋得像石头。快走吧。”在他送我到楼梯平台的时候,说:
“不要隔太久的时间才来。(他的声音中带着恳求)再见,再见。”
11月9日——在我看来,似乎有一种悲剧到现在为止还几乎完全没有被文学掌握过。小说处理命运的对比:好运与厄运,社会关系,情的冲突,性格的冲突——但从没有处理过人类生存的基本本质。
然而,基督教的整个效果却是要把人的戏剧转到道德层面。但不苟且的说,从没有过基督教的小说。有些小说,它们的目的在教育,但这跟我说的毫无关系。道德悲剧——譬如说,那种把福音书中的一句话做令人惊惧的阐释的悲剧:“若盐失了味,又用什么来咸呢?”——我关怀的是这种悲剧。
11月10日——奥利维考试的日子快到了。宝琳要他毕业以后去投考师范学校。他的生涯都已规划好了……如果他没有父母,没有亲戚就好了!我可以让他做我的秘书。但是他从没有想到过我,他甚至没有留意到我对他的关切,如果我表露,他会困窘。就是为了不让他困窘,我在他面前才装出漠然的样子,装出有距离的样子。只有当他不看我的时候我才敢好好看他。有时候我在街上跟在他后面而不让他知道。昨天我也是这样,可是他突然转身,我来不及躲。
“你这么忙着去哪里?”我问。
“噢,没特别要去哪里。我没事做的时候总好像特别匆忙似的。”
我们互相走近了几步,但找不出什么话说。他必定因为这样的相遇而恼起来。
11月12日——他有父母,哥哥,学校里的朋友。我整天这样告诉自己——没有容我的余地。如果他有什么欠缺,我当然可以为他弥补过来,可是他却什么也不缺,他什么也不需要。若说他的甜美使我快乐,其中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允许我自我欺骗的……噢,蠢话,可是我还是写了下来,而这正揭发了我内心的双重性……我明天要去伦敦了。我突然下定决心走开。是时候了。
为了太想留下来而走!一种对艰苦的爱——对放纵的恐惧(我是指对自已放纵)或许是我清教徒教养的一部分,是我发觉最难摆脱的。
昨天,在史密斯书店,买了一本笔记本(已经是英文的了),打算继续写我的日记。我不再在这本上写了。一本新的笔记本!
啊!如果我能够把我自已抛开!
柏纳与洛拉
生活中有时会发生意外,但要善加利用则需要一点疯狂。
柏纳最后读到的是艾杜瓦夹在日记后面洛拉的那封信。他突然明白了真相,那在信中说着如此恳求的话的女人再无可疑的就是昨天晚上奥利维跟他讲到的那绝望的女人了——也就是文桑?莫林涅抛弃的情妇。再者由于奥利维的话和艾杜瓦的日记两方面的可靠的资料,柏纳也突然了解到他现在还是惟一了解两边情况的人。这是一个他不可能保持多久的便利之处,他必须又迅速又技巧的玩他的牌。他立刻下定决心。他读过的东西虽然没有忘记任何部分,但却把注意力固定在洛拉身上了。
“今天皁上我还不知道应该做什么,现在我再没有疑问了,”他对自己说,同时冲出房间。“这命令,就像他们说的,是无上的。我必须救洛拉。拿手提箱或许不是我的义务,但既然拿了,我倒确确实实在里面发现了我活生生的义务。重要的是在文杜瓦去找洛拉之前赶到那里,在我为她效力之前先介绍自己,让她不至于把我当骗子。其他的就此较容易。现在我口袋屯的钱足够让我像艾杜瓦本人一样慷慨义气慈悲的去救她。惟一伤脑筋的是怎样去做。w为洛拉是魏德尔家的人,虽然她就要生个不合法的孩子,她却必然是敏感的人。我猜她是个注重尊严的人,会把你给她的钱撕碎,连着轻视一起丢在你脸上——那个钱虽然是善意的,可是装钱的信封太不够厚重了。我怎么样让她接受这钱呢?我怎么样让她接受‘我’呢?这是伤脑筋的地方!人一离开合法的大道,常会发现纠缠在什么陷阱里啊!投身在这么僵的麻烦事里,我确实还太年轻了一点。可是,见它的鬼去吧,年轻正
是我的优点。让我们发明一个坦坦白白的说词吧——个又感人又有趣的故事。问题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