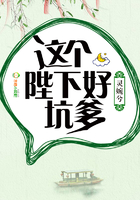“因为他的作品具有极大的容纳性和艺术性,他以追求真理的勇气和对心理的透视力,反映了人性的状况及相关的不同问题。”
颁奖辞
安德烈·纪德杰出的曰记保持了半个世纪之久,在第一页写道,当他20岁的时候,站在拉丁区一栋建筑物的六楼上,在秋天曰落的景象下,眺望塞纳河和圣母教堂一带,要为他们年轻的一群‘‘象征主义者”,找寻聚会的场所时,他感到像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主角拉斯提那(RasUgnac)—样,正准备征服在他脚下的城市:“而现在,我们有两个了!”不过,纪德的野心是要找寻长远而蜿蜒曲折的道路;他不肯满足于轻易的胜利。
今天这位获得诺贝尔奖荣誉的78岁作家一向就是受人争论的人物。从他写作生涯的开始,他就把自己置于传播精神焦虑的播种者的第一线,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今天几乎被全世界各地的人奉为法兰西第一等的文学家之而其影响力则无可置辩的影响到好几代。他最初的作品出现于1890年代;他最近的一本则出现于947年春天。在他的作品中,对欧洲精神史一段非常重要的时期有所勾勒,而这段时期也构成了他长久的一生戏剧性的基础。
或许我们会问:为什么这些作品的重要性到现在才被承认了其真正的价值?原因是,安德烈·纪德毫无疑问的是这样一个作家,其真正的价值需要放在长远的绝望中才可以评估,需要一段空间,才可以让辩证法的三个阶段有回旋的余地。纪德比他同辈中任何人都更有对比性,他是一个善变的普鲁杜斯,他的态度永远在变,不竭不休的从对立的一端来启手,以便激出火花。这乃是为什么他的作品看似不断的对话,而其中的信仰一直跟着怀疑奋斗,禁欲一直跟着对生命的爱奋斗,纪律也一直跟着对自由的渴望奋斗。即使他外在的生活也是动态而常变的:他著名的1927年的刚果之行和935年的苏联之行——我们只举这两者为例——就足以证明他不希望被列入安居乐业的文学阵营。
纪德出身于新教家庭,其社会地位允许他自由的追寻他的职志,大部分人都能将注意力集中于培养他的人格和发展他的内在。他的家庭环境在他著名的自传中有所描述,这自传的名称—Silegrainnemeurt(《如果麦子不死》,1924)引自圣约翰的话,就是:如果麦子不死,就不能结出新的果实。尽管他强烈地反对他所受到的请教教育,他却终生都在探讨道德与宗教的基本问题,而有时他用稀有的纯净来阐释基督教的爱,尤其是在他的短篇小说中,(《窄门》,1909)这本书可以与拉辛的悲剧著作相比。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纪德的著作中强烈的表现那著名的《道德主义》——这是他的敌人们常常误解的一个观念。事实上,它所指的是自由的行为,“无缘无故的”行为,是从良心的一切压抑之下的解放,是类似于美国的隐士梭罗曾经说过的:“最坏的是做自己灵魂的奴隶贩子。”我们必须常记心中,纪德并不认为缺乏一般公认的美德,这本身就是一种美德。LesNourrituresterrestres《地粮》,1897)是一部年轻时代的力作,在其中他热忱的歌颂南方美丽的果实,而这果实却不经久留;曰后,他自己从这番努力中转头他去。他向他的追随者与读者所做的劝告是:“而现在,丢开我的书,离开我!”但第一个遵从自己这种劝告的正是他自己,这在他后来的作品中甚为了然。
但不论在《地粮》或在其他作品中,他给我们留下最强烈印象的是分离与回返;这分离与回返含有浓烈的诗意,而他表达的方式则是如歌一般的散文。我们常常在他的作品中再度发现这种特质:譬如说,有一个五月的早晨,在布鲁萨一所清真寺的附近,他一篇简短的曰记中这样说:“啊!再度重新起步,感觉到细胞里那精细的温柔与欢喜像乳汁一样渗出来……花园中浓密的灌木,纯洁的玫瑰。在悬铃木的阴凉里懒散的玫瑰,你能够不知道我年轻的岁月吗?以前呢?我现在只是活在记忆里吗?我是真正坐在这清真寺小小的角落里吗——我这呼吸着并且爱你的人?或者我只是梦着在爱你?如果我是真真实实的存在,这些燕子怎么会这么向我贴近?”
不论在小说、散文,旅行曰记或对时事的分析中,纪德都不断提供给我们异乎寻常而不断变换的观点,但不管他的观点如何变化,我们始终都见到丰富的智慧,对人心普遍而深刻的了解,而其语言则达到古典绘画明晰程度,又具备丰沛的变化。著名的LesFauxMonnayeure(《伪币制造者》,1926)便是例子之这本书对一群法国年轻人做了毫不容情而透彻的分析。其新颖的写作技巧,已经在当代的故事写作艺术上造成了一个全新的趋势。另一个例子便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回忆录,在这本书中,作者意图忠实的记载他的往事,没有增加任何于他有利的话,也没有掩盖任何不愉快的事。卢梭也曾经做过同样的努力,但他有一点不同,就是在他展示自己的缺瑕之际,他相信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邪恶,没有一个人敢于论断他,或诅咒他。
而纪德却直截了当的拒绝同胞论断他的权利;他诉诸更高的法庭,要求从更广的角度来看他,在这样的法庭之下,他会把他自己铺陈在神的眼下。因此,他的回忆录的意义便可用圣经中那句神秘的话指示出来,而“麦子”则代表了人格:只要这人格是有情的、前思后虑的、自我中心的,他就只能孤独的存在,而没有创生的力量;只有以他的死和变形为代价,他才可以获得生命,并结出果实。“我并不认为,”纪德写道:“有任何看待道德与宗教问题的方式,或在这方面的行为方式是我所不知道的,或在我的生活中未曾实行过的。事实上,我希望把所有这些至今分歧的观点调和在一起,什么也不排除,准备将戴奥尼苏斯和阿波罗之间防争端交托给基督去解决。”
纪德心灵活动的多样性,可以在前面这段话中见其曙光,虽然他的多样性常常遭人误解与责备;但是他的多样性却从没有把人导入歧途。他的哲学有一种倾向:无论代价如何都必得要有新生,而且也一直在激起那神奇的凤凰,使它从火焰的巢中重新飞起。
今天,纪德作品中丰富的主题与动机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感谢与赞美,纪德本人虽然似乎喜欢引起别人对他的批评,我们却可以把这些批评放在一边。即使在已经成熟的年龄,纪德也从没有想要我们完全接受他的经验与结论。他最大的愿望是挑起问题,呈现问题。即使在未来,他的影响力也将落在对他作品热烈的争论上,而不是在全然的接受上,而他真正的伟大,正是以此为基础。
纪德的作品包含着一些段落,几乎带有忏悔录式的无所顾忌。他想跟法利赛人作战,但是,在这场战争中,要想不致摇撼某些纤细的人性模式是困难的。我们必须一直记得,纪德的这种态度是一种对真理的热爱,而这种态度,自从蒙田与卢梭以降,就已经是法兰西文学的一个公理了。纪德在他演变的各阶段中,都表现了对文学人格的真正捍卫,而这种捍卫乃是以作家人格的权利与义务,要把人格的一切问题毅然而诚实的表达出来。从这个观点来看,他在那么多方式中表现的、激起的文学活动,无疑代表了一种理想主义的价值。
安德烈·纪德先生不幸因为健康关系,不能前来亲自接受颁奖,但由于他表示以极大的感谢来接受这项荣誉,因此他的奖现在呈递给他法兰西大使阁下。
我被迫放弃这次预期中愉快而又有益的旅行,不能亲自来参加这次庄严的聚会,不能亲自用我的声音表达我的感谢,我的懊恼是无需说的。
如各位知道的,我一向拒绝荣誉——尤其是一些由法国所颁、而我凭着我是一个法国人这点即可当之无愧的荣誉。各位先生,我坦白承认,我是在一种头晕目眩的状态下突然接受了你们给予我的、一个作家所能期望的最高荣誉。许多年,我以为我是在荒野里呼喊,后来我只是对着一小群人说话,但今天你们向我证明,我信仰少数人的道德是对的,而这种道德迟早会获得胜利。
各位先生,在我觉得,你们的票与其说是投给我的作品,不如说是投给那种使它有了生命的独立精神,这种精神在我们这个时代从一切可能的方面遭受到攻击。你们从我身上看出了这精神,你们觉得有必要赞许它,支持它——这件事使我充满了信念和内心的满足。然而,我无法不想到,仅在不久前法兰西的另一位人士,他比我把这种精神表现得更好。我想到的是保罗·梵乐希;在我跟他半个世纪的友谊中,我对他的赞美与日俱增,而只因他的去世才阻止了各位把他选入我的位置。我常说,我总是用何等友善而又非示弱的虔敬向他的天才俯首;在这天才之前,我总是感到“人性,太人性了。”愿对他的回忆充满在这颁奖的会场,而此回忆,在黑暗越深沉之际,在我眼中越显得灿亮。你们渴求自由的精神,要它战胜一切,并透过这象征性的、不分国界的、不顾暂时派系纷争的奖励,你们给予了这个精神出乎意料的机会,使它发出特异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