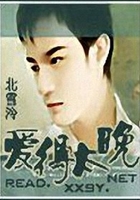法宝就是法宝,没有一次落空的,她见秦寮表情略为松动,心中窃喜不已。努力地眨眨眼睛,让眼眶发红蓄泪。
秦寮不语叹息。
“你不说话,我就当你答应了。”梅环儿眼泪一收,绽放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秦寮皱眉。
梅环儿怕他反悔,急忙又道:“反正你刚才已经答应了,就不能随便反悔。”说完扭身坐正。
竖起耳朵听动静,见秦寮没出声,才放下心里,可还是好像听见一声若有若无的叹息。
不过,只要没出言反对就行,梅环儿心情就大好起来。
“大哥,你虽然不说话,但我知道你一定是个好人。”梅环儿很狗腿地说道。
好人?如果她知道他这个好人曾想杀了她以图清静,不知道她还会这样认为吗?
不知道什么时候梅环儿又扭身过来,睁着亮晶晶的眼睛呆呆地望着他。
感受到她凝视的目光,秦寮不悦地皱了皱眉。
梅环儿回过神来讪笑道,“大哥,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长得很好看啊。”
秦寮皱紧眉头,十分不悦:“坐安生点,别动来动去的。”
梅环儿调皮地眨眨眼睛,端正身姿。
秦寮自惨遭家变后,性情大变,性格冰冷不说,更容不得常人接近半分。在东灵派十年,派中知道他存在的弟子并不多,除了掌门无规子的大弟子宁清与姬陕的大弟子致远外,再无其他人。
宁清与致远与他虽然自幼相识,但他拒人于千里的态度,俩人并不敢怎么亲近他,有时在后山小院相见时,也只是点点头,并无交谈。
而无规子与姬陕俩人则是尽心传授其毕生武艺,到秦寮青胜于蓝后,俩人便在旁指点。俩位长辈对他虽是关爱有佳,秦寮始终只保持师徒礼份,神情永远都是淡淡的。
至于无影门下众人对于他深不可测的武功与处事的斩伐决断更是把他当神一样敬仰,哪敢亲近半分,玩笑一句。
今日这般与人同坐一匹马,二人呼吸相闻,衣袂相贴,从未有过,很不习惯,所以身体一直僵着。
“早春清阳催人醒,
沐春风,
林涧花香沁入春,
山顶含翠,翠含羽。
江南特有的吴侬软音在竹林道上飘散开来。
这首小调,母亲石兰也曾唱过。
母亲的声音是温柔低醇的,常常伴他暖暖地进入梦乡。
梅环儿的声音却是清脆如林间翠竹,流觞如铃。
在吉县的客栈歇息了一晚,大夫替梅环儿包扎了伤口。
秦寮进入旁边的房间后再未出来。
第二天一大早,秦寮一打开门,梅环儿就在门口扬起一个大大的笑脸道:“大哥,早!”
秦寮冷冷地望着他。
梅环儿像被他看破了小秘密一样,低头呵呵一笑。
秦寮不再看她,径直走了出去。
梅环儿跺跺站得有些发麻的腿,跟了上去。
因梅环儿伤口未愈,不方便骑马,秦寮便找来一辆马车,将她扔进去,自己坐在前面驾车。
梅环儿挣扎一下,还未坐稳,秦寮便挥鞭驾马,一个颠簸,梅环儿便狠狠地撞向坐旮。
揉揉摔得发疼的额头,恶狠狠地瞪上秦寮,瞪了一会想到秦寮后脑勺没长眼睛,瞪再久他也不知道,想骂他两句,可又有些胆怯,只能手握成拳在秦寮的背后恶狠狠地比划了一阵,心里才舒服下来。
东看看,西摸摸,坐在马车里实在是太闷了。一把掀开帘子,梅环儿猫着身子钻了出来,坐在秦寮旁边,冲他嘻嘻一笑。
视野开阔了,呼吸也畅顺多了,心情也好了起来。
“大哥,你是不是去过很多地方?”
“你知道哪儿最好玩吗?”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哦,以前就在扬州转转,有时候出去没转一个时辰,娘就会派家丁把我寻了回去,真是无趣得很。不过,我也有一次跟宝姐姐溜去苏州玩了两天,还在寒山寺留宿了呢,寒山寺里的明空长老留着长长的白胡子,他闭着眼睛念经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去扯他的胡子。”
梅环儿一说就没法停住,说完了苏州的寒山寺明空长老,开始说府里丫鬟下人的各种趣事,说到高兴的时候,一个人乐得哈哈大笑,声音像银玲洒在慈州的路上。
秦寮神情依旧冷冷清清,像在听,又像没听,只是手中挥鞭的频率越来越高,马车越跑越快。
“大哥,你心情不好吗?”梅环儿撇了一眼秦寮,“我说了那么多话,你一句也不回。”梅环儿嘟嘴表示不满。
秦寮面色有些难看起来,好看的眉毛又皱到一起。
“要不,我给大哥唱个小曲吧。”梅环儿见状立即乖巧道。
未等秦寮回应,当然也没指望他能回应,便细细地唱了起来:
拂柳岸,泪染伊人妆,
绣桥轻叹这时光。
风动钱塘,波光微漾,
雨碎胭脂香,美其芳晨丽景
人醉也还香。
声音越唱越低,头越垂越垂低,渐渐地倒靠在秦寮肩头睡了去。
秦寮侧目看时,只有匀匀的呼吸声洒在他冰冷的衣领上。
自卯时便开始在客房门前候着,生怕他甩下她走掉。
本来还以为她精神力多好呢,想不到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就要补眠了。
一呼一息,密密落在颈处,秦寮不自在地皱皱眉头,缓缓地勒住马车,将梅环儿抱进车内靠在软垫上,复又坐到车前,继续驾马,只是落鞭的频率缓了下来。
行至半路时,看到一家茶水店,想到水囊中水剩不多,秦寮便勒马停车,走进茶水店,顺便买些干粮,免得等下她醒来饿了,嘴巴又会不消停地聒噪。
茶水店的人并不到,只有三五个去往慈做生意与送信件之人在此歇息。
人群中还有一个全身衣衫褛烂的老叫花,他正悠闲地拿着一个青花海碗喝着茶,不经意地看了一眼马车。
背对着马车买好东西,秦寮心中一动,转身疾步走到马车前,一把掀开车帘,里面空空而已。
秦寮神情微震,居然有人在他身后将人劫走,他竟然未察觉!可见此人的内息与轻功在自己之上,只是他要劫走梅环儿做什么,难道这个臭丫头又惹了什么厉害的仇家。
不管她惹了什么仇家,被劫了也好,世界终于清静了。
“表少爷,我们能找到小姐吗。”吉县人来客栈里,小娟忧心忡忡地问纪存之道。
“一定能找到,有人传出在太白楼内有一个少年与清河帮弟的人曾交过手,据他们描述那个少年的长相,就是环儿。”纪存之回答。
“那小姐有没有受伤?”小娟闻言担心地问道。
“应该不会,据说少年毫发无伤地跟着一个蓝衣青年走出太白楼。据我推算,定是那名青年男子救了她,要不然凭她的武功怎么可能在清河帮手中讨得便宜。”
“我猜这次肯定又是小姐又管了别人的闲事。”听闻梅环儿无恙,放心下来,很了解地进行分析。
纪存之则长叹了一口气。
“又是你这个老叫花!哼,上次抢了我的糕点,这次抢了我来做什么?”梅环儿睡醒过来,发现自己居然在一个小破庙里,而上次抢了她糕点的老丐正斜躺在一堆草垛里笑眯眯地望着他。
“小丫头,脾气很大啊。”老丐拿起酒壶喝了一大口,擦擦嘴边的酒渍,很享受地躺在草垛里,望着斑驳的庙梁脊。
“你说谁是小丫头呢。”梅环儿加粗嗓门地吼道。
老丐嘿嘿一笑道:“既然不是小丫头,就不要心虚地红脸嘛。”
“我这叫气色好。”
“小丫头,下次扮男子记得还要带个假喉结。”老丐好心提醒。
梅环儿摸了摸自己的喉咙,闷哼了一起,算是默认了。
“那你捉我来做什么?我跟你无怨无仇,又无任可瓜葛的。”
“的确没有无怨无仇,但瓜葛还是有的。”
“我跟你还有瓜葛?”梅环儿手指按着自己的鼻尖显得很惊讶。
“你一年前是不是救过一个胸口中箭的中年男子。”老丐慢悠悠地说道。
胸口中箭的男子?
好像是有这么回事。
那天,自己在家中无聊透顶了,躲过小娟和众家丁的监视,偷牵了一匹马去五灵坡。五灵坡有一个前朝留下的石头阵,至今无人能破,梅环儿便立志要做破阵第一人。
当时还未到五灵坡,就听到路边的草堆里传来呻吟声,下马看时,发现一个胸口中箭,奄奄一息的中年男子。她连忙将男子拖扶到马上,送到了扬州城内的仁济堂医治。在大夫施针吊药确定男子性命无碍后,留下身上的银子托仁济堂的人照顾那名男子,自己又偷偷地溜回到府中。
第二天一大早她再去仁济堂时,仁济堂老板告诉他,那名男子半夜清醒过来后就离开了,至于去了哪里就不知道了。
这名男子到底是谁?重伤未愈就要急着离开,应该有什么重要的急事吧。
事后,梅环儿便将这事淡忘了,甚至连那个人长什么模样也想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