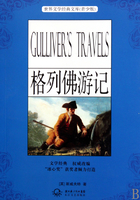本·格恩的小船足够能撑起我的体重袁很安全袁不会沉船。我划着小船,它的优点我深有体会袁轻快而灵活,但划起来又很别扭,老往一边偏,但这还不是最要命的袁最要命的是它在那不住地打转儿。
本·格恩说过,这小船“很不好对付袁除非你摸透了它的脾气”,我自然还没达到那个水平,它每个方向都肯去,但就是不肯去我要去的方向。
但我总算交上了好运,不管我怎么划,或者说不管我划不划,潮水一个劲把我往下冲,“伊斯班约拉号”就在我的航道上,想不靠上去都不可能了。
大船最初黑糊糊的一团出现在我面前,渐渐地显现出桅杆、帆桁和船体。紧接着由于我愈往前,退潮愈急,小船已接近锚索了,我就立刻把它抓在手里。
锚索绷得像弓弦一样紧,可见用多大的力量才把船拴住。夜色中泛着细浪的潮水在船身周围哗哗作响,犹如山间流淌的泉水。只要我用刀把锚索砍断,船就会被潮水冲走。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很顺利,但我忽然意识到,绷紧的绳索一经砍断,我的小船就会像被马蹄踢了一样翻进水里葬身海底。小船与大船的比例相差太悬殊了。
这下,我有点无可适从了,要不是命运之神再次眷顾,我可能要无功而返了。
恰恰这时,风向变了,变成了西南风,一阵风吹来,“伊斯班约拉号”逆流而起,锚索突然松了下来,我抓锚索的那只手一下子浸到了水里。
机会来了,我迅速掏出折刀,用牙把刀拉出来,一点点地割绳索,只是在剩下两股细绳时,又绷紧了,我停了下来,等待着锚索再次松弛,以便再次下手。
船上一直有人在高声谈话,我因为注意力都在锚索上,所以没有注意,现在有空了,就听起来。
说话的一个是伊斯莱尔·汉兹,当年弗林德手下的炮手,现在的副水手长,另一个是那个戴红帽的家伙,两个人都喝醉了,但还在喝,其中一个推开窗户扔出一个空酒瓶来,“扑通”一声掉进水中。
他们相互咒骂着,脏话连篇,随时都可能打起来的样子,可是却没有打起来,每次骂到最激烈的时候,声音就小了下去,过一会再激烈起来。
在岸上,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映得天都红了,有人在唱一支老掉牙的水手歌谣,每一句的末尾都降调、颤抖,没完没了。
在航行中我听他们唱过几次,其中有一句是院七十五个汉子出海去啊,只剩下一个活着回来。
没错,今天上午遭到重创的这帮家伙唱这首歌正合适。
不过,可以看出,他们并无忧伤,也无快乐,只是麻木的吼叫。
又来了一阵风,大船侧着身子凑近了我,锚索又一次松了下来,我趁机把它彻底割断了。
一股风吹来,小船载着我直向大船的船头冲去,就在这时,大船转了船身,首尾对调了。
我挤出吃奶的劲划着桨,怕被大船带翻。可无论我怎么划,小船就是不离开大船,干脆,我向大船的船尾划过去,可这样反而摆脱了它,我一用力,小船向后撤了。就在我撑罢最后一桨时,我的手突然碰到了从后舷垂下来的一根绳子,我一把抓住了它,只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伸手就抓住了,既然抓住了,另一头还很结实,我有了好奇心。
顺着绳子,从窗户看一下舱里的情况。
我双手交替地抓着绳子往大船上靠,冒着极大的危险我直起了腰,我看见了舱里顶板和舱内的一个角落。
大船和小船一起顺流直下,我们的位置已与岸上的篝火相齐了,涛声震耳,船如离弦之箭。
我的眼睛高过窗棂,当然时间不能太长,我只看了一眼:
汉兹正与他的同伙互相掐住脖子扭成一团。
我又及时跳回到座板上,差一点儿就掉进水里。霎时间我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两张凶神恶煞似的脸在熏黑了的灯下晃荡着,显得通红。我闭上眼睛,让它们重新适应黑暗。
没完没了的歌谣终于停了下来,篝火旁所剩无几的海盗又唱起我听腻了的那个调子:
十五个汉子扒上了死人胸,哟——嗬——嗬,再来朗姆酒一大瓶!
酗酒和魔鬼使其余的人都丧了命,哟——嗬——嗬,再来朗姆酒一大瓶!
突然,小船歪了一下,转了一个圈,潮水的速度更快了,我马上睁开眼睛,波光水影,细浪涛涌,我还在大船周围的漩涡中,而此刻,大船又改变方向了。
我回头一望,心吓得差点蹦出来,我背后就是红红的篝火。潮水带着大船小船一起向右转了个弯,水流急了,浪花高了,声音大了,我们一起奔向宽阔无垠的大海。
突然,大船船身一震,猛地转了二十度的弯子,船上传来两声叫喊,紧接着就响起了匆忙杂乱的脚步声。
我趴在可怜的小船底部,把我的灵魂虔诚地交给造物主安排。
只能听天由命了。
当时我绝望地想,不久我就会被浪涛所吞没,一了百了,也没这么多烦恼与担忧了。
其实死亡并不可怕,但等死却很难受。
就这样我趴了好几个小时,随着浪头一起一伏,一上一下,海浪打湿了我的衣服,每一次起伏我都在想,完了,可总也没完,渐渐地我对危险都觉着乏味了,竟然打起盹来,后来竟睡着了。真有些讽剌的味道。
在大海的波涛间,我梦见了我的家乡,梦见了那个熟悉的旅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