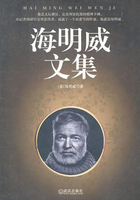在中欧和东欧,“诗人”一词的意义与西方略有出入,在那里,诗人不单单是美妙词句的创造者。传统要求诗人不仅要成为民族的“行吟诗人”,同时也应是民族的歌唱家,而其歌曲能够被大众咏唱,其诗歌能包含一切大众感兴趣的东西。当然,在历史的各个时期,诗人所承担的责任也不尽相同。如果戴尔塔生活在古代,也许他会感到如鱼得水,因为在那个时代,国王和王公贵族常常邀请诗人与他们同桌用餐,而诗人为了让国王和王公贵族开心,会在用餐时吟唱歌曲、说笑话。甚至那个时代的服饰,也比今天的西服更符合诗人的身份,弹诗琴和蓄长发也更符合诗人的性格。
戴尔塔的肤色像吉卜赛人那样黝黑,满脸雀斑。他个子不高,大笑的时候嘴唇歪扭,脸上露出痉挛狞笑的怪相。他前额突出,头发向后梳着。脑袋大得与他矮小的身材极不相称,就像过去画家绘制的王公贵族宴会上的侏儒和小丑。他穿戴也很奇怪,喜欢把领带打得很松,领结绑得很大。那些想以外在特征强调自己属于艺术圈子的人,其实只不过是二流艺术家。但在戴尔塔身上显示出的那种艺术的放肆,只是其全部表演的一部分。他做出的每个手势,运用的每个腔调,都是在与世界游戏(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他特别想强调自己与众不同。在坐满听众的大厅里,戴尔塔能非常出色地朗诵自己的诗。他是一个好演员,能掌控气氛,也就是说,他有足够的技巧掌控听众的情绪,知道如何将听众带入高潮,并用适当的语言和声调让他们一直维持在高潮中。他朗诵时速度很慢,在词与词之间非常注意停顿,尽管是在朗诵,实际上却像在吟唱。他用魔咒般的语言迷惑听众,使自己仿佛变得很高大,就像换了个人一样。
没有人知道戴尔塔的身世,需要时,他会为自己编造出适当的简历。他的父亲一会儿是教会职员,一会儿又成了餐厅老板;他的家庭有时来自捷克,有时又与莫斯科有什么关联。在戴尔塔身上,找不到幻想与真实之间的分界线。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学习不同语言的。很难想象他如何坐在桌旁从词典和语法书中查到词汇,因为他时常引用拉丁语、英语、法语、德语的诗句。他曾在大学待过很短的时间,并曾因撰写过一篇论文而出名,这篇论文叙述一位虚构的17世纪英国诗人。戴尔塔在这篇论文中详尽地介绍了诗人的生平,并分析了诗作的创作背景,及诗人素来想做一个招摇撞骗者和故弄玄虚的人的愿望。当那位治学严谨的教授因为戴尔塔的博学多闻而显得左支右绌时,戴尔塔却玩得十分开心。
戴尔塔是个积习已久的老酒鬼。酗酒把戴尔塔带入了一种幻觉(通常他一醉就好几天),且表现为行动,这种状态在别的酒鬼身上很罕见。每次,当他一迈进旅行社的办公室,他总是吆喝着:“先来杯啤酒!”他乘坐马车时(在“二战”前,马车在华沙一直是一种普通的交通工具),经常突然喝令马车停下,然后脱去外套并顺手扔到马路上,接着就旁若无人地在外套上撒尿,弄得众人瞠目结舌。这种行为极不合逻辑,只能说他有裸露癖,此外很难解释他为何要这样做。他常去熟人那里,但老是抱怨很难找到他们的门牌号码。于是,他就叫安置在一些街道上的“自己人”给他指路,可他又说,这些人往往打扮得他认不出来。戴尔塔这些近乎胡闹的言行证明,因为酗酒,他已经进入了霍夫曼斯塔尔雨果·冯·霍夫曼斯塔尔(HugovonHofmannsthal,1874-1929),奥地利作家,生于维也纳,在16岁时就因以Loris为笔名出版的无懈可击的诗集而享誉维也纳。与爱伦·坡埃德加·爱伦·坡(EdgarAllanPoe,1809-1849),美国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被尊崇为美国浪漫主义运动要角之一,以悬疑、惊悚小说最负盛名。爱伦·坡是美国的短篇小说家先锋之一,并被公认是推理小说的创造者,甚至被视为科幻小说的共同催生者之一。故事中的世界,他也因此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在文人聚集的咖啡厅里,议论戴尔塔最新的怪异行为,成了人们最热中的话题。
戴尔塔成为传奇式人物的第二个原因是他的诗歌。他的诗歌与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诗歌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戴尔塔不受任何文学流派的影响,他对于古老的拉丁-意大利诗歌文明心驰神往,这种文明在波兰留有很深的印记。他从那些古诗中引经据典,醉言呓语地堆砌辞藻。他的诗中时常出现古老的神秘,诸如:圆圆胖胖的巴洛克风格的天使;从窗户飞出去后被神秘力量抓住(在最后一瞬间被妻子咬住耳朵获救)的巫师;预言世界末日的占星家;携猎鹰狩猎等。与其交织在一起的还有:轮流播放着莫扎特和巴赫音乐唱片的留声机;卖蝴蝶的失业工人(他们最后为什么不能出售蝴蝶?);仿佛穿着蓝裤衩的姑娘般的行星;乡下人喜爱的民间舞蹈。他的诗歌既是悲剧风格的,也是滑稽的;虽看似无聊空洞,却又颇有意思。他的诗歌是他自己特有的荒诞和许多不同元素所构成的大杂烩,令人联想到处于低迷时期的现代诗歌;但另一方面,他的诗歌与现代诗歌又有所不同:尽管稀奇古怪地混杂了很多场景,但也并非不能理解。读者为他诗歌中的音乐魔力所震慑,接受了其中的抽象内容。而这种抽象内容如果发生在其他诗人的作品中,就只会引起读者的不快。他的诗中出人意料的急转弯会引得读者发笑。总而言之,读他的诗会使人在不知不觉之间陷入一个非日常生活法则所能控制的领域。
戴尔塔用了各种不同的笔名写了很多幽默诗,他所虚构的故事主题无穷无尽。例如,他曾写过系列题为“陵墓部主任之歌”的诗。他常列出一份虚构的诗集作品清单,我还记得有这样一个题目:“人吃人序——讲课手稿,销售一空”。因为他的诗颇受读者欢迎,不但出版社出版他的诗集,广播也时常播放他的诗选。写诗成了他唯一的收入来源。因为手头不时拮据,他对钱也就斤斤计较,可是他一拿到稿酬,扭头又会把它全都花在酒上面。
戴尔塔清醒时,见到他的人,谁也不会想到他就是那位大受欢迎的诗人。他生性沉默寡言,阴郁悲观,皱着眉头看人。只是一见钱才显得很激动。与出版社讨价还价时他铁石心肠。他只叫一口价,没有人能说服他让步。此外,他往往还没交稿就要求出版社预付稿酬,这时常导致编辑之间的内部争斗。当然,那是因为大家都想抢先出版戴尔塔的诗。但编辑们都知道,如果先给钱将会冒很大的风险;因为戴尔塔一旦拿到稿酬,马上就会去买酒喝而忘了自己的责任。有一些编辑的做法很极端:他们虽预支稿酬给戴尔塔,但在他交付手稿之前,会整天形影不离地粘着他。这种交易时常在咖啡馆里进行:编辑把钱摆在戴尔塔面前,每当戴尔塔觉得对方死也不会放过他时,他就会掏出笔来当场即兴赋诗(至于诗写得好或是很一般,端看他当下的情绪如何),完了之后,他就立即去买酒喝了。
戴尔塔曾被强制送到戒酒中心接受治疗,但总不见疗效。有人跟我讲了一个戴尔塔在戒酒中心与医生斗争且大获全胜的故事:在某个戒酒中心,戴尔塔与医生打赌,结果所有的医生和患者,包括酗酒者,全都酩酊大醉,双方在戒酒中心走廊上举行了一场自行车比赛。
戴尔塔是江湖骗子、酒鬼,但是,与他的外表相反,他曾是一位杰出的悲剧诗人。他在经济大萧条的年代开始自己的文学活动。那时工人失业,人们普遍对前途失去信心,**主义开始在相邻的德国盛行起来,这一切都对戴尔塔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他可以当之无愧地被冠以“荒唐之王”的头衔,然而,从他的诗中,却可以看到一种危险的预言——看出这一倾向的人并没有被他表面上的插科打诨所迷惑,他们看到了文明的终结、“铁器时代”的来临和大灾难爆发的征兆。在欧洲陷入黑暗与暴力之前很多年,根本没有任何征兆表明,当时现实中所有的一切都将崩溃。戴尔塔在诗作中所使用的概念和描绘的画面都像梦一样,旧日的各种意象——恐怖的和美丽的,再次回到他的诗中,就像平行飞驰的两列火车,互相追逐,没有交集。在戴尔塔的诗中时常会出现圣母马利亚,但她不是那位虔信者眼中的圣母马利亚,而仅仅是他文本中风格的装饰罢了。当***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戴尔塔的诗中,像木偶戏中的木偶那样,彼此厮杀时,戴尔塔就会嘲弄地大叫:“现实啊!神圣的母亲!对你来说就像打死蜘蛛一样!”他说得有道理:“靠着我的船夫,我前往永恒怀疑的深渊。”
世界末日(Koniecs'wiata)——这是他的一首长诗的题目。在诗中,学者与政客,革命党人,情人与酒鬼,金丝雀与猫,全都由于一场宇宙性的灾难而惨遭灭顶之灾——这结局让诗人满意,同时也实现了《圣经·传道书》的主题:“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旧约·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这一切都是由一支戏谑取乐的笔写出来的。他在另一首长诗《民间游戏》(Zabawaludowa)中描写的那些场景——旋转木马、草地上的情侣、随意弃掷空瓶的草地、秋千游戏场……天空顿时乌云密布,骤雨倾盆,天地间一片黑暗——令人想起罗马诗人维吉尔维吉尔(Vergilius,公元前70-前19),罗马帝国时代最伟大的诗人。着有《牧歌集》、《农事诗》、《埃涅阿斯纪》等。来。这就是戴尔塔所使用技巧的秘密:悲哀的牧歌和机关枪的“哒哒”声交响着。
戴尔塔所写的最不寻常的长诗是《在所罗门那儿的舞会》(BaluSalomona)。所罗门国王为何要举办舞会?所罗门国王为何会生活在20世纪?也许这不是所罗门国王,而只不过是个叫作所罗门的人?为什么卖蝴蝶失业者会闯到舞厅来?是谁在唱关于玫瑰园古丽斯坦的波斯歌曲?为什么突然有大批警察闯入,并开始跳着奇奇怪怪的舞蹈?其实,不值得为诸如此类的问题去伤脑筋。因为梦境总是存在着一定的特殊逻辑,只有戴尔塔这样的诗人才会灵活地加以运用。“有个女人絮絮叨叨地谈论米开朗琪罗”——艾略特这样写,是想表示这类舞会上对话的无聊和荒谬,戴尔塔却将在所罗门舞会上进行的对话提到了更高的境界——谵妄与“永恒怀疑”的范畴。
戴尔塔诗歌的主题令人感到压抑。但与此同时,他的诗歌——这种奇特现象在这里还有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它摆脱了悲观和失望。他的诗中充满了对生活的赞许。戴尔塔用自己掌握的每个词语来赞美他眼前的这个世界:荒诞游戏、愿望、语言和混成一团的争斗。他热爱自己的幻觉世界。他热爱旋转木马、跳舞的吉卜赛女人、星期天清晨维斯瓦河上挤满了人的游船、他为之写颂诗的妻子、睡在窗台上的猫、开满鲜花的苹果树。他天生喜爱热忱和快乐,不管遇到什么事,他都能让这些事变成充满动作、色彩和音乐的场景,生机勃勃、有声有色。也可以这么说,对戴尔塔而言,诗的主题只是一种借口,就像桑蚕吐丝那样,无论在路上遇到什么题材,戴尔塔都能用自己所吐出的丝缠绕住它们,创作出歌曲和赞美诗。
戴尔塔对政治从未表现出任何兴趣,他讽刺所有争权夺利的党派集团。因此,当他在1937年投身极右派民族主义旗下时,所有人都为之一惊。一位来自重要右派周刊的编辑一直希望能够与戴尔塔合作,最后终于成功了,戴尔塔的诗歌开始刊登在该周刊上,该周刊成为刊载戴尔塔诗歌的独家杂志。周刊内容具有强烈的排犹倾向。戴尔塔的诗销量很大,是由于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特别是在年轻人中形成了一种民族主义“运动”。与此同时,所有欧洲国家都展开了这一“运动”,尤其是意大利与德国。广大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读者对戴尔塔这次新的恶作剧简直不敢信以为真。戴尔塔讴歌行进队伍的“民族主义方阵”,在自己的诗歌和文章中预言“长刀之夜”——对犹太人、自由主义者和左派来说,这就是新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圣巴托罗缪之夜(St.BartholomewsDay),发生在1572年8月24日的浩劫。当时的法国国王查理九世表面上支持、笼络新教的领导人,暗中却怂恿旧教策划阴谋,利用圣巴托罗缪节当天基督教新教徒在巴黎集中的机会,发动了一场对新教徒的屠杀,当晚至少有两千人被屠戮。即将到来。但事实很明显——这类作品的确刊登了出来,署的是戴尔塔的姓名,而且带有他的才华的一切特征。
戴尔塔为何这样写?其实戴尔塔根本不关心种族主义问题。他有很多犹太朋友,在他发表种族主义声明的当天,他去找这些犹太朋友(当然,他那时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并跪倒在他们面前,对他们说,他爱他们,恳请他们原谅。戴尔塔与右派联合并非出于政治倾向。戴尔塔作为滑稽演员和行吟诗人,他有自己的职业原则。他尊重自己诗人的职业,但他自己写了什么或发表了什么,对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怎样写、为谁写。戴尔塔鄙视那些只知道迎合少数行家的神秘文学流派,他嘲笑那些诗人,因为他们的诗仅为少数知识分子所理解,他不喜欢那些不受读者欢迎、面对四壁孤独冥想的作家。戴尔塔希望自己可以像旧日的歌唱家和行吟诗人那样,手拿诗琴,身边围着一群崇拜者。在反对知识分子脱离社会这一点上,在20世纪,很难找到一个比戴尔塔更为典型的作家例子。假如戴尔塔不得不在只给少数假内行阅读的不知名杂志上发表作品,他就会像一个男高音歌手到了荒无人烟的小岛上那样孤独和痛苦。他对犹太人的敌视(他不是没有这种倾向)并不带任何种族主义色彩,只限于对犹太作家的敌视,因为这些犹太作家一本正经地强调所谓文学的“价值”和“品位”。正因为如此,戴尔塔与文学咖啡馆之间产生了矛盾,他想从这种文学咖啡馆中摆脱出来。此外,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戴尔塔是个有激情的人,喜欢热闹的场面,喜欢看到群众游行、群众群情激昂挥舞着手杖的样子。他认为,这才是健康,力量,原始状态,伟大的民间娱乐。“我的读者走到哪里,我就跟他们到哪里;我的读者喜欢什么,我就给他们什么。”——戴尔塔自己的每一首诗都表明了这一点。因为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戴尔塔也就加入了这个运动,他希望能与大众站在一起。他非常骄傲地说,有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能背诵他的诗歌。他这种骄傲不是空穴来风,因为只有少数人对“先锋派”感兴趣,“先锋派”从来没有像戴尔塔这样掌握如此宽泛的艺术手段。最后我们必须考虑到,为了生存,戴尔塔需要庇护者——而庇护者必须强迫他写作,强迫他克服酗酒。简言之——庇护者必须控制他,同时也要关心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