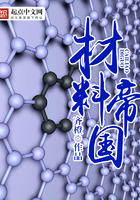既然季巧巧想玩儿大的,那她奉陪到底。
“小姐,”若薇眼角氤氲出水光。
“无妨的,”江兮浅抿唇,比起玉香天青丸,玉香蛇那点儿毒性说是微末也不为过,她倒要看看这次季巧巧拿什么来掩住凤都千万百姓的悠悠之口。
江兮浅让若芸取来笔墨,寥寥数语落在宣纸之上,“水阳,亲自交给银面。”
“是,”水阳抬头,深深地凝望江兮浅一眼,然后蓦然离开。
刚才的事情,她和水冰都一清二楚,只是小姐何其无辜……
“我没事的,”江兮浅抬起头,对着空气,“记住,不管如何,护住若薇和若芸。”
“水冰知道,”声音处,却无人知晓她的方位。对这一点,江兮浅非常满意,当真不愧是银面亲自调教出来的暗卫。
江兮浅抿唇,神色淡然半倚在软榻上,抬头向外张望。
“大小姐,相爷带了好多家丁侍卫朝这边来了,”一个小丫头战战兢兢。
“嗯,下去吧,”江兮浅摆手示意,果然不出她所料。
当年她身落荷花池时,他说了什么来着?
不过风寒,区区小事,找他做什么?
可如今呢,那季巧巧不过中毒而已,虽有妨害却并不致命,只是痛苦些许,他就这般急不可耐的带人冲过来了,啧啧,当真是“父女”情深呐。
“小姐,你要不要避一避?”若芸抿唇。
“那岂不是做贼心虚了,”江兮浅唇角微扬,看着江嘉鼎怒不可遏的带着大批人马,浩浩荡荡地仍开守门的婆子,冲进汐院的时候,她突然忍不住大笑起来。
那笑声冲破屋墙,仿若直达天地般。
声声回音,悲悲戚戚,天地时光,仿若静止。
所有听到的人都心底一滞,好似细针扎入胸口处,丝丝疼痛蔓延开来。
“小姐,你别这样,”若薇张了张口,却再也说不下去。
江嘉鼎已经冲了进来,“你这个逆女,居然还笑得出来。”
“我为何笑不出来?”巴掌大的小脸上尽是轻蔑和鄙夷,“能除了眼中钉、肉中刺,我开心得不得了,自然要笑。”
“你,”江嘉鼎气得胸口一起一伏,“既然你已经承认了,那就别怪为父心狠了,来人呐,把人绑起来拉到祠堂去。”
看着走上前的两名侍卫,若薇若芸一左一右紧紧护住江兮浅;两名侍卫还未用力就被两人掀翻扔出了大门。
江嘉鼎眸色一沉,没想到这女儿身边的小丫头居然也有这等武力,“你这是想造反不成?”
“退下吧,”江兮浅抬了抬眼皮,最后抿了一口茶道,“银针过季而衰,陈茶难昧,新茶将出,若芸,不可偷懒了去,丞相大人也不必动怒,小女子跟你走一趟便是了。”
都是死过一回的人了,皮肉之苦又算得了什么。
“哼,”江嘉鼎沉声冷哼,到底有些下不来台。
“小姐,”若薇一反常态,紧紧抓着江兮浅的手。
“放心,”江兮浅拍了拍若薇的手背,她比谁都想要活着,季巧巧没死,齐浩远没死,她又怎么舍得死。
相府祠堂。
江兮浅上下打量,阔别三年,景物依旧,人依旧,甚至连场景都与当年何其相似。
“逆女还不跪下!”江嘉鼎坐在主位上,手狠狠地拍在桌上发出啪的一声闷响。
江兮浅抬头,看着那密密麻麻的牌位,嘴角微勾,心中的嘲讽达到了最大,不声不响亦不跪。若真的祖先有灵,她前世为何过得那般苦楚颠沛流离;若真的先辈有灵,又如何会让一个外姓女子霸占属于她的一切;若真的地下有知,又怎会任由那数典忘宗之人高坐明堂?
江嘉鼎面色难看,这个女儿她越发的看不透了,“来人呐,给我摁下去!”
屋外侍卫虽有些不忍,犹疑了一下,还是左右摁住江兮浅,只是那微薄力道还不足以撼动江兮浅,江嘉鼎却兀自起身在江兮浅腿弯处狠踢一脚,“让你给我跪下!”
“砰——”
“噗——”
江兮浅双膝及地同时喷出一口鲜血,她起先将玉香天青丸的毒性逼到腿处,江嘉鼎那一脚却将少量毒性踢散,内力冲击致使心脉受损,当真是计划不如变化,她嘴角冷笑,重新将毒性逼回一处。
只是却无人注意到那鲜血中亦带着丝丝黑线。
“江兮浅我问你,你为何要对巧巧下毒?”江嘉鼎沉声。
“为何?我也想知道为何,”江兮浅轻蔑一笑。
“你,”江嘉鼎抿唇,“既然你对下毒之事供认不讳,那……”
不等他说完,江兮浅轻蔑一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何况我何时承认过?”
“我亲眼所见,你也要狡辩么?”大抵是安置好了季巧巧,江文武匆匆赶来,刚好看到这一幕,与他同来的,还有接到消息匆匆赶来的季巧萱。
江兮浅冷笑,“你亲眼所见?你当真亲眼所见了么?”
江文武愣住,可只要一想到大夫说的话,他就忍不住,垂在身侧的双手紧握成拳,“巧巧生性善良,对你亦是一再忍让,甚至带了她生母留下唯一的一套头面去给你赔罪,你怎么忍心这样对她?”
“我怎么对她了?”不同于江文武的气急败坏,江兮浅却是云淡风轻,好似所有的事情都与她无关一般,纵使身形狼狈,可那股淡然的气质却怎么都让人忽视不了。
“你,”江文武扬手。
江兮浅仰起脸,“怎么想打我?”
“你,”眼见江文武的手就要落下,季巧萱厉喝一声,“住手文武!”
“娘!”江文武皱着眉,声音拉长,语气不满。
“不管她做了什么,都是你唯一的妹妹,”季巧萱面色难看。
江文武撇过脸,“我没有这样心狠手辣的妹妹。”
“刚巧,我也不想要这般脑残的哥哥,”江兮浅呛声。
“你说谁脑残?”江文武黑脸。
“谁应说谁,”江兮浅亦抢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