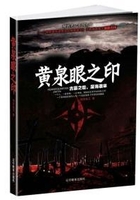“革命小将们,行动起来!炮打上海市委!揪出陈丕显!砸烂他的狗头!将他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这是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解放日报》上的一篇新闻稿。
陈丕显曾任上海市委书记,文革期间他和很多老干部一起被打成“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游街示众,万人批斗,在监狱里关了八年,罪名是“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
由于是新式社区,黄浦新苑有完整的电视监控系统,小区的道路和电梯里都安装了摄像头,记录了以下画面:
四月十九日晚十二点三十分左右,一个穿黄雨衣的人从六号楼十八层进入一部电梯。由于摄像头的位置居高临下,而且这个人戴着宽檐的雨帽,拍不到他的脸,也就无从辨别他是男还是女。
这个人离开大楼,走到道路上,进入一个摄像头难以拍摄的死角,就这么消失了。
河滨大楼的电梯管理员徐阿姨被请到刑侦队,观看这段录像。“很象呢,”徐阿姨连声说,“应该就是她吧!”
与河滨大楼一样,这个女孩“来路不明”,她既不是楼里的住户,也没有进入过大楼,却莫名其妙地从案发现场走了出来,消失了。
十九号晚上的天气很阴霾,没有下雨,没有月亮。这个穿雨衣的女孩,就象雨衣里滴下来的水珠,冷飕飕,阴森森。
另外,齐卫东的手机里也有那几条短信,内容完全相同。
彭七月拿出自己的手机,他用的是诺基亚6600,六万五千色分辨率的屏幕和三十万像素的摄像头显然已经落伍,但喜欢它矮矮胖胖的造型。
彭七月决定给这个号码发去一条短信:
“我叫彭七月,是警察。聊聊好吗?”
对方没有回答,似乎不屑一顾。
彭七月不甘心,又发去一条,“你也做了亏心事。第5:杀戮。”
仍然没有回答。
彭七月有点气急败坏,发去第三条短信,“我操你十八代祖宗!”
这是他第一次在短信里骂脏话。
还是没有回答。
彭七月泄气了,把手机一扔,正打算找点东西吃,没想到躺在沙发上的手机滴滴滴叫了起来,真的有回复!
对方发来一张图片,黑白的,上面有一块四四方方的东西,冒着气体,下面配有简短的文字:
“我很硬的,你操得动吗?”
“中国移动”其实是一家电信运营商的名称,但在彭七月听来,似乎有一种“中国在移动”的感觉,因为从地质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块大陆都不是静止的,只是这种移动非常缓慢,每年不过几毫米。
通过中国移动下属的上海移动(中国都在移动,上海怎么能不移动?),彭七月查到了这个号码的用户,他叫洪本涛,住在浦东德州新村。
在一排排兵营一样的房子里,彭七月敲响了其中一扇防盗门,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给他开了门。黑苍苍的方脸盘,嵌着一双精明的小眼睛。
“我不是洪本涛,那是我哥。2003年他出了车祸,在第二医科大学门口被隧道八线撞死了。”
“我叫洪本波,”没等彭七月开口,这个人就先问开了,“你是看了那本小说来的吧?”
“小说?”
“是啊,我家的地址,包括这个号码都被写进小说里了。来访的人很多,不过你是警察,这倒是有点新鲜。”
“是什么小说?”彭七月问他。
“一本恐怖小说,叫《第51幅油画》。”
彭七月头一回听说这本书。平时工作忙,逛书店的机会本来就不多,即使去,也不会对那些青面獠牙的恐怖故事感兴趣,胆小的女生才爱看呢。
“是写一家齿科诊所里发生的鬼故事。除了诊所的名字,其余的内容百分之九十都是真实的!”
彭七月觉得不可思议,既然是鬼故事,何来“真实”?况且,把一个真实的手机号码写进小说里去,莫非这个作家疯了?
“小说出版后,手机就没消停过!尤其在江苏省《快报》上了连载,我统计了一下,一个月里就有四千多只未接来电!幸亏我没有接听,不然的话,通话费不让我破产,电磁信号也得让我得脑瘤!”
彭七月问:“你怎么不去起诉这个作家,告他侵权?”
“起诉什么呀,机主是我哥,他人都死了,还侵谁的权呀!再说现在的出版商都巴不得别人来起诉自己,等于花钱帮他炒作。哼,我花钱诉讼,让他出名,我才不干这种傻事呢!”
彭七月又问:“这个号码现在谁在用?”
“你听我说下去——”洪本波咽了口唾沫接着说,“打来电话的读者太多了,我烦透了,就去移动公司申请封号,暂停使用,谁想到捅出大篓子啦!139网络瘫痪,该号段的所有号码只能进行网内通话,网外的统统打不出去,连短信也不能收发。一查,是机房的一台贝尔交换机出现了死机,需要重新启动,折腾了一个半钟头才恢复正常。这件事情没有对外声张。后来听说公司高层把这部小说传阅了一遍,一致认为这个号码‘不宜封’,就让它去吧,结果把五十元的月租费也给免啦!”
彭七月问他:“你最近用过这个号码吗?”
洪本波把头摇得象拨浪鼓,“我不是跟你说了?人家不肯封,我也不去用它,反正我有第二只手机。”
彭七月犀利的目光盯住他,“我正在办一个案子,几个当事人都收到过这个号码发出的短信,号码显示是不会错的,肯定有人使用,不是你就是别人。”
洪本波眨着精明的小眼睛,支支吾吾地说:“这个……也许是她干的。”
“她是谁?”彭七月忙问。
“是个女生,年纪很轻。”
“你见过她?她长得什么样?”
洪本波摇头,“从来没见过。她给我打电话,打我另一个手机,说她对这个号码感兴趣,要我转让给她。”
“为什么感兴趣?”彭七月有意放慢了提问的速度,希望洪本波回答慢一点,清楚一点。
“她说这个号码对她有特殊的意义,所以需要它。”
“怎么个‘特殊意义’?”
“她说……代表了她的身世。”
彭七月嘲笑了一声,“你觉得可信还是可笑?一串阿拉伯数字居然能代表一个人的身世?”
洪本波脸一红,“反正她是这么说的。”
彭七月不打算在这些细节上纠缠,示意对方继续说。
“既然她诚心想要,我就开了价,一万元。”
见彭七月露出惊讶的神色,洪本波忙解释,“你不懂,1390是中国移动推出的第一批手机号码,号码越早,用户就越有身价,因为当时一个手机要卖一万元呢,没有财力的人怎么用得起?所以有的人特意要购买第一批号码,想显示身价。”
“她接受了?”
洪本波叹了口气,慢吞吞地说:“她说一万元太少了,她就按这个数字出价,一亿三千九百零一万六千七百三十六元九角三分。”
彭七月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
“她把钱给你了?”
洪本波点点头说:“她很慷慨,给我两个亿,还说不用找了。”
说着,洪本波打开抽屉,拿出一封信,信上的地址是用电脑打印的,没有用手写,洪本波从信封里抽出四张钞票,彭七月一看,“扑哧!”笑出声来。钞票的印刷很粗糙,正面印着玉皇大帝和“阴曹地府银行”的字样,每张钞票的面额是五千万,加起来正好两亿。
“这是恶作剧。”彭七月看着这些钞票说。
“我也这么认为,可是这个号码我已经无法使用了,显然已经归她所有了。”洪本波无奈地耸了耸肩。
“开价一万元的号码,被一个陌生人无偿使用,你就甘心?”
“我当然不甘心,可有什么办法,我不敢追究,这个号码鬼气太重,我还是离它远点的好!”
见彭七月流露出难以理解的神情,洪本波解释起来,“西方人把666认为不吉利,因为它代表了魔鬼撒旦,在中国,凡是有369的地方就有鬼气笼罩。”
彭七月皱着眉头问:“666的典故我知道,369的说法从何而来?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
“唉,你去看看那本小说就知道了!”
彭七月开始怀疑这个洪本波是不是被出版商雇佣了,怎么一个劲儿在推销?
不过既然他这么说,我还真得去看看这本书……彭七月想。
781路公交车载着彭七月离开德州新村,从打浦路隧道返回浦西。彭七月在第一站就下了车,穿过六车道的中山南路,沿着鲁班路漫无目的地朝前走着,满脑子都是那串数字。
当他走到瞿溪路的时候,抬头一看,对面是地铁四号线鲁班路车站。
与艾思相识的那个夜晚,他就是从这儿进去的。
彭七月东张西望了半天,有一个小小的发现:这里没有门牌号。
只是一瞬间,大脑里灵光一闪,他朝路口一名穿黄色制服的交通协管员走去,指着那边客气地问:“师傅,那儿怎么没有门牌号?”
协管员翻着眼睛看了看他,没搭理。
“是多少?”彭七月问。
“你打听这干吗?”协管员反问。
彭七月出示了刑警证,协管员肃然起敬,忙不迭说:“是鲁班路369号。”
“ICE,十九号晚上你在哪儿?”
彭七月尽量显得很平静,这样问艾思。
“晚上?”艾思眨着那双单眼皮的眼睛,笑着说,“不管是十九号还是二十九号的晚上,我永远只在一个地方,做一件必须的事——上床睡觉!我可不是黑花,白天懒洋洋趴着,一到晚上就蹿上房顶不见了。”
对她的幽默,彭七月无动于衷。
“怎么?你又在怀疑我了!”艾思伸出手,拧着彭七月脸颊上的肉,掐着玩,一边说,“别胡思乱想啦,我只有你一个男人,我对天发誓!不信你可以查我的手机,看看有没有异常的通话记录!你是警察,想查这点隐私还不是易如反掌?”
彭七月把她的手抓到手里,捏得很紧,没有放松的迹象。
“说到手机,我正想问你——上个月你有没有跟一个叫洪本波的人发去短信,问他租用一个手机号码,那个号码是13901673693。”
彭七月一边说着,一边留意她脸上的表情。
艾思的表情很惊讶,“什么呀,我都被你搞糊涂了!我自己有号码,干吗还要另外一个号码?退一步说,就算我需要,可以买一个新号码呀,举手之劳,干吗问别人去借呢!”
彭七月咽了口唾沫,耐心解释道,“我在电讯公司查了,你确实给一个叫洪本波的人发去过短信,说你需要他的号码,因为这个号码特别,能够‘代表你的身世’。这些都是电脑上的记录,决不会无中生有的。”
他盯住艾思,认真地说:“艾思,我希望你能够严肃地对待这件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因为它涉及到一宗谋杀案。”
“天哪,谋杀!”艾思似乎吓了一跳,忙解释说,“七月,请你相信我,我从来没有发过那种短信,再说我的身世怎么可能用一个手机号码来代表呢?那只是几个数字呀!”
说到这儿,她若有所思起来,喃喃地说,“会不会是有人盗用了我的号码,想陷害我……”
彭七月没有再问下去。这场看似恋人间的谈话、实质是非正式的审问就这么结束了,艾思没露什么破绽,彭七月也没多大收获。
但彭七月对艾思的怀疑,已经升级了。
当彭七月盘问艾思的时候,在这个城市的某个角落,一对男女在床上激烈地肉搏。男在上,女在下,上面的是托尼,下面的是小苏。
“裁员”一说其实是托尼的鬼话。该部门的六名女职员,除了和总经理有暧昧关系的安吉拉,都必须先跨过他的床才能踏进公司。眼看试用期就要结束了,小苏很想留在这家公司,艾思的离开本来让她松了口气,既然两个只能留一个,艾思走了,她自然就留下了,可是她小看了托尼,这位道貌岸然的男上司其实是采花大盗,哪能轻易放弃这朵唾手可摘的鲜花?
“人员需要调整,不能超过九个,艾思走了,还有一个人也得走,你看着办吧!”托尼的表情始终象那身阿玛尼西装一样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