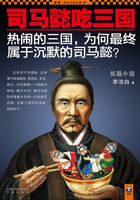灶披间里停着一辆凤凰牌男式自行车,砌在墙内的水泥烟囱一直通到楼上的晒台……彭七月忽地意识到,他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黑猫和周围的器物上了,忽略了一样最重要的东西。
其实灶披间里有个人。
她象猫一样蜷缩起来,坐在小板凳上,低头拣着绿豆,把混在绿豆里的石子和坏掉的绿豆拣出来,动作很轻,很慢,仿佛不是拣,而是数。
她的手指又细又长,关节凸出,纤长的手指是年轻女孩的特征,但眼前的这十根手指,却让彭七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不舒服——它们好象太长了,象外星人的手指。
女孩穿着一条黑色布裙子,一件白色短袖衫,左下角有一只锈花的小口袋,放着一串沉甸甸的钥匙,以至于领口往下坠,露出胸罩的白色带子来。她和艾思一样是平胸型的女孩,戴A罩,几乎没有胸脯,女性的魅力就要靠别的来弥补了。
彭七月有这个本事,一眼就能看出来,这只是第一级别,到了第二级别,能看出这个胸脯是不是靠胸罩才挺起来的,胸罩内层有没有塞水袋。当然还有更高的第三级别,可以看出这个胸脯有没有做过隆胸手术。当然,这种难度系数最大,彭七月远没有达到这种境界,拥有“第三级别法眼”的人,上海滩也不过那么七八个。
女孩默默地坐着,低着头,长长的黑发朝前面披散下来,遮住了面孔。女孩子都喜欢做一个潇洒的甩发动作,让头发飞到后面去,不管露出的面孔是好看还是难看,这个动作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本身就充满了女人味。但是这个女孩没有,她似乎更愿意长头发把自己的面孔遮起来,彭七月想起《午夜凶铃》里的贞子,头发里隐藏的是一张狰狞的脸……
灶披间很安静,一个披头散发坐着的女孩,一只披头散发趴着的猫,一个站在木条门外的窥望者,恰好形成三足鼎立。
喵呜!黑花叫了一声,似乎在提醒主人,有客人。
女孩慢慢抬起头,用外星人的手指把一片头发捋到耳朵后,露出那张脸来——
根据户籍记载,沈云锡终生未娶,只在1952年领养过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姓什么叫什么、从哪儿来,已无从考证。户口簿上她的身份是沈云锡的女儿,随养父姓沈,叫沈晶莹。
1967年2月22日,即沈云锡死后的第十八天,沈晶莹在离家不远的方浜中路上被车撞死,卒年22岁,尚未出嫁。
当沈晶莹把脸露出来的时候,彭七月几乎在心里喊出来:天哪,又一块“冰”!
虽然她的姓名里没有“冰”、“艾思”这样露骨的字眼,但“晶莹”这个词却露了破绽:晶莹为何物?不就是冰块吗?
她的单眼皮、她的嘴形,乃至那张没有喜怒哀乐的脸,那种冷漠的表情,跟艾思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唯一不同的,她的眼睛不象猫头鹰,是一双普通的黑眼睛。
莫非她是艾思的生母?
艾思是1984年出生的,沈晶莹死于1967年,也就是说,艾思呱呱坠地的时候,沈晶莹已经死去整整十七年了,所以她俩不可能是母女关系,那么,她们又是哪一种血缘关系呢?
彭七月深深吸了口气,这种问题实在是“谋杀脑细胞”。
当沈晶莹走过来,把木条门打开的时候,彭七月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忘了自己站在台阶上,险些摔了个仰面朝天。
望着这个提着行李的陌生人,沈晶莹目光里带着警惕,声音不大地问:“你找谁?”
她的声音和艾思的沙哑截然不同,又尖又细,象钢笔尖在玻璃上划过,彭七月在想,如果这种声音发出尖叫的话,绝对受不了。
“我找沈医生,沈云锡,”彭七月把事先准备好的话说出来,“我是慕名而来,求诊的。”
“我爸爸早就不看病了。”
彭七月忙说,“沈小姐,你就行个方便吧,我大老远地跑来……”
“你叫我什么?”沈晶莹翻了翻眼睛看着他。
“小姐”这种称呼,当时是绝对禁用的,如“资产阶级大小姐”就是骂人的称呼。
彭七月忙更正道,“沈同志,你就帮帮忙吧,我……”
“我爸爸正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写思想小结,不可能给人看病。”沈晶莹朝左右看了看,说,“你快走吧,别站在人家门口。”
面对这个“女门卫”,彭七月无可奈何,没想到见这个沈云锡会这么难。正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头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晶莹,让他上来吧。”
彭七月抬头望去,亭子间的窗户开了,探出一个中年男人的头来,头发乱蓬蓬的,小脑袋,戴着一副老式方框眼镜,左边的镜片被打碎,用透明胶布临时粘起来,右边的镜脚掉了一只,就用橡皮筋扎在耳朵上。光看这副伤痕累累的眼镜,就知道他吃过不少苦头。
不用问,这就是沈云锡。
“可爸爸……”沈晶莹朝上面争辩着。
“你不让他进来,人家不会走的,回头让周围的革命群众看见就麻烦了。”沈云锡说完就把头缩了回去,把窗户关上了。
沈晶莹看了彭七月一眼,不大情愿地把身体侧开,彭七月终于踏进了这幢房子。
经过灶披间的碗橱时,彭七月特意朝下面看了一眼,黑花蜷缩成一团,呼呼大睡,并不介意有陌生人进来。
沈晶莹把彭七月带到二楼的左厢房,这里每个房间都有一排高大的窗户,少则六扇,多达十扇,所以房间的光线很充足。左厢房的窗户是朝南的,可以望见一排比人还高的防盗铁栅栏,高高地耸立在大门的门楣之上,尖尖的矛头对准外面。
1958年全国大炼钢铁,街道的群众早就瞄上了这排坚固的铁栅栏,套上绳子,几个大汉在下面吭唷吭唷拉,试图把它扳倒,居然纹丝未动,反而把绳子扯断了。老房子的坚固可见一斑。过去是没有“豆腐渣工程”这种词汇的,建筑商无不视质量为生命。
彭七月坐在一只红木圆凳上,看了看周围,全套的红木家具,大橱、化妆台、床和五斗橱,这些家具要是放到今天,少说值几十万。
沈云锡走了进来,穿着一件白色“的确凉”短袖衬衫,透过薄薄的衬衫,可以看见里面穿的背心全是窟窿眼,真有点欲盖弥彰,刚刚洗过手,带着一股药皂的味道。他在红木圆台前坐下来,先问彭七月,“你怎么知道我家的地址?”
“噢,我去过医院,碰到了张院长……就是张鲁丰,他告诉我的。”
“他已经被打倒了,不是院长了,可不要用这种称呼,被革命群众听见会有麻烦的。”
“谢谢沈医生。”彭七月开始对这个沈云锡有了好感。
沈云锡朝他摆摆手,苦笑一声说,“别这么叫我,我是被剥夺行医资格的黑五类分子。他们担心我在药方里下砒霜,对革命群众进行疯狂‘阶级报复’,所以……”
后面的话,沈云锡没有说下去,便开始例行询问,彭七月把事先准备好的不轻也不重的症状述说了一遍,沈云锡一边听,一边给彭七月号脉、观舌苔,然后就开起药方来。
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的“阶级划分”,全国八亿人民,划分为三六九等。最好的是“红五类”,指工人、农民、商业职工、学生、解放军官兵。最差的是“黑五类”,指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及右派分子。介于两者中间的是“灰五类”,指医生、记者、教师、文艺工作者这些知识分子(俗称臭老九),还有小商小贩小业主,政治上属于小资产阶级一类,需要指出的是,“麻五类”的子女是禁止参加红卫兵组织的。
红五类是当仁不让的领导阶级,如同第三帝国时期的纯种日耳曼人,可以昂首挺胸走在大街上。灰五类属于“被教育”、“被改造”、“可以挽救”的阶层,而黑五类相当于第三帝国时期的犹太人,最终的下场就是两个字:灭亡。
单从成分上来看,沈云锡是中医,理应划入灰五类,但且慢,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是资本家,开过大药房,剥削过劳动人民,沈云锡就是资本家的大少爷,他又著书立说,宣扬反动学术,这又是一条罪状。
沈云锡把写好的药方递给彭七月,看着彭七月的眼睛,冷不防冒出一句话来,“年轻人,你不是来看病的,因为你根本就没病。你来这儿另有目的,是吧?”
彭七月怔住了,没想到这个看似书呆子的沈云锡目光如此犀利,既然这样,就没必要兜圈子了,彭七月打开旅行袋,拿出一本《百冰治百病》放在圆桌上,对沈云锡轻声说:“请你把这本书仔细看一遍,就会明白的。”
这是新版的《百冰治百病》,从封面设计到出版社名称都变了,没有变的是书名和作者,沈云锡稍稍楞了一下,赶快把书收了起来,这一拿一接,有点象敌特务接头。
彭七月问他,“这本书初版的时候,写了多少条冰(病)例?”
“不多不少,一百种。”
“嗯,我给你的这本书是一百零一种,多了一种,它的名字叫‘痔宁冰栓’,前一百种都是口服的,惟独它是外用的……”
沈云锡的眉头越拧越紧,拧成了一个“?”他喃喃地说着,“这……怎么可能?我从来没有研究过外用的冰呀!”
嘭嘭嘭!
一阵敲打声从楼下传来,有人敲那扇木条门,沈晶莹下楼去开门,随着纷乱的脚步声,一群红卫兵涌了进来。为首的是个十七八岁的高中生,正处在荷尔蒙分泌的旺盛期,满脸痘痘,幸亏痘痘是红的,这样一来革命的心就更红了。依此类推,酒糟鼻也是令人羡慕的。
“我们是南市区红卫兵团的革命小将,贴在墙上的‘勒令书’看到没有?”
“什么……勒令书?”沈晶莹声音低低地问。
“哼,资产阶级的臭小姐,原来是睁眼瞎!”
“红痘痘”走到门口,想把贴在东马街墙上的“勒令书”大声读出来,这才发现三天前贴上去的“勒令书”早就被别的大字报覆盖了,只好凭着记忆说道:
“饲养宠物——这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表现!限期三日,让东马街的居民把自家饲养的鸟、鸽子、金鱼、乌龟,还有猫和狗统统处理掉,逾期全部打死!”
他打量着沈晶莹,继续道,“我们是红卫兵团打猫战斗队的。根据群众检举揭发,你们家养了一只黑猫,还给它起了名字叫‘黑花’,一股资产阶级的铜臭味!说,它在哪里?”
“猫……没有啊……”沈晶莹偷偷朝黑花睡的地方瞥了一眼,黑花已经不见了,无声无息地溜走了。
别看红痘痘人不大,心却细,他走到碗橱前蹲下来一看,冷笑一声,“你再敢说你家不养猫?这就是罪证——这是猫窝,盆里还有猫屎呢!”
沈晶莹心慌意乱地说:“它……跑了,看见你们雄纠纠气昂昂的样子,它就给……吓跑了。”
“哼,少拍马屁!是你把它藏起来了吧?要是被我们搜出来,连你一块打死!”红痘痘朝身后一招手,红卫兵们呼啦一下涌了进来,开始在这幢房子里大肆搜捕一只猫。
文革伊始,抄家风席卷全国,沈云锡家已经被抄过三四次了,有区里的红卫兵抄的,地段医院造反派抄的,东马街里弄革委会抄的,除了笨重搬不动的红木家具,其余的古董字画、金银首饰、沈云锡的爷爷和父亲穿过的马褂西装,就连他们的灵位和遗像都被砸得稀巴烂。据说地段医院的造反派在抄家的时候,为了寻找传说中的“发报机”,把楼梯的地板撬起来,结果被一枚铁钉扎破了手,血流不止,沈云锡拿出云南白药来,要给他治伤口,遭到严词拒绝,生怕是毒药。沈云锡告诉他,如不早治,弄不好会得破伤风,对方才勉强接受。事后,云南白药也被当作战利品带走了。
损失些财物,沈云锡倒觉得没什么,让他心痛的是这些年来自己精心搜集的几千册中医药书籍,有的还是珍贵的古籍,有宋版、明清版,统统被抄走,在口号声中付之一炬,化作飞灰。
俗话说虱子多了不痒。今天红卫兵又来抄家,为了抓一只猫,想想实在有点滑稽。所以任凭他们翻箱倒柜,沈云锡岿然不动,不过他把彭七月给的那本书藏了起来。
登登的脚步声,红痘痘领着两个红卫兵走进了二楼左厢房,沈云锡赶紧站起来,恭恭敬敬垂首而立。红痘痘厌恶地朝他看了一眼,把目光停留在彭七月身上,老规矩,先对暗号。
“不忘阶级苦!”红痘痘喊。
“牢记血泪仇!”彭七月站起来喊。
红痘痘问:“你是谁?在这个地方干什么?”
“他是来……”沈云锡刚想解释,红痘痘掉过头来对他大喝一声,“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只许资本家老老实实,不许资本家乱说乱动!你给我滚一边去!”
沈云锡乖乖又把头低了下去。
彭七月知道这些不是街头跳忠字舞的红卫兵,不可能糊弄过去,就把预想好的方案拿出来,“我叫彭七月,是杨浦区防火器材厂的,我们厂革委会的孙主任最近身体不舒服,一直便秘,叫我来问问沈……”彭七月差一点儿说“沈医生”,赶紧改口,“问问这个姓沈的,要他给开个药方。”
红痘痘冷笑一声说:“便秘?自己到药房买点泻药不就行了?你知道他是谁——他是黑五类,反动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这种人根本没有资格给革命群众看病开药,难道你们不知道吗?”
彭七月不慌不忙说:“当然知道,可沈云锡看便秘是最好的,这得实事求是嘛,再说了,即使是废物,也能废物利用,就把他当废物利用好了……”
红痘痘身后的两个红卫兵咧开嘴笑起来,红痘痘回头瞪了他们一眼,把手一摊对彭七月说:“把你的工作证给我看看!”
彭七月掏出一个装有塑料封套的小红本,里面贴有自己的大头照,盖有“杨浦区防火器材厂革命委员会”的大红印章。这是他来之前找那些专门制假证件的人给办的,对方很纳闷,因为他们接的活儿大都是大学文凭、结婚证、身份证、驾驶证之类的,这人居然要一本六十年代的工作证,实在有点离谱,不过他们还是给办了,为人民币服务嘛。
红痘痘仔细地看了看,没看出什么破绽,他的目光往周围一扫,落在彭七月的两件行李上,盯住看了半天,用脚踢了踢它们说:“找人开药方,居然带两大包行李?里面是什么?打开看看。”
两个红卫兵上来就要翻旅行袋和帆布背包,“谁敢动!”彭七月大吼一声,立刻把他们震住了,连红痘痘都倒退一步,吃惊地瞪着彭七月。
彭七月知道,这种时候不来点横的是不行了,软的怕硬的,硬的怕不要命的。他把胸脯拍得山响,大声说:“他妈的,老子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工人阶级是老大哥!你们这些鸟红卫兵是不是昏头了?居然敢检查工人老大哥的东西,看谁敢动!叫他尝尝工人阶级的铁拳!”
屋里的空气一时凝结住了,两个红卫兵把手缩了回去,不敢再碰。红痘痘心里很不服气,他知道,若是一对一,自己肯定不是这家伙的对手,不过仗着他们人多势众,要给这个狂妄的家伙一点颜色看看。
那些红卫兵停止了搜查,朝二楼左厢房聚过来,一时围拢了七八个人,有的人已经把腰里的铜头皮带解了下来,看起来一场肉搏是难免了。
彭七月心里连声喊倒霉,真是最怕什么就遇上什么。开弓没有回头箭,到了这份儿上,不出手是不行了,无论如何得保护行李里的东西,他的右手暗暗往腰后摸,那儿插着一支伸缩式警棍,这是他唯一的防身武器……
沈云锡低着头,一点一点往后退,他知道,在这种时候,自己多说一句,都有可能招徕灭顶之灾。他只是有点想不通,别人打架,战场却在自己的家里……
喵——啊——呜!
一声响亮的猫叫,众人紧崩的神经顿时被牵到另一头去了,黑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了出来,站在厢房门口朝他们叫着,好象在示威,“嗨!我在这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