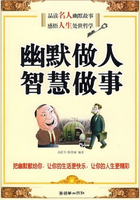他们边吃边聊一些无关痛痒的世俗百态,倒也聊得合拍。
掌舍的胃口出奇得好,每道菜都吃得津津有味。倒是公子南和子渡,都只是轻描淡写地夹一点。掌舍这时只对满桌的美味感兴趣,任他们闲聊,他只偶尔有一搭没一搭地插句话。
夕阳西下,夜幕低垂。街上突然间躁动起来,一只庞大的军队,从街面穿过。
铁蹄阵阵,战车隆隆,碾过路面,发着嘈杂而沉闷的声音。
战车由青铜打造,两匹高头大马拉着,马头戴着青铜面罩,马身披着青铜鳞甲。战车上有三人,都是头盖青铜盔,身披铜片鳞甲,手持长戟、腰佩利剑。按当时的军制,一车乘三人,尊者在左,御者在中,骖乘居右;君王或战争时的主帅居中,御者在左。车右都是有勇力之士,任务是执干戈以御敌,并负责战争中的力役之事。战车左右各立一个青铜巨盾防身,巨盾上的饕餮,张牙舞爪,面目狰狞。
威风凛凛的车兵过后,是手持目雷纹刀,跑步行进的步兵。步兵一般勇猛,敢于搏击,兼善奔跑。作战时车兵坐车行进,在前冲锋,将敌人击落车下,步兵从后斩杀。
“这就是天子的‘六兽之师’的熊师。‘六兽之师’分别是以熊、罴、貔、貅、龙、虎命名,熊、罴两师是先锋,有上将师岩统领。其他四师,直辖天子,有天子亲自统帅,战时出征,休止时戍卫王宫。天子‘六兽之师’前锋出行,不知是哪个诸侯国,又要遭殃了!”子渡说道。
“这是出征宛国。”掌舍嘴里噘着大块的肥***不经心地说道。
“天子为什么要攻打宛国?”子南急切地问道。
“据说,宛国今年没有纳贡。”子渡见掌舍满嘴的食物还没有下咽,就代答道。
“不是说宛国今年遭遇洪灾,颗粒无收,哪还有余力纳贡?”子南愤愤地说。
“似乎天子并不考虑这些。宛国每年向天朝不仅缴纳田赋,还要进献大量的貂裘,白狐皮,海珍珠等奇珍异宝,可今年据说宛国的使者不但空手而来,还向天子伸手请求救济。”子渡说道。
“宛国是王后的娘舅国,天子怎能坐视宛国受灾而不管?”子南说道。
“管,天子当然得管。个把月前天子已经向宛国派送了粮食千乘。”掌舍说道,
“可据知情人透露说,派发救援的不是天子,是王后从自己的采邑征收的粮食,拿去救济宛国的,而且说是要支援千乘,已经运去的不过五百单。”子渡插嘴道。
“难道天子因为这个要发兵宛国?”子南问道,心下不免嘀咕,如果是这样,天子和王后之间,似乎并不像外界传颂的那样美满,难道天子和天后之间也有了裂缝?
“天朝已经在月初就向宛国押运了五百单粮食,剩余的粮食,已经着手准备。宛国承诺来年向天子加倍进贡,以报答天子的救急之恩。至于是天子还是王后,还不是一样,都是一家人。可是,天子突然向宛国大兵压境,内中的隐情,你们知道吗?”掌舍用手摸摸油腻腻地嘴唇,仰着头,故意卖关子地说道。
“为什么?”果然子南和子渡都热切地问道。
“因为一个女人?”
“一个女人?”子南和子渡异口同声地反问道。
“公卿端木大人运送粮食到宛国,见到了宛国国君有一位貌美如仙的公主。据端木大人说,这位公主美到无可比拟的地步,他画了一幅画,给天子带回来,天子见了她,也如痴如醉。遂遣使者到宛国,要娶她为妃。可是宛国的国君不知好歹,竟然婉拒了,说公主已经婚配,婚期在即。天子恼羞成怒,就决定出兵宛国,这只是先锋,天子似乎还打算亲自出征。当然打得旗号是宛国素来桀骜不驯,以遭灾为由,不但不缴税赋,还诓骗天朝粮食辎重,蓄意屯兵造反。”
“用莫须有且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掩盖自己卑劣的行径。堂堂天子,竟如此龌龊。”子南说道。
“不平有什么用!他是天子,全天下都是他的,何况一个女人。也怪宛国国君太不识时务了,招惹这样的祸端。”掌舍不以为然地说道。
“天子已经有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凡一百二十一人。还有各国进贡的美女无数,他还要为了抢强一个女人,发动一场战争。简直荒唐!”子南说。
“男人喜欢女人,就像收刮财物的,那是有瘾。只会嫌少,不会厌多。何况这次,宛国竟敢据婚,一个女人是小事,天子丧失颜面那才是大事了。”掌舍仍是一副无关紧要的口气,淡淡地说道。
“满朝文武都没有反对之声吗?”子南说。
“天子专横,连王后都为避偏袒母族之嫌,不好过问,更逞论别人。”子渡幽幽地说。
子南豁得起来,向子渡说道:“抱歉,夏公子,在下要先行告辞了,感谢您的款待。”
子渡起身挽留道:“天就要黑了,兄台这么着急,冒昧地问一下,你这是要去哪里?”
“我要去宛国。”子南如实说道。
“宛国马上就要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了,你还要去送死吗?”掌舍不客气地说。
“我有亲人在那,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身陷险境,作壁上观。”
“没用的,天子的精兵还没有到达,可是宛国的国都在两天前就被包围了。”
子南和子渡不明就里,对望一眼,同时又把询问地目光投向了掌舍。
掌舍慢悠悠地说:“天子早就下令宛国的邻国——善国和丛国,先行出兵,包围宛城。”
“善国和丛国这不是为虎作伥吗?”
“天子的神威,谁敢不从,刚才精兵的威武,你们也看到了。”
“不行,我一定得去一趟宛国。在下告辞,公子的盛情,子南改日一定再行拜谢。”
“小弟和兄台一见如故,兄台此行凶险万分,请务必珍重,若有机会再见,一定到排兴楼,到时掌柜自会通知小弟前来相会。”
“一定,保重!”子南深情地说道,随即也向掌舍施礼道:“多谢壮士,据实以告。山高水长,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掌舍也起身还礼道。
子渡将子南和问荆送出排兴楼。
子南对子渡说:“公子请留步吧!”
夏子渡却说:“天色已晚,城门已关,兄台在此地,人生地不熟,见到官家,怕不好应付。向阳城的城尹和我略有交情,我去打个招呼,让他给你们行个方面,免得耽搁误事。”
“难为夏公子想得周全!”
“有道是出外靠朋友,不过是举手之劳,兄台何必客气。”
星河街上只有大的酒楼,茶肆,依然灯火辉煌,歌舞升平。
城门关后,万家灯火星星点点,街面上也清冷下来了。
子南和子渡沿着星河街,向着西大门走。子南忧心如焚无心应酬,子渡几句宽慰的话过后,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说什么,二人都沉默了。两人并行往前走,月光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问荆牵着马跟在后面。卫矛还在排兴楼,子渡的身边换了另一个精瘦的黑衣汉子。黑衣汉子对问荆不加理睬,总是保持着与子渡三步之遥的距离,时刻警觉。
走了一炷香的功夫,就到了西大门。黑衣汉子进去和守关的士兵耳语几句,一会儿,一个青衣戎服的人,热情地迎出来。
“这位就是城尹大人。”
“这位是我朋友虞公子!”子渡将二人略作介绍。
两人行揖礼,互相客气道:“幸会!幸会”
子渡深知子南急如星火,就对城尹开门见山地说:
“我朋友,有急事赶着出城,希望大人行个方面。”
“一句话的事!夏公子派人吱一声就行,何必亲自跑一趟。”城尹爽快地说,随即转身大声叫道:“开城门!”
厚重的大门吱吱呀呀地打开,吊桥“哐”地一声着地。子南和问荆跃上骅骝马,拜谢子渡和城尹,一夹马肚子,骅骝马扬蹄而去,两人的身影瞬间就消失在夜幕中。
出向阳城,一轮圆月,已经爬上了树梢头。夜空清碧如海,略有些浮云。月亮像一面的镜子投下冷冷的清辉。群山沟壑,都只剩下一个黑色的轮廓,仿佛一幅静谧、安详的素描画。
这样的夜晚,像一位参禅的老者。
秋意渐浓,夜微凉。一只白狐,突然间跳入他们的视野,像一道白光,撕碎山峰的阴影。它在地面上梭巡,偶尔跳跃穿梭,如同幽灵一般。
子南和问荆披着月光,趁着夜色,往宛国奔驰而去。子南心急如焚。因为天子觊觎的美人,就是他要准备结婚的恋人——宛国国君的掌上明珠——宛若公主。
虞国和宛国一衣带水,世代聚居在淇水的两岸,虞国在淇水上游,宛国在淇水下游。两国王室世代缔结秦晋之好。
当今,虞国国君最宠爱的如姬,就是宛若的姑姑,名曰宛如。宛如虽然长宛若一辈,却只比宛若大五六岁。宛国国君本有意撮合子南和宛如,因为他俩年岁相当。
可是子南,他只钟情宛若。
静谧的夜,奔驰地脚步,耳边呼啸而过的风,拂过他干涸的嘴唇,吹痛了他的双眸,撩起他潮湿的心,记忆如画卷般被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