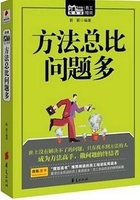安丰塘远在淮南寿州,其塘水溉田数万顷。地产丰沃,民无凶岁。人说国朝覆军丧地自彦贞始,刘彦贞入为神武统军,只因他阿附“五鬼”广遗贿赂,而其财源即是安丰塘。刘彦贞甫任寿州清淮军节度使,即以疏浚城濠为由,大兴工役,决塘水入濠中,于是民田干涸,而征赋益急,民人皆鬻田而去。刘彦贞便择肥沃良田低价买进,复引濠水回流塘中,使安丰塘涨水如初,遂又高价售地。如此买进卖出,岁积巨亿财货。
张洎即是发迹于安丰塘。太学生上书揭发其底细:安丰塘买卖农田的谋划者正是这张洎!那时他在刘彦贞幕帐掌书记。刘彦贞得此妙计暴富,张书记也得获仕进显达的资本。(编者注:这与好莱坞电影《唐人街》的黑幕何其相似!寿州安丰塘。加州橡树关水库。《唐人街》是虚构,《无尽藏》却是史实。)
人说他贪鄙无耻而又好攻人短,而这皆因他自有一套固宠术。笑骂任由他人,我自锐意钻谋。樊若水有国主御赐的金禅杖,这位大司徒又将持何物以示威?
他们带我走过这廊桥,此时无尽藏火势已见小。他们并不带我朝那火场走。这廊桥尽头的匾额是“水穷处”。
他们拐上一条上山的麻石道,这小道通向湖山高处的琅琊台。
望着高台周边起伏错落的山势,我不知自己会被带入怎样的迷境。
他们带我走在盘山蹬道上。
飞檐凌空,古柏森峻,引路禁兵状如青面鬼卒,他们像是在将我引向一个鬼门关。
那几株古柏奇姿异状,或卧地三曲,或形似旋螺,它们盘枝交柯,结构成一顶硕大的华盖,那华盖覆罩着高处的平台。
“几人平地上,看我半天中。”我忽又想到韩熙载那诗句。那高台之上孤亭耸峙,若飞鸟之展翅欲翔。我曾听说那山亭名为“云起时”,此刻却见那额题是“拜月亭”。那匾额依然是云波的形状。
那亭前已有一簇人马在静候。青罗伞下有一张雕花椅,座椅上有一位峨冠博带的大官人。大官人手执一柄雕龙金杖,看似就是樊若水那柄御赐金禅杖。
“禀大司徒,林公子前来叩见。”
那头目唱罢,就凶恶地瞅我一眼。我却不想跪拜。父亲依礼接旨,随即就束手就擒。我并非朝官,就不愿遵从他们的礼数。我拒不跪叩,亦是为维护父亲的尊严。
这大司徒却远非我想象中的嘴脸。我拒不跪叩,他却并不怪罪和动怒。他起身离座,和颜悦色朝我走来。我一时有些发懵,我没想到他竟是一副白面书生样。我想这众人声讨的国贼,本是该有凶神恶煞般的威仪。
“呀!林公子可是受累了。”
声气柔和,举止斯文,跋扈之气全无,真可说是笑容可掬了。他从袖中抖出一块丝帕,伸手揩去我额上的血水。这意外之举反倒使我更清醒,我悄悄收紧背后的行囊。
“好算是机缘难得呢!今见林公子,老夫方知何为‘将门有虎子’!后生可不畏乎?林统军有福!我大唐国有赖!”
“大司徒既为国家着想,就请放家父一条生路。”
“林公子有见识,老夫正是为此而来!”大司徒兴奋地拍下手,就指向一个石鼓,“林公子看座。”
大司徒挥手屏退禁兵,又坐回那雕花座椅。他将金杖斜倚座侧,又给我一个请坐的手势,我便在冰凉的石鼓上坐下。
石桌上有食盒,也摆置着酒榼和肴馔。大司徒执壶斟酒。
“端的是缘分呀!林公子来年应试,没准咱就是你座师!圣上命我知贡举,来年我便主省试,这就少不得要关照你了,有了这般缘分,我倒想先给你透道题呢!来,先与你递个盅儿。”
他双手将琥珀酒盅递与我,我退后一步,又摇头拒请。大司徒抿一口菊花酒,又吃一片酱瓜。
“来年死活都是未知,只想大司徒眼下就开恩,你能确保家父平安无恙么?”
“老夫正是为此而来呀!经此一番变故,林公子想是受惊不小了,眼下究竟就看你如何做!”
“我是说此时此刻,你能确保家父仍是健在么?”
“林公子,你总该晓得与你说话的是何人,佛家无诳语,适间我去看过林将军,也确是与他说了话。”
即令如此,我也难以确信父亲依然平安无事。即令大司徒确是在动身前去见过他,那也该有一个时辰了,而我在灯笼熄灭时的那预感,却是半个时辰内的事。我暂时不想说出这疑虑。
“咱们这就开门见山罢,若是你能如着我的愿,我就担保圣上释放林统军。”
“只不知如何才能如着你的愿。”
“欲得未得之物,此心人皆有之。文士之于奇书,武人之于宝剑,醉翁之于名酒,佳人之于美饰,此乃一往情深,必欲得之而称心意。穷人所需者财,富人所需者官,贵人所需者名,而圣上所需者……”
人说他才疏学浅而又好充斯文,此刻他却是在出口成章。这位大司徒曾以太子党为引援,当年太子弘冀作恶暴毙,他以议谥而得名。国主当年立为太子时,他又入东宫主笺奏。此刻他并不明说国主所需者为何物。欲得未得之物。
“此乃必需之物,必欲得之而免祸患。”
“我不知你们所要是何物。”
“可你定能找得到。”
“也未必,但若能找到,我要当着家父面才会拿交出。”
“正是!老夫亦有此意!”
“可你何以担保国主会开释?”
“圣上自会有圣断。”
“樊若水也说自己是钦差……”
“樊若水呀!你是说那个一苇法师么?幸好你未受了他诳骗!圣上先是遣他来,回头又差遣老夫来,就是防他独吞开溜。”
“可是他有御赐金禅杖……”
“眼下他就只有一根盲杖了!圣上心善耳根软,总是滥赐无度,这些咱都不好说。至于这金杖,也就权当是令箭。时事万急,樊若水出师不利,咱就收回这令箭,他也就不再是钦使。也有一事你须记着,告发林统军的正是这个樊若水。科第落榜,屡考屡败哇!”
大司徒收敛笑容瞅着我,我脸上有他期待的惊疑。
“樊若水,噢,一苇法师不是在江上钓鱼么?某一日他求见圣上,献上他钓的一条鱼,那鱼肚中就有一布团,那上边居然有些个文字……”
大司徒卖个关子,站起身子踱几个方步。
“那鱼肚帛书上写的是‘树下无人被缚,林中有人肇祸’。‘人’即是‘仁’,这后半句就有令尊的大名:林仁肇。”
我如遭重击,一时哑然失语。
“一苇献鱼我在场。”大司徒握一下金禅杖。
“国主会是如此轻信么?谁能担保那布团不是有人塞进去?兴许就是他樊若水!”
“一苇法师有人证。他本是拎着鱼去那李家明家开荤,动刀剖腹就现出了那布团。教坊副使李家明是证人,也有他那妹子作证说,开刀前是活蹦乱跳一条鱼!”
那个楚楚可怜的琵琶女,她也曾帮他们一起作伪么?人心竟是如此之歹毒!如此说来,她在藏书楼身遭不测也就无足惋惜了。而她为何要去藏书楼?莫非也是受了李家明指使?
我忽然又有些后怕。借了那点情色,她或许是为我设下了绮障,幸好我从那媚惑中及时脱了身。那时我确也有些许伤感和迷乱,我当为此而羞愧。忘掉那个狐媚的李家妹,也许她是罪当遭灭。也忘掉那个风月惯家王屋山,尽管我亲眼见她被那假和尚掐死,而眼下我面对的就是她的老主顾。
大司徒是为我而来。
“这些字眼也是牵强,就算有这巧合,‘肇祸’二字也未必与国主相关。”
“祸从口出哇林公子,你就称咱们圣上为国主么?目今天下纷攘,中原贬损咱们国格,降咱们皇帝为国主,可在咱臣民眼中,国君还是圣上啊!不称圣上称大家也好……不过也无妨,幸好只是我听到。”
大司徒又坐回那雕椅,我却按捺不住地站起来。
“家父因一条鱼获罪,圣上的圣明在哪里?”
“少安勿躁,待我说个分明。樊若水带来的不只是一条鱼,还有要命的机密。有个叫史虚白的不知你可听说过……”
我微微垂首,小心地避开他的探究。
“身在江湖,心存魏阙。史虚白从北方携来一件宝物,死前将其传给了韩熙载,韩熙载死前又传给林统军。圣上要的就是这宝物,这宝物关乎圣上的大事业,尊大人却是好不识时务!”
“你说来此之前见过家父……”
“这你情管放宽心,林统军饭也吃得,觉也睡得。”
“家父可对你说过些甚么?”
“尊大人本与国家无嫌,不过是因惧罪起见,此番便只是使倔,武将概莫如此,所以才吃了这般辛苦。这般光景下去,就断断没有活的命了。你读书定然比他多,读书自然明理,自然知时达务,你若献出这宝物,圣上必然欢喜。明里说透这个,你须自作个主张。圣上可是有御限。”
“这却教我怎处?我确实不知你要的是何物。”
“确实……樊若水也是这般说,可他说你定能找到那藏处。”
大司徒反操双手踱到台边,又眯眼望着无尽藏的烟雾和残火,仿佛是为这夜景所陶醉。当他踱到台边时,那些暗伏的卫兵便后退几个台阶。在这园林的最高处,远方的城市尽可一览无余。我默默地望着城市的灯火,那皇宫就在灯火阑珊的夜色深处,此刻那皇宫深处正燃着一盏命灯,我恍若看见那盏命灯飘忽的火苗,那团火苗旋即化作一场大火。他们号叫着逃出火海,那个月白色的身影就是国主,那衣发散乱的鬼魅般的身影,那双细手仍是捏作佛印状……
“大局已危,事机益急,非用林统军为大将,怕是万难支持了……”
这是大司徒若有所思的沉吟声,这声音扰乱了我的幻觉。
“家父正可为国效力……”
“我也曾有几番的力荐,奈何圣上却是有大顾忌。林统军新镇南都,忽有蜜蜂数万飞集其身,左右齐声称贺说,此乃封王之兆!这你想想看,圣上闻知此事会怎想!至于这宝物,圣上却是要用来图大事,再不济,也可用作一番讨价还价。天下至公,非一姓独有。”
我依旧立在原地。我想尽快跟他谈成这桩交易,这也是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并不指望这贼官会履约,只当这是一个脱身之计。
“眼见着就有这大好前程,林公子万不可蹉跎自误,更往远处想,你救国家于危难,也不枉了一个青史留名。今日得此大缘,我倒是真想透给你考题。我且点到为止,却就看你的悟性了。譬如说‘忠臣良臣辨’,治世多良臣,乱世多忠臣。譬如说世道昏乱,就有令尊这等的忠臣。”
“忠臣总为奸臣所害,而国君总是昏昧不明……”
“若说国君不明,忠臣遭殃,历朝历代史不绝书。《韩非子》想必你是读过,那《和氏》一节可也记得?说来我听。”
“楚人卞和得璞玉献厉王,厉王硬说是石块,就砍断卞和左脚。武王即位卞和又献,武王也说是石块,又断其右脚。直至文王才识此玉为宝物。”
“荆山之玉,价值连城。何为天下至宝?不过是一片忠心!若说‘和璧三献’乃绝妙寓言,就是这题意了。只如你能领会,明春就准能高中!”
“这也不敢当。明年的事明年再说。”
“老夫跑题了,也怪我是爱才心切!这也就有漏题之嫌哩,罢了!”
“我若能找到,我总得当着家父面才交出手,也要当着国主面。”
“这个何消说!老夫钦命在身,这就答允你。究竟说来,这是大家脸上都有光辉的事。只是……你得称国主为‘圣上’。”
“我要自己去找,你的舆从断不可盯梢。”
“甚好,量你也难诳我。大司徒自有天罗地网,只是不无担心,因你不知要找的是何物。”
“或许我能找到那藏处。”
“甚好……只管找到那藏处,但恐违了钦限,我只许你一个时辰。”
大司徒仰观天色,又直望着拜月亭的楹联。他扬起金杖指向楹联。
“‘书藏绝妙画,月赏无声诗。’好诗!好书!韩公真乃不世出高人哇!只是这诗句无须乎当真。书藏绝妙画。这秘藏却绝非是一幅画!”
大司徒笑眯眯瞄我一眼,便又扶杖踱步。他轻步舒徐,双脚落地无声,从他身后望去,那身姿好似夹着一条长尾巴。他双脚落地无声,袍带间却有叮当脆响。我忽想到那市井传闻,传闻这位大司徒啬刻成性,家中妻儿难得妄支一钱,他甚至将箱笼锁钥悬挂腰间,走路时便叮当作响,好似妇人家环珮一般。
国朝的大司徒尽是这等贪吝之徒啊!国丈爷周宗富可敌国,却是每日里持筹握算,悭吝超乎常人。我极力排出这杂念。大司徒已在亭侧的石碑下停住。
风扫云开,月色溶溶。这石碑据说是仿照北方琅琊刻石打造,碑文却是韩公本人的诗句。
“琅琊自古出书家!昔有王右军、颜鲁公,今有韩熙载韩宰相,异代之奇呀!林公子识得这碑文否?”
“知是韩公诗句,我也略能猜出几个。”
“可你知这是谁的法书?又是仿了谁的字体?”
“像是徐尚书的法书,秦丞相李斯的小篆……”
“卞和献宝,楚王断其双足;李斯竭忠,胡亥施以极刑。李斯之后,篆书惟李阳冰一人而已。喔哟,有了!老夫忍不住再考你一考。史载李斯也曾留下八字手迹,林公子也能说出来么?”
我立时想到徐尚书书斋里的那书轴,但那只是徐铉的仿李斯小篆。我压根不想为他这些考题而费神。明年的会试与我无关。明年的春天,这个江南唐国还会有读书人的仕途么?国将不国,臣民惟求保命而已。
“李斯原迹并非小篆,那是一种鸟虫书。”
“哇!来年你便是金榜状元了!”大司徒高举起酒盅。
我再也难以忍受他的扯淡。我连州府的解试都未曾经过,怎会有资格赴明年的春闱?莫非他们又要巧立名目设特科?我已是心焦如焚。灯笼已被鬼风吹灭。这恶兆令我抓狂。他限定我一个时辰交货,我也不想拖延到天明。
“古导师有云:宝所非遥,须且前进。目下我也拿这话送你。”
“我是要去来自由,你的舆从若有跟踪,也就休怪我爽约!”
“林公子总可放心!密去密来,老夫在此相候!”大司徒举杖戳地。
城头传来沉沉鼓声。这是三更的鼓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