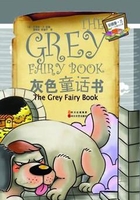有些话题特别引人入胜,可要是正经八百写成小说,那就太恐怖了。假如不希望触犯众怒或是招人厌恶,纯粹的浪漫主义作家应该对此类题目加以规避,只有以严肃而权威的事实真相来作为支撑,方可进行一定的处理。我们读到一些文字时,经常会瑟瑟发抖,感到“愉悦的痛苦”,譬如贝瑞西那战役、里斯本大地震、伦敦黑死病、圣巴托罗缪之夜、加尔各答黑牢里的一百二十三名囚犯窒息死亡,都能给人这样的阅读感受。不过,这样的叙述之所以会激动人心,就在于它揭露了事实的真相、展露出了真实、连通了历史。如果恐怖的表述纯属虚构,则会让我们产生厌恶。
我已提及几场有史记载的大灾难,它们都是那么突出,那么令人敬畏,但是在这些事例中,灾难的规模之大,比灾难的本身给人留下的印象更加的深刻。不必我提醒读者,从人类连绵不绝的超级灾难中,就能列出许多个体的灾殃。在本质上,它们比这些大规模的灾难更具有苦难性。其实,真正的悲惨——终极的悲哀——是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可怕的、终极的痛苦总是由个体来承受的,而不是由群体来承受的——让我们为此感谢慈悲的上帝吧!
不用疑问,在降临到芸芸众生身上的终极灾难之中,人被活埋可谓最恐怖的一种。能思考的人几乎大都不会否认,活埋人的事一直经常发生。隔开了生与死的边界线,是含混而且模糊的。谁能说出生命在哪里便终结、死亡又会在哪里开始?我们知道,有的疾病可以使患者的外观生命机能终止,但恰当地讲,这一终止不过是暂停而已,是我们尚未了解的生命机制的暂时性停止。一段时间后,有某种看不见的神秘法则,会再次开动那些神奇的小齿轮,开动那些具有强大魔力的大飞轮,银链并不是永久性的松弛,金碗也并非知道无可修复。可这期间,灵魂寄于什么地方?
然而撇开这不可避免的话题,撇开这由因及果的推理,生命的暂停是会导致人所共知的活埋事件的发生。医学上和日常生活中鲜活的事例,都可以证明大量的活埋事件的确存在。假如有必要,我可以马上举出好多个真实的例子。一个性质不同寻常的事例前不久还发生过呢,就在临近的巴尔的摩市。它引发了一场痛苦、激烈、大范围的骚动。某些读者可能对此仍然记忆犹新。一位很受人尊敬的市民的妻子——一位杰出律师、国会议员的夫人,突然患上了奇怪的病症。这病让她的医生完全不会知道如何应对。经历很多的折磨后,她死了。或者说人们认为她死去了。没错,没有一个人会怀疑,也许说,没有一个人有理由怀疑她事实上不是真的死了。但从表面上看,她呈现出的全部特征就是平静的死亡:她的脸部轮廓是收缩的、凹陷的;她的嘴唇是大理石般的苍白;她的眼睛光泽尽失。她没有一丝的温度了,连脉搏也停止了跳动。尸体放了三天,变得像石头一般僵硬。总之,考虑到尸体很快就会腐烂,葬礼举行得很是仓促。
那位女士的尸体存放进家族的墓穴之中,此后的三年里,墓窖没有再次被开启。三年期满,因为要放进一口石棺,墓穴终于重见天日了。可是就在那天,当丈夫的突然亲自把墓门打开的时候,可以想象吧。等待他的是怎样可怕的惊人场面!墓门旋转着朝外打开,一个白花花的物件喀嚓响着倒进了他的怀抱。那是他妻子的骷髅。她的白色尸衣并没有霉烂。
经仔细调查,她显然是在被放入墓穴两天之后便复活了。她在棺材里挣扎着,棺材就从架子上翻倒在了地,摔坏了,使她得以从棺材里逃了出来。一盏不经意间留在墓穴中的灯,本来满满的灯油已经没有油了,但也可能是蒸发掉的。在通入墓穴台阶的最高层,有一大块棺材碎片,好像是她为了拼命引起众人的注意,用它在铁门上敲了过去。也许就在她敲打的时候,极度的恐惧令她陷入昏厥或者死亡。在她倒下的一瞬间,她的尸衣缠在了铁门上向内突出的地方。于是,她便腐烂了,可依然直立着。
1810年,法国就发生过这样一起活埋事件。人们自然认为,事实真的比小说还要离谱。故事的主人公是位年轻的小姐,名叫维克托希娜·拉福加德,她出身在名门,极其富有,而且容颜非常美丽。在众多的追求者之中,有个巴黎的穷文人也可以说是穷记者——朱利安·博叙埃。他的才华与善良吸引了那位女继承人,他似乎已经赢得她的芳心。但是最后,她天性中的傲慢却促使她坚决地拒绝了他,然后她嫁给了赫奈莱先生。和这位出众的银行家和外交家结婚后,这位绅士却不喜欢她,甚至不惜虐待她。跟着他不幸地生活几年后,她死了——至少她的状态酷似死亡,看到她的每一个人都被表象所蒙蔽了。她安然的入葬了——但不是埋在墓窖里,而是葬于她出生的小村子,埋在一个普通的坟墓之中。那位记者痛苦欲绝。在他的记忆中,深切的爱情之火从未熄灭。痴情的人从巴黎出发,跋山涉水到了这个偏僻的外省村子。他怀揣浪漫的想法,要把心上人的尸体从坟墓中挖出,剪一束美丽的秀发珍藏。他到达了墓地,于午夜时分把棺木挖出。他打开了棺材盖。当他动手去剪她的头发时,他发现心上人睁开了眼睛。事实上,那位女士是被活埋了。但是生命并没完全离她而去。情人的抚摸使她从昏迷中唤醒了。她的昏迷却被人们误会了死亡。他发疯般把她抱回了自己在村里的住处,凭借丰富的医学知识,给她吃了些补品。最终,她竟然复活了。她认出救了自己命的人。她继续和他生活在一起,渐渐的,她完全恢复了原有的健康。她那颗女人的心肠并非无情,这事给她上了爱情的最后一课,足以软化她的内心。
她没有再回到他的丈夫身边,也没有被他知道自己复活的事情。她把心儿偷偷的许给了博叙埃,和情人一道远离美国。二十年后,因为确信时光已大大的改变了她的面容,不会再有朋友把认出她来,两个人于是又重返了法国。然而他们的想法是错的,一碰面,赫奈莱先生就认出了自己的妻子,并要求她回到自己的身边。但是她拒绝了,法庭判决对此予以大力的支持。说他们的情况很特殊,那么多年都过去了,于理于法,做丈夫的特权都应该结束。
莱比锡的《外科杂志》是一份权威性和价值性很高的刊物,如果美国的一些书商能够买下版权翻译发行的话,那就好了。在该刊物最新的一期上,记录了一起极其悲惨的事件,在本质上,它正合乎我们一直讨论的活埋。
一位身材魁梧、体格健壮的炮兵军官从一匹无法驾御的烈马身上摔倒下来,因头部伤势很严重,当时便失去了任何知觉。他的颅骨也轻度骨折,但是没有直接危险。开颅手术成功完成。他被放了许多血,并采取了其他常规的镇痛方法。逐渐地,他陷入了深度的昏迷状态,而且越来越不可救药。人们都认为他死去了。
因为天气暖和,人们仓促地把他下葬了,地点就是一个公墓,是在周四。但可是就在那个周六,公墓那里和往常一样聚集了大批游人。大约到了中午时分,一位农民说,坐在军官的坟头时,他清晰地感到了地面在颤动,好像地下有人乘机挣扎似的。他的话引起了许多骚动。当然,起初人们并没有在意他说的,但是他惊恐异常,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说法。最后,他的话自然对人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有人马就拿来铲子。坟墓很浅,极不体面,几分钟之内便被挖开了。墓中人的头部裸露在阳光之下。那时,他看上去是死了,但却几乎在棺材中坐直了身子。由于他的拼命挣扎,棺材盖都被他顶开了许多。
他马上被送往最近的一家医院,医生声称他还活着,只不过是陷入窒息状态。过几小时,他便苏醒了。他认出了熟人的面孔,慢慢地说出自己在坟墓中所受的苦楚。
在他的讲述中,人们可以明显看出来,埋身坟墓之后,他在一个多小时内肯定有了意识,之后才陷入昏迷。坟墓是草草便填上的,泥土中有很多透气的小孔,所以非常的疏松。他也就呼吸到了必要的空气。听到头顶有人群的脚步声,他就拼命乱动,想让人们也听到坟墓里的声音。他说,是公墓那些喧嚣的人声把他从沉睡中唤醒的,但是刚一苏醒,他就完全感到了自己的恐怖境遇。
据记载,这位病人情况有了好转,似乎有望彻底的恢复,但却成为庸医进行医学实验的牺牲品而已。他们用上了电池电击疗法。在偶然的意外中,他突然昏迷,一下子便断了气。
不过提到电池电击疗法,我倒想起了一个非常著名的例子。它可真是不同寻常。电击疗法使伦敦一位被埋葬两天的年轻律师重回了人间。这事是发生在1831年。那时,只要有人一谈到这件事,都会引起大片极大的骚动。
这位病人叫爱德华·斯特普雷顿,他显然是死于斑疹伤寒引起的发烧,伴随着令医生都觉得奇怪的一些奇怪症状。在他表面上呈现死亡的状态,医生曾要求他的朋友准许验尸,但是遭到拒绝。如同一贯出现的情况一样,被拒绝之后,医务人员决定将尸体挖出来,从容地进行秘密解剖。伦敦的盗尸团伙多不胜数,他们也很轻易地就与其中一个商定妥当了。在葬礼之后的第三天,这具假想中的尸体被人从八英尺深的坟墓中挖了出,摆上了一家私人医院的手术台之上。
在死者腹部切开一道长长的口子之后,没发现见皮肉有腐烂现象,医生想到了使用电击的方法。一次又一次的击打,尸体依然不动,从所有各方面看,都没有出现什么异常。只有那么一两次出现了痉挛,比一般程度都要剧烈的多,显露出明显的生命迹象。
夜深了。黎明将至。终于,他们认为最好立刻进行解剖。可一位学生想检验下自己的理论,坚持要在死者的一块胸肌上通电。粗粗划了一刀之后,电线便急急地接上了。病人急促地动了一下,绝对不是痉挛——他从桌子上一下跃了起来,走到房子的中间。他不安地朝四周打量了半天,便开口讲话了。他说的话非常含糊,但他确实说出了字句,音节划分得非常清楚。话音刚落,他就轰然倒在了地。
一下子,众人目瞪口呆,都吓得半瘫。但情况紧急,他们的意识很快便恢复正常了。显然,斯特普雷顿先生依然活着,只是又陷入昏迷状态。用了乙醚,他醒转了过来,并迅速恢复健康。他再次回到朋友圈子里。不过,在确定病情不会再复发之后,他才把自己起死回生的事情说给他们。可以想象,朋友们自然非常惊诧,同时又极其狂喜。
然而,这个事例最耸人听闻的地方,还在于斯特普雷顿先生的自述。他自称,他的意识没有一刻是完全丧失的——他一直恍惚着,但恍惚之中,他却知道自己所遭遇的一切。从医生宣布他死亡到最后摔倒在地上,他都知道。“我还活着”——这就是辨明自己身处解剖室里,他拼尽全力说出的那句无人领会的话。
这样的故事轻易就能讲许多出来,但我不准备再继续讲了。活埋经常发生,可我们实在不必以此来证明。当我们一想到觉察这种事发生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就必须承认,它们也许在不为我们所知的情况下,已多次发生了。其实,当人们占用一块坟墓之时,不管目的是什么、占多大地盘,几乎都能发现骷髅,它们都保持着令人极为疑惧可怕的姿势。
这种疑惧确实可怕——但更可怕的,则是厄运。毫无疑问,没有任何经历像活埋那样,能使灵与肉的不幸达到极至。肺部的压迫不堪忍受,泥土的潮湿令人感到窒息,裹尸布裹绕着身体,棺材逼仄,紧紧包裹着自己,夜晚的绝对黑暗,深海般的寂静压了下来,虫豸虽说看不见,但却能感觉到,它们征服了一切——加上还会想起头上的空气和青草。忆起好朋友,想着他们一旦得知我们的厄运便会飞身前来拯救,可又意识到他们不可能获悉到这一点。令我们对命运绝望的,只有真正的死亡。这样的思绪和坟墓中的感觉混杂在一起,给尚且跳动的心脏带来巨大的恐怖,既骇人听闻,又无法忍受,无论怎样大胆的设想,都难以达到这一境界。我们不知道,人间还有什么比这更痛苦。而且,做梦也想像不出地狱到底有多恐怖,我们想不出有什么可怖的事能赶得上它的一半。然而,凡是关乎这一类话题的叙述,都能引起深切的兴趣。不过,鉴于人们对这一话题敬若神明,这种兴趣又恰恰奇特地取决于我们是否信服所讲事件的真实性。我现在要讲的,是我自己的真实感受——纯粹我自己的亲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