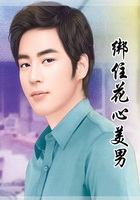观闻人自叹如泥鳅
潘源盛水果行老板王国生并不反对杜月生加入青帮,认为有了这层关系,杜月生外出提货销货可以更加顺畅,水果店也可以不受地痞流氓的欺侮。但杜月生心里却越来越不安,他总想赌赢几次为店里补上亏空,却输得更惨了。
袁珊宝多年以后回忆说:“想当年,有一次月生哥赌铜钿输脱了底,他自己的衣服不能脱,就叫我缩在被窝里不要起床,把我的衣服裤子裹成一卷送进当铺,当点钱来作赌本。我躺在床上暗暗祝祷: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保佑月生哥这次赢了能赎当回来。我身上只有内褂内裤,他输了我就不能出门啦。”
如此下去当然不是办法。一天晚上,杜月生彻夜难眠,思来想去。当年自己在高桥镇赌棚惨败,舅舅绝情地把自己赶出家门。如今,情深义重的好兄弟知道自己这样做,肯定会翻脸……杜月生简直不敢想下去了。他宁愿让朋友背后恨他骂他,也没有勇气当面被恩人责骂。
第二天清晨,他不辞而别,投奔师父陈世昌。这位“老头子”虽然早已不玩街头套签子的游戏了,但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营生,就介绍杜月生到花会赌场谋个拉生意的差事,行话称之为“航船”。
花会是当时上海流行的一种赌法。庄家列出36个人名,写在布幅上公开悬挂,称为“花神”;再从36个人名中任选其一,背着赌客写在另一布幅上并卷成圆筒,也悬挂起来,称为“彩筒”。随后赌客也在36个“花神”中任选一个,将其名字记在一张纸条上,并写上自己所押的赌注,投进一个密封的柜内。接着就开彩,如果赌客所选的人名与庄家所选的人名不同,自己所押的赌注全部输给庄家;如果哪位赌客猜中了庄家写的人名,庄家按照赌注的二十倍赔付。赌场庄家是一人,赌客是多人,再加上庄家善于玩弄手脚,所以常来赌的人最终要输给庄家。
杜月生本来就玩过这种赌法,与赌场老板混得很熟,又有青帮罩着,靠“航船”也能弄几个钱,但有一次得罪了比较厉害的赌客,连师父也保不了他,只好东躲西藏避风头。由于经常陷入经济困境,杜月生就依仗帮会势力,联络以前的小兄弟,干些“收小货”“拉船”“拆梢”之类的勾当,甚至学会了到各家小店铺收点“保护费”。
“收小货”就是强行包买走私货。有些轮船水手从香港等地带来一些走私货,上海当地的各家店铺派出小伙计到码头上购买。杜月生就带几个泼皮兄弟拦住小伙计,威胁说:“侬(你)是掮了招牌格,阿拉(我)是日吃太阳、夜吃露水格。识相点,给阿拉一条生路,不然要侬好看!”穿鞋的怕光脚的,店铺伙计只好把走私货让给杜月生等人。
“拉船”就是在码头上强行以低价买货。杜月生等几个人拦住往上海运送蔬菜瓜果的小船,威逼货主远远低于市价出售,再转手卖出。
有一次,杜月生“拉船”时遇到另一伙小瘪三,双方为抢生意发生争执。杜月生看自己一方势弱,就来个不吃眼前亏,暂时把这笔买卖让给他们。事后,他经过一番打听,找到前几年在街上认识的“花园阿根”顾嘉棠,请他帮忙。顾嘉棠还真没忘记旧情,又亲自出手帮助杜月生,把那伙小瘪三狠狠教训一顿,那伙小瘪三服气后也加入杜月生的小团队。
“拆梢”,就是“敲竹杠”。比如,有的客商在旅店吸烟,杜月生等人就过来硬说商人私售洋烟,索要5元银洋,否则就把他拉到公堂接受重罚。客商为做生意,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愿意花钱消灾。
有时实在没有什么寻钱之道了,杜月生就带几个混混兄弟在街头游荡,看到哪家店铺生意好、人气旺,就假装上前帮助招呼顾客,然后找到店主,说这些顾客都是自己引来的,要求支付报酬。如果店老板不同意,他们就整天在店铺前面打架,把顾客都吓跑。那个年月负责治安的巡捕房也不愿管这类小事,店老板无奈,只好向杜月生等人交点“保护费”。
杜月生就这样混过一秋一冬之后,时光就到了1908年的春天。
3月5日这一天,上海有一场盛典——第一辆有轨电车正式通行。这路有轨电车是英国人在三年前成立电车公司时开始筹建的,总共花了三年的时间,按照今天的方位来说,是从现在的西藏路沿着南京路向东铺轨,一直铺到南京东路外滩。
这路电车每趟可坐24个人,可当时上海的中国人都不敢去乘坐,大家纷纷传说:“电车电车,车上有电,乘了触电,一电完蛋。”为了辟谣,英国商人决定搞一场隆重的通车典礼。
到了这一天,电车棚顶上插满了“万国旗”,从始发站开出。乘坐首班车的是一批特邀乘客,包括洋人、中国著名买办和几位“海上闻人”。一路上,观者如潮,大家这才相信乘电车毫无危险。而此时,一直挤在人流中的杜月生却另有一番感悟——他正在琢磨电车上那几位“闻人”发迹的历史,有关故事还是从师傅陈世昌那里听来的。
杜月笙看着电车上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大家指指点点说他就是上海大名鼎鼎的“赤脚财神”虞洽卿。他也是十五岁到上海瑞康颜料行学生意,去店里那天正赶上天降大雨,他把母亲精心缝制的一双布鞋揣在怀里,一路赤脚,进门后脚下一滑,摔了个仰面朝天,气得店老板当时就要把他轰出去。幸好带他来拜师的介绍人会打圆场:“恭喜老板,这小老弟在地上真像个大元宝,这是财神进门、大吉大利啊。”老板仔细一看还真有点像,这才转怒为喜,收下这个小学徒。后来他步步上进,在洋行当买办,三年前帮一位来自广东的妇女跟英国人打官司,名震上海,现在自己开办了私人银行。
再看那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他就是那个会说洋话的朱葆三。他十四岁那年到上海一家卖小五金的协记商号当学徒,看到上海是个十里洋场,华洋杂处,洋行势力很大,就省吃俭用学了几句“洋泾浜”英语,后来发了大财,继续给洋人拍马屁,先捐出舟山路地段上的一块空地皮给英国租界当局造监狱,又捐出一条马路给法租界。
还有那个坐在电车里扬扬得意的郑伯昭,幼年也学过英语,三十岁进入推销雪茄烟的永泰栈,起初是一名职员,不久跃居为合伙人。前几年,在中国的英美烟草公司面临倒闭危险的时候,郑伯昭给头头们出了几个歪点子,偷偷地把“皇后牌”改成“强盗牌”“老刀牌”“仙山牌”,于是在中国打开销路,洋烟草公司发了大财,提拔郑伯昭当上公司的买办。
杜月生看看他们,想想已经二十岁的自己,既感到自愧不如,又觉得很不服气。这些人的出身不比我强,只是运气比我好。我的聪明也不比他们差,可到现在还是一个小瘪三,关键是我没有找到一个好靠山,特别是没有门路利用洋人。
杜月生百感交集,他在心中正定决心:在大上海的机会多得是,无论是什么门路,一旦让我遇到决不放过。别人是鲤鱼跳龙门,即便不成仍然是江里的鲤鱼;我是河滨里的一条泥鳅,先要修成鲤鱼,然后才有资格跳龙门。以后我干任何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攀大树迈进黄公馆
杜月生跟随陈世昌混日子,再次落魄起来。一晃又过了半年多,转眼又是深秋季节。他尽量躲着潘源盛水果行和王国生,连他最铁的小兄弟袁珊宝也找不到他了。可是有一天,袁珊宝还是看到他与“老头子”在一起,赶忙过来打招呼问候师父、师兄。叙礼完毕,袁珊宝趁陈世昌与别人谈事的机会,拉着杜月生来到僻静的墙角。
“你怎么不回潘源盛了?”小师弟劈头就问。
“这……”杜月生憋了半天才说出口,“我赌铜钿用空了店里的钱,王国生一定对我恨之入骨,我哪还有脸去见他自讨没趣?”
“天地良心!”袁珊宝迫不及待地替王国生喊冤,“国生哥天天都在念叨说:‘也不知道月生哥跑到哪里去了,我们店里少了他,生意做得越来越不好。’这么长时间了,你欠店里钱的事,我从来没听他提过一个字。”
一听这话,杜月生心头涌起一股暖流,眼泪差点流出来。他自幼孤苦,最看重朋友感情,也最好面子,此刻感到王国生对自己恩重如山,就想回去再帮王国生做生意。他拉着袁珊宝来到“老头子”面前,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令杜月生没有想到的是,师父陈世昌不但丝毫没有怪罪的意思,还面露喜色,说杜月生将来肯定会有出息,鼓励他回潘源盛要好好干。
陈世昌一辈子也没混出什么名堂,后来,成为海上闻人的杜月生把这位师父养了起来,不但供给吃喝用度,逢年过节还请他到杜公馆观看大众聚赌,赌场上收的采头也全部孝敬给师父。陈世昌有个很败家的儿子,赌输了之后被债主追讨,杜月生两次出钱援助,一次给25万块大洋,另一次给2万块大洋。钱又被这个败家子输光后,陈世昌再也没脸求杜月笙了,竟然被儿子活活气死了。
杜月生面带愧色回到潘源盛,王国生欢天喜地走出店门迎接他,对亏钱的事一概不提,对待他一如既往。杜月生也专心干活,即使赌博也不再动用店里的钱,偶而还用自己的工薪去“花烟间”散散心。当时上海有“风雅”气派的妓院分为“书寓”“长三”“幺二”三个档次,“书寓”里面艺妓居多,多数是卖艺不卖身。“花烟间”属于第四个档次,在嫖妓时可以吸几口大烟,比简陋的“燕子窝”强那么一点点。杜月生此时还不吸大烟。
杜月生还结识了一位人称“大阿姐”的花烟间女老板。这位“大阿姐”认识很多三教九流白相人,在十六铺一带很吃得开,她与杜月生的好兄弟顾嘉棠很要好。上海花烟间的妓女当时流行结拜“十姐妹”,所谓“十姐妹”并非都是女的,而是九女一男或十女一男。这个男的被称为“大阿哥”,必须是能在世面上立住脚的猛人,或者是黑社会中有势力的人物,十来个妓女与他结拜,为的是做生意时不受小瘪三的敲诈和伤害。顾嘉棠会些拳脚功夫,遇事敢出手,是大阿姐这个花烟间里的大阿哥之一,到这里来消遣自然不用太多花费。所以,杜月生在这里经常与顾嘉棠会面,哥俩的感情也越来越铁。
此时的杜月生虽然又有了稳定的工作,但已加入青帮,又经过前番闯荡,在十六铺一带的小混混兄弟中已经小有名气,被称为“军师”,大家遇到什么小事还要找“水果月生”帮助摆平。杜月生也发现,对于自己的能力来说,水果行这种生意实在是小事一桩。
正当杜月生想着怎样才能出人头地的时候,机会还真来了。有一天,杜月生正在街上无聊闲逛,忽听有人在后面叫:“月生!”他回头一看,连忙转身答应一声:“黄爷叔好!”
这位“黄爷叔”名唤黄振亿,在青帮中与陈世昌是同辈兄弟。此人也是庸庸碌碌之辈,比“套签子福生”混得还差,人们都叫他“饭桶阿三”,但杜月生见了他总是恭恭敬敬,他也认为杜月生聪明、机警,是个能做大事的料。
“听说你回潘源盛了,怎么还是不得意的样子?年纪轻轻,靠白相混时光,成何事体?”
“爷叔教导有理。”杜月生只好应对着。
“月生,你是个有志气的人。”黄振亿拍拍杜月生的肩膀,很诚恳地说,“如果你还有上进的心思,我可以推荐你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八仙桥同孚里。”黄振亿压低声音神秘地说,“黄金荣老板的黄公馆。”
一听“黄金荣”这三个字,杜月生的眼睛瞪得像铃铛一样大,还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这个名字早已如雷贯耳,对于杜月生这样的小人物来说,这位法国巡捕房里的华探头目是端坐在青云里的大人物,简直就是财势绝伦,八面威风,高不可攀。
同孚里距离民国路不远,那一排两层楼的房子里住的,都是在法租界响当当的大阔佬。那整条弄堂的房子都是黄老板的,他自家住一栋,余下七栋住的都是他的朋友和手下。
黄公馆附近人来车往,门庭若市,那些进进出出的人个个趾高气扬。杜月生无数次走过,总是远远望两眼,从来不敢靠近,就连黄公馆进出的小当差,都让他羡慕得不得了。杜月生有过各种飞黄腾达的幻想,唯独没敢想过攀上黄金荣这棵大树。
黄振亿连喊几声,才让如痴如呆的杜月生回过神来:“爷叔,我真的可以进黄公馆?”
“看你说的,我和你师父都是“通”字辈的人,如果没有把握,会对你闲讲?如果你愿意,现在就去收拾行李,我马上就带你去。”
杜月生大喜过望,连忙应承,返回潘源盛的路上,脚步都轻飘飘的。他先到隔壁店里把好消息告诉袁珊宝。正在地上清理水果的袁珊宝一听也是笑逐颜开:“月生哥,你这次算是一步登天了。”杜月生这才想起还没和王国生商量一下,他和袁珊宝一起出来走进潘源盛。
王国生听说这件事后,也为杜月生高兴,说:“这可比在我这小小水果行中强多了。你去吧,肯定会发达。万一有什么不如意处,我这里也随时欢迎你。”王国生还帮他找了几件像样的衣服,包在行李中。杜月生向外走时,袁珊宝又提醒一句:“黄公馆厨房间里的马祥生是我们的同参弟兄,有什么事情他也会照应你。”
杜月笙来到和黄振亿约定的地点,已经是下午,二人一同向孚里走去。道路很熟,杜月生真想跑到前面,但他还是克制住兴奋的心情,亦步亦趋地跟在黄振亿的身后,边走边听“爷叔”的嘱咐,满口答应着。
到了同孚里弄堂,看见黄公馆的大门了,杜月生的心情却逐渐紧张起来。他想,等会儿见到黄金荣,他会不会看中我?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一个个派头十足,杜月生想,只要黄老板能用我,我以后也要从这里进进出出了,可我能干什么呢?
转眼间已经来到弄堂口的街楼下,只见一条长板凳上坐着几名彪形大汉,都一身黑色褂裤。黄振亿很亲热地和这些保镖打招呼,这几个人皮笑肉不笑地点点头,让他们进去了。杜月生心想,这几个家伙的胳膊比我大腿还粗,看来我是没有能力当保镖的。
走进大门后,黄振亿不时与一些人打着招呼,还告诉杜月生这些都是什么人,应该怎样称呼,杜月生此时正想着自己的前途,听过之后根本就没记住。两人直奔客厅。
黄金荣在同孚里居住时,房子的客厅并不是很大,各种陈设也远不像后来钧培里的黄公馆那样豪华奢侈,但室内古色古香、中西合璧的布置已经让此时的杜月生感到光彩夺目、富丽堂皇。他不敢四处张望,默默看着坐在方桌周围玩牌的几个人。
“老板,”黄振亿走上前说道,“我介绍的那个小伙子,已经给你带来了。”
“喔。”一个身材偏矮的胖子应了一声,转过脸来看杜月生。只见这位黄老板长得方头大耳,圆眼阔口,脸上还有一些麻点,两道目光一瞬间已经把杜月生从头到脚扫了两遍。杜月生不由得微微低下头,不敢与他对视。杜月生觉得时间仿佛都凝固了,半分钟就像半天那样长。黄金荣终于缓缓地说:“蛮好。”
杜月生一颗悬着的心顿时落了下来,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
“你叫什么名字?”黄金荣问话时和颜悦色。
“小的姓杜,木土杜。名月生,月亮的月,学生的生。”识字不多的杜月生自报家门时倒有几分文气,又简明又得体。
黄金荣哈哈大笑,向在座的几位赌友说道:“真是缘分,给我帮忙的小朋友们,个个都叫什么生,在老天宫戏院帮我的是苏州的徐福生,照应前堂的是顾掌生,后面厨房里管事的是苏州的马祥生,今天又有了杜月生,好,好,都是来生财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