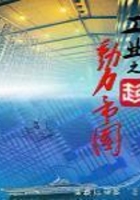四个人推开门,抬起张小林就往外走,杜月生一挥手,十来个人一拥而上,眨眼之间就按倒四个巡警,堵住他们的嘴,5分钟后,巡警们爬起来大喊捉人,张小林与那些人早已不见踪影了。
杜月生把张小林交给“吊眼阿定”安顿,嘱咐好生照顾这位爷叔,便与马祥生匆匆赶回黄公馆了。
张小林死里逃生,休养十来天,身上的伤也好了,就暗中打听,得知将他往死里整的稽征吏头目名叫“金狮狗”,他咬牙切齿要报仇雪恨。张小林不方便再找杜月生,便请“吊眼阿定”助他一臂之力。
这“吊眼阿定”也是个闲不住的角色,在小东门一带以卖拳头而闻名,谁家有事,赏他几角钱,他便出去替人家出了这口气。这一次青帮爷叔相求,岂有不帮之理;再说他自己在码头上也与“金狮狗”有些过结,对这人看不顺眼,所以就答应张小林整治“金狮狗”。
依张小林心中的本意,真想一下子结果了“金狮狗”的性命,可是,他在杭州已经有一条人命在身,而且“吊眼阿定”以后还要在码头上混生活,所以也不想把事情弄大。那年月,能混上个稽征吏头目的人都是有些来历的,他草菅人命害死老百姓可以不了了之,如果老百姓把他弄死了就难以逃脱。
张小林很快谋划出一个办法,“吊眼阿定”佩服得直点头。
结死党成立小八股
一天上午,“金狮狗”一个人在码头上转悠,东瞧西望,各条船上的商人都和他打招呼,有人还把一些家乡特产或上等烟酒送给他。忽然,他看见离码头很远的地方有一条较小的船,有几个人上上下下,好像在往岸上搬东西。
“这些大胆赤佬!”“金狮狗”嘴里骂着,向那边走了过去。他以为这是一些小商贩为躲避码头稽查在远处卸货,心中暗想,这回一定要狠狠罚他们一笔钱。
“金狮狗”来到船边,见几个卸货的人都躲进船里不出来,他就踏着跳板来到船上,看见一个船舱就冲了进去。一进舱门,身后突然闪出四个蒙面大汉,他来不及反抗就被按倒了,堵住口捆住手脚。
船立刻向江心驶去,顺水行过一段路,离码头更远了,有个人把“金狮狗”口中塞着的破布扯了出来:“金狮狗先生,咱们可以聊几句了。”“金狮狗”喘了一口气,抬眼一看,对面站着一个人,对襟褂裤,正是张小林。
“林生!光天化日之下,你想干什么?”“金狮狗”吃了一惊,但口气还很硬。
“哈哈,让你认识大爷!”张小林左右开弓几记耳光,打得“金狮狗”嘴角流血:“实话告诉你,老子我不叫什么‘林生’,大号张小林,在别的地方就打死过人,宰了你就像拍死一条虫子!老子与你有什么冤仇,你那天就想下毒手?”
“金狮狗”闻言,自知今天凶多吉少,口气立刻就软了下来:“张大哥千万别误会,那天也是执行公务,你又打伤一名稽征巡警,他们才想害你,并不是我的主意。还望高抬贵手,你要钱给钱,要占码头给码头,以后但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
“够了!别跟老子玩这一套。”张小林打断“金狮狗”的话:“这一次并不想要你的命,否则也不跟你废话了,现在就给你种荷花!记住,我的朋友们都不是好惹的,以后你夹好狗尾巴,别再自找麻烦,否则就活到头了!”
“多谢张大哥宽宏大量。”“金狮狗”这才放心了,又试探着说:“这条船是张大哥的?有什么需要小的去办的事,尽管吩咐。”
“这条船是我们弟兄几个硬借过来的。”张小林说着用手一指,“船主在那边,此事与他们无关。”“金狮狗”这才注意到,有一个小商贩模样的中年男人躲在船舱的角落里,吓得什么话也不敢说,浑身都有些发抖。
“弟兄们的意思是……”“金狮狗”想不出这些人要怎样处理自己,心又悬了起来。
张小林面带微笑,不慌不忙,话语越来越和气:“承蒙你棍棒疏通经脉,本人的筋骨更加强壮了,总想报答你老哥厚爱。那天晚上你想请我饱喝江水,我当时正是口渴难耐,也想承情,可惜中途被几位朋友拉到别处去了,没能承受你的赏赐。今天嘛,我特意请尝一点有滋味的东西。”
张小林一边耍着贫嘴,一连问旁边的人:“靠近了吗?”
“靠近了。”一名蒙面大汉答道。
“好。酒宴准备妥当,请‘金狮狗’先生入席!”张小林伸手做了个请客的动作。
四名大汉立刻把“金狮狗”拖到舱外,抬起来就往船下抛。“金狮狗”仰面朝天,本能地一歪头,眼睛只看到下面的江水,吓得大喊“饶命”,话音还没落,扑通一声落在一种糊状液体中。
原来,在张小林那条船的下面,有一条农民运送大粪的船。“金狮狗”正好落在粪舱内,真可谓激起民愤(粪)。粪船上的农民看见抛下一个捆绑着的活人,也顾不上害怕,只好想办法赶快救他,而张小林等人哈哈大笑着把船开远了。
上海的码头待不下去了,张小林只好再躲到别处去,好在他结识的各路朋友有很多,总有收留他的地方。后来,杭州官府发生许多变化,张小林打死人命一案被搁置不提了,他又回到家乡公开露面。
就在张小林整治“金狮狗”的时候,杜月生也在帮助桂生姐整治英租界的沈杏山。
近一段时间,不断有人向桂生姐报告,英租界巡捕房探目沈杏山,已经把触角伸进上海当时两大缉私机关——水警营与缉私营。身为沈家“大八股党”成员的郭海珊、戴步祥担任了这两个营的营长。他们利用工作之便,把抢烟土改为收保护费和包运烟土,于是官盗合一,缉私机关变成最大的走私团伙,贩毒事业由暗转明。烟土一至吴淞口外,便经过他们,一路通畅地运到英租界出卖,从而控制了上海的大部分烟土生意。
桂生姐就询问手下:“那些土商的货源在哪里?”
杜月生说:“除了从外国运来以外,华人烟土商还有潮汕、两广、山西、云贵与川湘五大帮。山西帮从陆路运进上海,其余几帮大多通过水路,从吴淞口进外滩上岸的。”
“那沈杏山在什么地方接手?”桂生姐又问道。
顾掌生说:“潮汕帮与两广帮的烟土一般是由海面运到吴淞口外,再由沈杏山派船去接应,由水警营与缉私宫护送,稳稳当当地进入英租界烟土行仓库。”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大八股党”和土商们就不把法租界的黄金荣看在眼里了。在岸上贩卖烟土的土行多半开设在英租界,而法租界地小、人少,力量有限。“大八股党”收了土商的保护费以后,一般只向法租界黄金荣这边打个招呼,分一点俸禄,自以为这样也就够了。
可桂生姐岂是这么好打发的?她让顾掌生去接管别的事情,把抢土这方面业务全权交给杜月生,要求他拿出一套打中沈杏山要害的方案。
杜月生虽然不读书,却自幼喜欢听书,对《三国演义》中偷营劫寨的“智取”故事知道不少。三天后,杜月生有了对策。他认为,现在“大八股党”人多财大,又有官府势力,与他们公开硬拼肯定吃亏,所以,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搜罗亡命之徒,组织一支精干队伍,躲在暗处,神出鬼没,专门去抢由“大八股党”出头保护的土商烟土,逼他们让出利益。
听了这个对策,黄金荣当即表示赞同。桂生姐却不免有些担心:“重利之下,亡命之徒不难找到,可要找几个既有真本事又忠心不二的人,就不那么容易。”
“对,选好人手最重要,我听说过一些朋友,可以找找看。”杜月生此时在心里已经有了初步的人选。
得到黄家夫妇首肯之后,杜月生立刻开始招兵买马了。他首先确定核心骨干“四大金刚”,分别是顾嘉棠、叶焯山、高鑫宝、芮庆荣。
第一位顾嘉棠,在前面已经出场多次了,不再细说。
第二位叶焯山,老家在广东潮州,自幼来到上海,曾经在美国领事馆开过汽车,由于车上常插美国国旗,他得了个“花旗阿根”的绰号。他冷兵器善使短柄斧头,火器善使手枪,出手动作快,枪法奇准。如果有人把一枚硬币抛向天花板,他抬手一枪就能击中。
第三位高鑫宝,上海本地人,小时候当过球童,在网球场上给外国人拾球,耳濡目染之间学会了英语,曾经在怡和洋行当仆人,也当过汽车司机。他个子高,头脑灵,好勇斗狠,曾经加入过“斧头帮”,在赌场砍伤过赌客。
第四位芮庆荣,出生在上海漕河泾,铁匠家庭出身,身有蛮力,性格暴烈,有一次用门闩打老婆,一失手竟将老婆给打死了。
除了“四大金钢”以外,杜月生还物色到四员干将,分别是杨启堂、黄家丰、姚志生、侯泉根,都是有些故事的人物。找齐八个人之后,杜月生还举行了一个特别的仪式,在“关帝神明”像前点燃蜡烛,焚香磕头、歃血为盟,虽非替天行道,亦属盗亦有道。
杜月生论年龄不是最大,但他被尊为盟主,跪在前排正中,其余八人分列两行跪在其后,齐声说道:“关帝神明在上,我等弟兄,同闯码头,决不相叛,有钱同得,有难同当,若有异心,天诛地灭!”誓毕,九个人端起一碗酒,每人割破手指滴血其中,轮流饮下。
就这样,威镇上海的“小八股党”就正式产生了,背靠黄金荣,直接听命于杜月生。杜月生对他们一不摆架子,二不充派头,亲亲热热,不分彼此;出则同行,食则同席,再加上所干的行当又有可观的工钱,把这八个人笼络得死心踏地跟着他跑。队伍建起来了,就要通过实战来锻炼和检验。杜月生严格制订行动方案,精密调查,妥善布置。他避实击虚,专攻“大八股党”的软肋。
财大气粗的土商们不惜血本,常以10万银元的运价包租远洋轮船的部分货仓,直接从国外运送烟土到上海,数以吨计。船只抵达上海附近的公海,与吴淞口岸的沈杏山互通电报,于是“大八股党”出动小舢板,由水警乘船保护,列队驶往公海接驳。货一上岸,经高昌庙、龙华进入英租界,换了便衣的武装军警身带短枪沿途保护。
遇到有人抢劫烟土,便衣军警可以开枪射击,但“小八股党”在杜月生亲自率领下,趁月黑风高或雨雪载途之时出动,看准一个空隙立刻一涌而上,抢到一包两包掉头就跑,来无踪去无影。“大八股党”运烟土水陆兼程,战线拉得很长,内部又有人向外送情报,虽然人手众多,仍然对这种抢土“游击战”防不胜防。
土商付出巨额保护费之后,烟土还是不断被抢,“大八股党”的威信直线下降。外表文弱的杜月生组织得力,指挥得当,亲临战阵,能够从戒备森严、如临大敌的押运行列中虎口拔牙,令黄金荣和桂生姐刮目相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