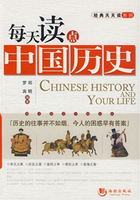我进门时看到的便是这样一番景象,心中对素兰颇为同情,更看不惯舒宁的嚣张跋扈,未及多想,出言讥讽:“姐姐说的是,再怎么着也不能丢了皇家颜面。”走到素兰身边,握住她的手,以示安慰。
遂又转头看着舒宁,含笑道:“姐姐出身相门,家世显赫,自是幼承庭训,应该明白言辞犀利,便显得心胸狭隘,更有仗势欺人之嫌乃女子德行之大亏。姐姐惩治鼠窃狗偷之人本是好意,若是因此坏了姐姐贤良的名声,姐姐岂不亏了?”
“你……”舒宁脸色铁青,被噎的说不出话来。我看着她吃瘪的样子,心中暗呼痛快,决定趁热打铁再气气她,“姐姐一口咬定素兰拿了您的银票,妹妹心中奇怪,这银票都是朝廷所发一模一样,姐姐怎么断定这银票是您的呢?还是姐姐一叫,银票就会答应你呢?”
舒宁趾高气昂道:“我玛法是一品大员,一等公爵,这里只有我可以拿出这么多的银两。”
我和舒宁争执不下,锡兰此时站出来看着众秀女:“锦月小主说的不错,为公允起见,舒宁小主能否先将银票交给奴婢?”
舒宁纵然张狂,但毕竟还没有入选,对锡兰还是有几分顾忌,于是将手中的银票交给锡兰。
锡兰接过银票问舒宁:“舒宁小主,请说出银票的数目?”
“银票总共三千两,两张一千两,两张三百两,一张二百两,两张一百两。”
锡兰听后并没有急着查验而是看向素兰问:“素兰小主,你说呢?”素兰似乎被舒宁的气势惊着了,手心全是汗水,张张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感觉到她的畏惧,我鼓励道:“素兰,怕什么?我们又没做过,说!”
素兰看了我一眼,深吸一口气:“我的银票是一张一千两,一张八百两,一张五百两,两张二百两,一张一百两,共计两千八百两。”
锡兰听后仔细数了数手里的银票,抬头看着大家:“银票跟素兰小主说的无误。”
舒宁大喊:“怎么可能?那我的银票跑哪去了?”扭头看着锡兰,“区区几千两银子,我不在乎,可从小到大,还没人敢动我的东西。既然素兰这里的银票不是我的,那么姑姑,不妨搜检所有秀女和陪侍丫鬟的包袱,最终还是找得到的。”
我看着大喊大叫,不依不饶的舒宁心中不免有些鄙视,亏她也是侯门千金,竟如此不稳重,真枉费老天赐给她的如花容颜和显赫家世。
锡兰听后一脸为难,能在钟粹宫待选的秀女,即便家世不如舒宁,可也是官宦千金,从小金奴玉璧的伺候着,包袱说搜检就搜检,颜面何存。若是传扬出去,不是锡兰一个小小掌事姑姑担当的起的。
我看出锡兰的为难,上前几步,走到舒宁身边:“姐姐这话有些过了,纵然佟佳氏门庭显赫,可我们也是官宦千金,再者到了这里大家身份都一样,都是小主,没有谁比谁高一头的说法。”
一番话说的舒宁脸色涨红,哑口无言。但若细想想,舒宁纵然张狂,可想来也不会胡说,钟粹宫出了鼠窃狗偷之事,此风断不可长。想着便说道:“姐姐的钱也不能白丢,妹妹有个建议,不如到姐姐房中看看,或许会有些线索也未可知啊。”舒宁没有说话算是默认。
舒宁推开门,大家一起进去。舒宁拉开梳妆镜上的小抽屉,转身对大家说:“我的银票原来就放在这里,现在不见了。”
不经意间看见梳妆台前有些红色的粉末,凑上去,发现打开的小抽屉旁边的夹缝里也有一些红色粉末,心中奇怪,扭头瞥见一旁的妆粉盒,一一打开比对,发现胭脂盒里的胭脂摔碎了。心念一动,看着舒宁:“姐姐的胭脂平时是放在左边吗?”
“不是,胭脂是经常用的东西,放在左边太不方便了,我平常都是放在小抽屉旁边的。”
“那姐姐有没有失手将它摔在地上过呢?”
舒宁不满道:“你开什么玩笑,我怎么可能那么粗手粗脚呢。”
舒宁如此肯定,我心里明白了几分,顺手将胭脂盒放在梳妆台上,弯着腰在人群中慢慢走着,仔细的查看众人的衣服和鞋子。从头走到尾,没有找到我想找的东西,正疑惑是自己推测错了时看到一个丫鬟一探头就缩了回去,我心中疑惑,喝道:“你站住!”随即走了出去。
走出房门,认出那个丫鬟是钟粹宫小厨房的粗使丫头小雯。我注意到她的裙摆上有些红色印记,鞋面也有红色的粉末,于是问道:“小雯,你的手绢呢?”
小雯抬头瞟了我一眼,小声说:“奴婢的手绢不见了,怕是丢在哪里了。”
我冷笑一声:“不是丢了,而是你将它扔了,因为你是贼,舒宁小主的那三千两银票是你偷的。”
小雯慌忙跪下喊道:“冤枉啊。”
我看着她:“冤枉?那你身上的红色印记和鞋面上的红色粉末是哪里来的?”小雯听后脸色煞白。“说不出来了,那我来说,舒宁的胭脂有摔过的痕迹,梳妆桌抽屉旁边的缝隙和地上都发现了红色的粉末,这应该是小偷在偷银票时因为很慌张失手所致。现在你的身上有于胭脂相同的印记,而你的手绢是擦拭过洒出来的胭脂,太过显眼被丢掉了。我说的对吗?”小雯此时已经瘫软在地,浑身发抖。
舒宁上前扇了小雯一巴掌,接着又要打,我忙拦住她:“你要干什么?每个人不论贵贱都有自己的尊严,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去践踏别人的尊严,她犯了错自由宫规处置,轮不上你!”舒宁瞪着我,愤愤然站在一边。
锡兰喊道:“来人!”两个小太监走了上来。“小雯偷盗财物带下去交给那总管,按宫规处置!”
此时的小雯跪在地上哀求:“姑姑,奴婢的母亲得了重病急需用钱,奴婢一时糊涂才做下这糊涂事,姑姑饶命,姑姑饶命啊!”两个太监不理会他声嘶力竭的呼喊,毫不留情的将她拖下去。
回到房中,素兰拉着我的手,唤了声“姐姐。”话未出,泪先流。我知道她是感激我今日帮她,伸手拂去她的泪水:“不要这样,你我同是背井离乡,本来就应该互相照应。”素兰听后更是感动,握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松开。扶着素兰坐下,吩咐莲儿为我们沏两杯茶,边喝边聊。
选秀的日子渐渐临近,素兰也越发紧张,她担心自己不能入选,连日来忧思恐惧竟病倒了。于素兰来说,成为皇上的宠妃是她内心最深处的渴望,我却不能理解,也无法理解。可后来想想,便释然了,对于这个时代的女子,她一生的宿命注定与家族荣耀息息相关,没有自由,更别说是爱情。有时细细思来,倒真的可怜可叹。
与素兰一起病倒的还有舒宁,连日来舒宁神思倦怠,浑身无力。锡兰奏请内务府请了太医医治,也开了方子,可几副药吃下去却没有起色。近几日更是连床都不下了,也不见人。
我趁她睡着时去瞧过一眼,眼窝深陷,脸色惨白,憔悴不堪。若再不好,以她这幅光景,就算她家世鼎盛怕也要被撂牌子。我虽与她不睦,此时也不免动了恻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