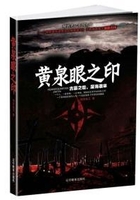冯长平由于还没有进干休所,组织关系仍然在计划部,他每个月的月初都要到办公室交一次党费。
退休时间比较久了,部里的那些局长、副局长,冯长平大部分还都认识,其他的年轻干部,有一部分叫得出名字,多数都是陌生面孔了。他每次向党小组长交过党费,如果邱正良没有开会或有其他的急事要办,他就会到继任部长的办公室坐一会,打个招呼或者说一会话。
冯长平今天交过党费,听秘书说邱正良在看文件,就进了他的办公室。
邱正良对冯长平一向很尊重,他让秘书给冯长平泡了一杯茶,笑着问老部长:“最近身体怎么样?还是‘心中无事一床宽,一觉睡到日出山。’?”
冯长平也笑着说:“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近年来的身体大不如以前:迎风淌眼泪,撒尿滋脚背,躺下睡不着,坐着打瞌睡。”
“人逐年衰老是自然规律,关键是要拥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和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邱正良安慰冯长平。
“你讲得很对,良好的心态是一个人身体中最需要的营养,而良好的生活习惯是身体各部件正常运转的润滑剂。对于老年人来说,未来岁月是人生存折上有限的余款,用一分就少一分。所以,要精打细算,合理安排,不能花光,更不能透支,要不断提高生活质量,争取健康长寿。”
冯长平看到邱正良在认真听自己讲话,又接着说:
“像我们这些退休的老干部,对物质占有的欲望越来越小,对精神慰藉的需求越来越大。除了组织的照顾和家人的关心,与其他人的沟通和理解,也是老年人精神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原来老战友互相想念了,大家聚一聚,聊一聊;后来改成打电话了,不见其面,只闻其声;现在倒好,电话也不打了,逢年过节时,自己或者是让子女发个短信了事。先进的联络方式把人们相互之间心的距离隔得越来越远,原来都把战友都装在心里,后来把名字记在电话薄上,现在都将信息存在手机里,有的人手机一丢,仅存的战友情谊也没有了。”
邱正良对冯长平的话表示赞同,也不无忧虑地说:“我很快就要加入你们的队伍了,像我们这个级别的人,退休以后不愁吃穿,不怕生病,有房住,有钱花,最容量失落,最害怕孤独。不过,我有思想准备,退休后就重新营造适合自己的生活圈子,包括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和培养个人爱好。”
“你的想法很好,我最近刚报名参加机关老年大学,主要学习书法绘画,觉得很有意思,生活也很充实。我准备动员老伴一起参加学习,免得我去上课了她一个人在家里觉得孤单。”
“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件事,部里原计划最近在研究所对年轻干部进行轮训,但是,乔新安要去国防大学学习三个月,因为这件事是他主抓,就只好推迟了。乔新安可能还没来得及给您讲,在两期的年轻干部轮训班上,想请您分别讲一次发扬革命传统的课。”邱正良认真地对冯长平说。
冯长平听了邱正良的话,连忙摆手说:“老一套行不通了,现在有些年轻人最不愿意听老人讲过去的事,很多家庭子女与父母的主要矛盾,就是说者有意总想说,听者无意不想听。”
邱正良知道冯长平的话是谦虚,也是无奈,便给他做工作说:“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后来觉得不对。当年你给我们讲老传统的时候理直气壮,我给年轻人讲老传统的时候就有些底气不足,总怕他们不爱听,看来这样下去不行,多年来被我们称为‘传家宝’的东西要丢。讲传统不是让现在的人干过去的事,而是要让他们继承和发扬先辈们的那种精神。”
“你讲的很有道理,但是,现在很多事情,道理上讲得通,实践中行不通。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根源,就是有些领导自身不正,也无法正人,以至于成了道理与实际两张皮。比如社会上一些党员不像党员,他们不过是党员中的‘膺品’;一些干部不像干部,他们不想干事,只想‘进步’。其实有些道理他们比谁都懂,对于个别领导来讲,把他们在大会上讲的话记录下来,就是很好的政治课教材;把他们私下里做的事列举出来,就是证据确凿的犯罪事实。”
冯长平说这些话时有些气愤难平。
邱正良劝冯长平说:“有一句话叫做‘少怕贪色老怕气’,老部长不要为社会上的一些不良现象生气。外边的有些事我们管不了,争取把自己管辖的事情办好,不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我们这些人,一辈子接受正面教育,也从正面教人,什么情况下都不会对国家、对组织有二心,不管风雨有多大,一路同行到天涯。我就是这样,平时做人办事把握几条原则:有时候如果不便于说真话,起码不能讲假话;有些事不得不考虑自己,但是决不能损害别人;对部属和别的同志能办的事不推,不能办的事不吹。”
“你讲的这些话我很赞同。”冯长平点点头,接着又问邱正良,“刚才你说乔新安要到国防大学学习,我怎么没有听他讲?”
“昨天刚来的通知,他肯定是还没有来得及对你讲。”邱正良回答。
“去国防大学学习的干部一般都是预提对象,乔新安是不是要接你的班?”
“这可不好讲。”邱正良笑着说,“计划部有个好传统,用人不仅看才,更要看德,这一点您比我更清楚。乔新安当副局长、局长的时候,在群众中就有很高的威望,他不会为达到个人目的到领导家送贵重东西,别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送到他家的贵重东西,他有的退还别人,有的交给组织,被群众称为‘无缝钢管’。我还欣赏乔新安一点,就是说到做到不放空炮,如果他把自己的心掏出来放天平上称一称,你会发现,与他说出来的话是同样的重量。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他的很多方面都是跟老部长您学的。上级领导向我征求新任部长人选意见的时候,我推荐了乔新安,听说他要去国防大学学习我也很高兴,但这并不代表新任部长人选就一定是他。您知道,现在仕途上人满为患,经常堵车,社会上不按常规走路的人太多了,最可恨的是有人不遵守交通规则,随意加塞和超行。”
冯长平感慨地说:“你讲得很对,如果考察和任用干部都由‘组织’按原则去办,重视群众的意见,事情就会办得比较公平,也能够做到公正,群众看干部的眼光一般都不会错,关键是有些领导的意见重于组织的意见,或者是个人的意见以‘组织’的形式出现,这样有些问题就不可避免了。一个领导有一个领导的好恶,就像有的人想把手擀面烫曲了泡着吃,有人想把方便面熨直了煮着吃。正因为如此,一些人习惯于在不同的领导面前投其所好,他们之中,有的因自己的优点而得势,有的因自己的缺点而受宠,群众最讨厌的就是这些人,大家心里都清楚,凡是善于讨好领导、在上司面前当孙子的人,一般也是喜欢在群众面前当爷爷的人。”
“老部长看问题很尖锐,话说得也很尖刻,有些话我们只能在私下里讲一讲,犯点自由主义。”邱正良笑着对冯长平说,‘欲知上山路,须问下山人。’有些事我还会继续请教您,但是,刚才谈论的话题就此打住,以后少讲,还是那句老话:相信组织,相信党。”
冯长平看看手表,见时间不早,邱正良面前还有一大摞文件没看,便起身告辞。
鲍清彦最近由于上网时间多了一些,原有的生活规律被打破,造成身体不适,喉咙疼痛,前两天还有些低烧,门诊部的医生到家里连续三天给他输液,直到今天早上他才觉得身上轻松了一些。他坐在轮椅上,在客厅里指挥小翠给花浇水,给欢欢喂食。
老关从厨房里端出来一碗煮好的白糖银耳汤,递给鲍清彦说:“你不要没事找事干了,北京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但是咱们家的花不少都是被水淹死的,给花浇水要见干见湿,前天刚浇过,今天怎么又浇?欢欢也不能一天喂好多次,你看它现在胖得动都不想动了。你要是在屋里着急,我还是陪你到楼下活动活动,我从窗户上偶尔还能看到冯部长夫妻俩在楼间的小花园散步,你如果出去碰到冯部长,可以与他在一起聊聊天。”
“我今天身体刚好一些,还不想出去。你说这个冯长平,我与他讲好了让他经常给我通电话,他有快一星期的时间没有理我了。”
鲍清彦的话刚说完,身边的电话铃响了。
鲍清彦抓起电话,大着嗓门喊:“你这个家伙,在我们家装窃听器了吧,怎么刚说起你,你就来电话了。”
冯长平在电话线的那一端说:“我刚才耳朵发热,心里猜想一定是你在讲我的坏话。你这个老东西是不是上网入迷,有好几天没有到楼下活动了,我每次散步走到你家楼前就对方洁说,我想进楼看看老鲍上网,他现在的水平肯定大有提高。方洁说,鲍部长要是上网上得正有兴致,你去了不是干扰他吗,所以我就没有去见你。”
鲍清彦爽朗地笑着说:“上网真不是上年纪的人干的事,时间长了,眼睛发涩,脖子发直,嗓子发干,浑身发酸,照这样下去用不了几个月,你别看我上网,还是看老关上坟吧!”
“你这个老东西,净胡说八道,上网的事悠着点,别把身体搞坏了。人们常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故,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以后去哪里找你这样肝胆相照的老朋友吹牛聊天去?”
“我也是这么想,人生道路万千条,终点都在奈何桥,但是,能晚走的就不要早走。再说了,我也不能今年在‘这边’刚过了重阳节,明年到‘那边’又过清明节,那样也太累了。”
“你是越扯越远了,给我汇报一下,这几天身体怎么样?”
“不怎么样,前几天一直发低烧,好像是有点感冒。”
“你这个老鲍,无组织无纪律,不请示不报告,谁批准你感冒、谁批准你发烧了,现在怎么样?”
“今天好多了。”
“人到了一定的岁数,抵抗病毒的能力就差了,你要注意起居饮食。对了,我们家孩子昨天刚给我送来一盒燕窝和几袋即食海参,你吃了不一定能治病,但是可以补充营养、增强免疫力,一会儿我给你送去。”
“不敢当,不敢当。”鲍清颜一只手拿着电话,一只手乱摆,好像冯长平能看得见。
“你也学会给我客气了,年轻时可是没少与我抢东西吃。”
“我年轻的时候嘴馋,总是想吃好东西,看见肉就像熊猫看见竹子、兔子看见萝卜一样。但现在就是喜欢粗茶淡饭,像别人说的什么转基因食品、有机食品,还有什么、什么食品一时说不上来,我都不感兴趣。唉,老冯,你说说,将来的科学不知道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说不定公马的睾丸里能挤出酸牛奶来,母鸡的肛门里能下出咸鸭蛋来。”
冯长平在电话里笑了,对鲍清彦说:“你的想像力很丰富,这辈子没当作家可惜了。”
“我这样的大老粗还能当作家,肚子里的墨水不够染肠子,自从当了副局长以后,包括以后的局长、副部长、部长任职期间,我的讲话稿都是别人写的。”
“你总是说直政部的老林这不好那不好,听说人家的讲话稿从来不让别人写,最多让部属找些素材,尔后自己动手。”
“别提老林,提起他来我就生气。前天他儿子还给我打电话说,鲍伯伯劝劝我爸我妈吧,都是六十大几快七十的人了,还天天吵着闹离婚,他们不嫌丢人我还嫌丢人呢!我先给老林的老伴打了个电话,劝她说,你要想开一些,现在忠诚可靠、一心为家的男人,与大熊猫一样稀少,与金丝猴一样珍贵,你不要总想着把老林拴在自己的裤腰带上。老林白天帮朋友跑跑生意,晚上与女人跳跳舞蹈,不会把你怎么样,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只是想尝尝天鹅肉的味道,并不想把天鹅当配偶,公癞蛤蟆想与自己过一辈子的,还是母癞蛤蟆。”
冯长平在电话里笑出声来:“你这是在劝人吗?明明是糟蹋人家老太太。”
鲍清彦不以为然地说:“我讲的是实话,我就不信老林能与他现在的老伴离婚,再去娶个年轻姑娘。”
“你这话别说得太早了,有人讲过,现在对有些男人来讲,有奶便是娘,对有些女人来讲,有钱就是郎。老林不一定去追求年轻女人,但有些年轻女人有可能会别有用心地算计他,她们中的有些人高明得很,把你的心、肝、肺都摘走,让你不到医院照爱克斯光都发现不了。”
“在这个问题上,你的有些说法我同意,有些年轻女人找年老男人,为了爱情的也有,但是不多。现在的一些年轻女人,头发长,见识更长,嫁给老头,不过是你先当郎,我后当‘狼’,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房。但是,对于老林这个人,我比你心里有数,他的心眼不少,筛子底一样,这个问题的后果他还能够看得透。给老林的老伴打过电话,我又给老林打电话,臭骂了他一顿,我对他说,你的脸很白,但是心很黑;你的嘴很甜,但是手很辣;你的胆子小,但是欲望大;你的情很薄,但是脸皮厚;你现在面前的路有很多条,但条条都是通往万丈深渊,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你说你当了领导以后就不会写讲话稿了,可是,骂起人来,排比句倒是编得挺快的,有些话也太难听了。”
“我当时也是给他气急了眼,急中生智嘛!你知道,我这个人肚子里一根直肠子,从嗓子眼通到屁股门,有什么话一下子就倒了出来。”
“他没有给你着急?”
“他敢给我着急?惹恼了我,让他与我一样,下半身残废、性功能丧失。我们俩的关系你可能还不是十分清楚,当年我们在工程团工作的时候,我是连长,他是指导员,我们连是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英雄连队,我是团里树立的先进典型,后来我破格提拔为团副参谋长,他还是指导员,半年后才调到团政治处当宣传干事。我调到北京的机关工作时间也比他早两年,他刚到机关的时候,在我面前毕恭毕敬,当了直政部的副部长以后才牛气起来。老林是个书生,胆子小,在集体宿舍里,蚊子打个喷涕能吓得打个哆嗦;我是个粗人,胆子大,黑夜里敢一个人躺在停尸房里听死人打呼噜。老林平时能言善辩,巧舌如簧,那一天,我在电话里连骂带损,奚落了他半个小时,他原本就怕我,加上理亏,屁都没敢放一个。”
“你这个老鲍,别看没念过几年书,说出来的话很有意思。”
“讲得很对,我在连队工作的时候,战士们都喜欢听我的实话实说,不喜欢听老林的高谈阔论。他们说,我们希望鲍连长的讲话像女人的头发,越长越好,希望林指导员的讲话像女人的裙子,越短越好。”
“我们俩别在电话里胡扯了,你等着,我一会就把孩子带给我的东西给你送过去。”
鲍清彦又开始摆手,着急地说:“你不要送,我、我真不要!”
“要不,你让小翠到我家来取!”
“那、那好吧!”
鲍清彦难为情地说。
乔新安已经在国防大学学习了半个月,他每周日下午到学校报到,每周五晚上回家休息,分管的工作暂时交给了殷副部长。
为了保持对部里工作情况不间断地了解,乔新安让崔秘书将一周的有关文件集中起来,每个星期六的上午到办公室看半天文件。
这天上午,乔新安从办公室看完文件回家,一进宿舍楼门口,看到冯长平站在自己家门外,对着门铃,一副想按欲止的样子。
乔新安感到很奇怪,老部长虽然住在他的楼上,上下楼都经过他家门口,但是很少到他家里来,有什么事需要与自己面谈,也是一个电话“你上来一下!”乔新安就会放下手里的事,赶快上楼。乔新安心里也清楚,老部长与他的感情很深,但是,他看不惯龙传珍盛气凌人的样子和那种强势作风。
冯长平听见脚步声,扭头看见乔新安,红着脸说:“我还以为你在家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