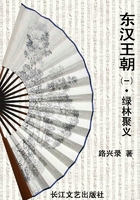晓刚平时循规蹈矩,与世无争,但人生的道路一直是高低不平,而且收费站太多,每走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他高考时,刚过本科录取线,好不容易才在北京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到处跑招聘现场,找关系,投简历,才有了一个并不理想的工作;结婚以后没过多久安稳日子,妻子又有外遇,离婚后人财两空;现在又有病住院,真是屋漏偏遭连阴雨,破船又遇顶头风。冥冥之中如果真是有一个关注和决定着人世间芸芸众生命运的“老天爷”,那他一定是患了青光眼,或者是应该配一副老花镜了。
崔莹听说儿子脖子上被查出长了肿块,吓得快要精神崩溃了,整天以泪洗面,妈妈对儿子的爱有多深,有时是要用眼泪的重量来衡量的,尽管眼泪在很多时候无助任何问题的解决。晓刚出生以后身体不太好,虽然娘家、婆家的人经常到县城帮助排忧解难,但是,由于任春华不在身边,让她最难以承受的,不是生活的重担,而是精神的重负。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甚至更早一些时间,军队基层干部两地分居的很多,离婚的也比较多。军人的妻子,不少在生活困难面前表现得异常坚强,成为甘愿付出的军嫂。也有一些在孤独无助或巨大的思想压力下止步退却,成为让人理解和同情的离异女人。
崔莹在艰难的生活中挺了过来。
任春华尽管有负疚和沉痛两块石头压在心上,但从表情上看,要比崔莹镇静得多。晓刚是什么病还有待确诊,如果他真正是得了难治之症,着急又有什么用呢,当你改变不了现实的时候,只有勇于面对现实。
任春华一直认为,男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拥有自己的一片天空,经风雨、见世面,而不应当在父母的羽翼下避风躲雨。晓刚由于身体和意志方面的原因,可能还有家长引导的不当,在阴云雷电面前畏缩不前,并没有达到自己期望的结果。
任春华也做好了思想准备,如果晓刚这次患了家人不希望有的病,自己要尽一个父亲的责任,用理解、热情和爱心,填平两代人之间那条鸿沟,并且要请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手段,为他会诊、治疗,使他早日康复。
晓媛由于晚上没有休息好,第二天早上感到头重脚轻,她心事沉重地刚到医院换好工作服,手机响了。
是秦月芳打来的电话,她那爽朗的笑声,晓媛平时觉得那么亲切,今天觉得有些刺耳。
“你回北京了吗?”晓媛问。
“没有,我现在在天津郊区。”
“你长时间不在家,把郑叔叔一个人留家里,就那么放心,还不赶快回来,又去天津郊区干什么?”
“一个大老爷们在家有吃有喝的,我有什么不放心的。我回老家也不是参加乡村几日游,而是去看望小荔的爷爷奶奶。我本打算在家住半月二十天就回北京,后来小荔的奶奶不小心摔伤了胳膊,我才又在家照顾了老太太一个多月。我这次回北京等你郑叔叔办好了退休手续,我们还要一起回去。我现在来的这个地方是你郑叔叔工作过的老部队,距离你爸爸原来工作过的部队不远。我以前从农村到部队探亲时认识的几个老姐妹,现在多数也随了军,她们邀请我来这里见见面、说说话。”
晓媛看了看手表,快到交接班时间了,便催促秦月芳:“秦阿姨,您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回北京以后咱们再聊,我要上班了。”
“别急别急,我还有件要紧的事要对你讲,不说出来憋得慌。”秦月芳加快了说话的节奏,连忙说,“我昨天晚上与几个姐妹在饭店里吃饭,看见一个姑娘与你长得一模一样。开始我很惊讶,以为是你到这里来了,朝她喊了一声‘晓媛’,她扭头看了看我,理都没理,我才知道是认错人了。你说说,她长得与你一模一样,是不是侵犯了你的肖像权?”
晓媛听了秦月芳的话,吃惊得手机差点掉在地上,楞在那里几秒钟才回过神来,结结巴巴地对秦月芳说:“秦阿姨,我,我要去接班了,这事你千万别、别对其他人讲。”
在科里的交接班会上,晓媛目光呆滞,心不在焉,像刚害了一场大病,以至于科主任在说话时,探询的眼光几次从她脸上掠过。
晓媛曾经怀疑过自己不是现在父母的亲生女儿,因为自己与哥哥出生的时间间隔太短,而且从外表看,晓刚人高马大,身材如爸爸,面目仿妈妈,而自己娇小玲珑,身材与长相与爸爸妈妈都无相同之处。但是,晓媛想到爸爸妈妈对自己多年的疼爱和呵护,又为自己曾经的怀疑感到内疚。刚才听了秦月芳的话,她忽然想到,爸爸在天津当过兵,难道自己是爸爸妈妈抱养的,而且那里还有一个孪生的姐姐或妹妹?
晓刚的检查结果出来了,他颈部的肿块是甲状腺结节,结节的体积比较大,需要手术。尽管这样,一家人仍然喜不自禁。多少天来晓媛提到嗓子眼的那颗心也落到了肚子里,她想起有人说的最令人感到欣慰的一句话:不是你买彩票中了五百万,而是你的肿瘤是良性的。
过了两天,晓刚的另一项检查结果也出来了,他患有双相情感障碍,也就是抑郁症。看到这个检查结果,晓媛刚刚放回到肚子里的那颗心又悬了起来,她没有对爸爸妈妈和哥哥细说,只有自己心里清楚,这是一种不会危及生命,但却是比较难以治愈的病症。
晓媛值完夜班,先去刚回到北京的秦月芳的家里,反复叮嘱她,不要再对任何人提起天津那个与自己长得很像的姑娘的事,然后就急忙往晓刚住院的病房赶。
推开病房大门,晓媛惊奇的发现龚长治正在与晓刚又说又笑。
龚长治扭头看到晓媛,调皮地笑了一下,对她说:“你在这里看到我肯定想说‘怎么又是你?’我先告诉你,崔助理病愈上班了,处长说我前一段时间一个人管两个人的事比较辛苦,让我休假二十天。我准备利用这二十天的时间,写一份关于军队医院如何解决本职医疗任务和开展对外有偿服务之间矛盾的调查报告,要经常下病房了解情况,今天来这里刚好看到任大哥,就随便聊了一会。”
晓媛表情复杂地朝龚长治笑了笑,没有说什么。
龚长治走后,晓刚告诉晓媛,龚长治这个人很幽默,讲话非常有意思:“我对他说,我虽然从小就身体不好,但是没有住过院,住院的味道真不好受,应该是与坐牢差不多。他说,在限制人身自由这一点上,住院与坐牢差不多,如果说住院如同坐牢,那么,你好比‘一审’被判了‘死缓’,‘二审’改判‘有期’,下一步好好治疗,争取‘提前释放’,重新获得自由。”
晓媛把削好的一个苹果递给晓刚,不高兴地说:“别听他瞎胡扯,什么乱七八糟的。”
晓刚接过苹果,高兴地说:“不能那样讲,他的话我爱听,我说我在医院只吃饭不活动,身上的肥膘会越来越厚。他说现在我身上的肥膘不算太厚,是‘肥而不腻’。我问他,你这样爱说爱笑,小时候是不是很调皮,他说他小时候是个好孩子,上小学时一个学期就五次因为拾金不昧受到老师表扬。我说你在什么地方捡那么多‘金’,他说他将捡到的一张五元的票子换成零钞,每次只给老师交一块钱。唉呀,真是笑死人了!”
晓媛知道龚长治讲的是自己曾经听到过的一个笑话,不过,她没有说穿。她现在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哥哥高兴。
晓刚今天的情绪不错,他吃完苹果,感慨地对晓媛说:“我住院的这几天,看到别的病号有的来有的走,心里苦辣酸甜咸,五味杂陈,感觉到了生命的宝贵,也看到了生命的脆弱。人活在世上的时间性是有限的,应当珍惜生命,善待生命。”
晓媛高兴地说:“你能认识到这一点,我非常高兴。生命短暂,如果一个人手里总是抓住一件东西不放,特别是抓住了不再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他就失去了本可以抓住属于自己东西的好机会,就不能说是善待生命。”
“你说的很有对,刚才龚助理也给我讲了类似的道理。他对我说,人世间有很多美好的东西,但往往是你得到一些东西之时,也是丢掉另一些东西之日。你成了活力四射的青年,也就失去了天真烂漫的少年;你到了经历丰富的老年,也就要告别稳健成熟的中年;你要欣赏太阳的炽热,就看不到月亮的冷艳。人的一生,正是在得失之中度过的,你看看医院里的这些病人,都在拿着金钱换取生命,平时舍不得花小钱吃菜,现在都在花大钱吃药。”
“这个人能言善辩,有点油嘴滑舌,你不要听他瞎忽悠。”
“我不这样认为。”晓刚说,“你对他有偏见,而我觉得这个小伙子人不错,话讲的很有道理,我从他的话里听得出来,他对你仍然很在意。”
“哥哥,你现在要静下心来治病,少操心其他的事。我刚下夜班,现在回家吃饭、休息,下午再过来看你。”
“你好好休息,下午不要再过来了。”
“不行,我必须过来,不但来看你,还要问问医生你明天做手术的事是怎么安排的。”
晓媛离开晓刚的病房,就急忙往家赶。
晓媛吃过午饭在屋里睡觉,任春华去超市买水果准备给晓刚送去,崔莹怕影响女儿休息,一个人在厨房把门关得紧紧的,收拾刚刚买来的柴母鸡,准备炖一锅汤晚饭前给晓刚送去。
崔莹这几天也是悲喜交加,思绪万千,她对任春华说,如果晓刚患了治不好的绝症,自己经受不住打击,可能就要跟他一同去另一个世界。
任春华嘴里安慰她,心里却很害怕,晓刚是不足月剖腹产生出来的孩子,崔莹为了生产晓刚,差一点付出自己的生命,而且终生不能再生育。
崔莹生下晓刚以后,身体非常虚弱,晓刚也总是生病,她无法正常上班,大部分时间在部队与任春华一起生活。有一次,崔莹到驻军医院给晓刚看病,听一个医生讲,一个未婚女子因为怀孕时间超过七个月,无法再引产,准备到时候把孩子生下来送人,让那个医生悄悄帮她找一个想抱养孩子的人家。崔莹听到这消息,与任春华商量之后,向组织汇报了想抱养孩子的愿望。因为当时的政策是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但要间隔四年以上的时间,组织上考虑到任春华家的实际情况,同意了他们的请求,帮他们办理了有关手续,并答应为他们保密。
崔莹对老家的人和任春华的同事都说自己早已怀孕,两个月后,她装模作样地在医院招待所住了几天,把未婚女两个孪生女儿中的其中一个抱回了部队,起名叫任晓媛。吃奶粉长大的晓嫒,从小就身体瘦弱。
又过了一个多月,任春华夫妻俩一个抱着刚满周岁的晓刚,一个抱着满月不久的晓媛,一起从天津回到了老家。
任春华在老家的探亲假还没有休完,就接到了调他去北京工作的通知。
崔莹一直担心晓媛知道了自己的身世,去寻找她的亲生父母,特别是晓刚住院以后,心神不定,寝食难安。任春华安慰她,晓媛是个聪明的孩子,她可能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身世,也可能早已知道自己不是我们的亲生女儿,对于一个医生来讲,这是很容量做到的事情,她只是不愿意捅破这一层窗户纸而已。这件事顺其自然,她不捅破,我们也不点明。
晓媛休息了不太长的时间,就急忙从家里到医院,先找到准备给晓刚做手术的医生,了解了有关情况,然后走进病房大楼。
在病房大楼大厅,她看见龚长治正从电梯里出来。
“真是有缘分,一天几次碰见你。”龚长治笑着先给晓媛打招呼。
“你不在宿舍里老老实实地写调查报告,总是跑到病房大楼来干什么?”晓媛不热不冷地问他。
龚长治往一个人少的地方跨了两步,也示意晓媛走过去,然后说:“我刚才又到晓刚大哥的病房去了,你别误会,是他让我有空陪他聊聊天的。我给他找了几本幽默故事和经典笑话之类的书,又与他说了一会话。我在军校读书时同宿舍的一个同学也患过忧郁症,当时队里让我陪着他治疗。忧郁症不算什么大病,但是治疗起来比较麻烦,我带着那个同学除了找心理医生疏导,也使用了传统的森田疗法,还有我发明的‘龚氏疗法’。我主要是每天给他讲笑话、编故事,说一些令他高兴的事,激发他的生活热情。所以,治疗忧郁症我有不算是太丰富的实际经验,知道除了药物,亲友的关心、沟通、理解,是最好的‘百忧解’。我那个同学的忧郁症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就基本上好了,他最近刚被提升为某师后勤部财务科的副科长。”
“你学雷锋做好事有悠久的历史了。”晓媛与龚长治开玩笑说。
“也不算太悠久,还不到五十年时间!”
龚长治的话把晓媛逗笑了。
“我刚才本来想与任大哥多聊一会的,你们家老爷子关心儿子,到病房送水果来了。”龚长治接着说,“我看他与你哥哥讲话,就像是中央党校的教授给省市委书记上理论课,你哥哥似乎对他的话一点也不感兴趣,他要是我的老岳父,我就与他——”
晓媛涨红了脸,笑着说:“你是大白天做美梦!”
“打个比方,何必当真,好吧,我把美梦留到晚上去做,不耽误你的事了,再见!”
崔莹小心地提着鸡汤刚要进病房大楼,看到女儿和一个年轻军人站在离电梯不远的地方比划划地说着什么,便闪在大门一边偷偷地观看。她见两人说了一会话,晓媛上了电梯,年轻军人朝门外走过来,崔莹把他的外表看了个一清二楚。小伙子高高瘦瘦,白白净净,看着非常精干。他大概就是晓刚说的姓龚的财务助理员了,崔莹满怀深情地看着小伙子走远的背影,满意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