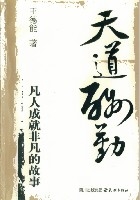什么是旅行?旅行有何益处?任何落日都只是落日;你不必非要去君士坦丁堡看落日。旅行能带来自由感?我可以从里斯本出发去本菲卡来获得自由感,而这种自由感甚至要多过人们从里斯本去中国。因为如果心中没有自由感,无论去何处都没有用。“任何一条道路,”卡莱尔说,“通向N市的任何一条道路,都可以把你引向世界的终点。”但是通向N市的道路,如果径直通向世界的终点,同样可以引导我们返回N市。这就意味着,作为我们起点的N市,也是我们打算去寻找的世界终点。
孔狄亚克在一本著作中,一开始就写道:“无论我们爬得多高或跌得多深,都逃不出自己的感觉。”我们无法脱离自己而去。我们无法成为其他人,除非我们积极地、生动地去想象自己是其他人。我们是真实景观的创造者和上帝。无论如何,它们在我们眼中的真实模样,就是我们所创造的模样。世界上四大洋的任何地方我既无兴趣去看,也不曾真正去看过。我游历在属于我的第五大洋。
有些人环游了四大洋,却走不出自己的单调。我的航程比任何人的都要远。我见过的高山要多于地球上已有的高山。我途经的城市要多于已经建起来的城市。放眼望去,我渡过的壮丽河水在不存在的世界里奔流不息。如果真去旅行,我只能找到一些蹩脚的复制品,是对我无须旅行就已看见的东西的复制。
其他旅行者像无名的外国人一样到访那些国家。而我在到访那些国家时,不仅能感受到那些无名旅行者才会有的秘密快乐,而且是统治那里的国王,是生活在那里的人民和他们的习俗,是那个国家及其周边国家的全部历史。我所见到的每一处景观和每一幢房屋,都是上帝用我想象的材料创造出来的,它们就是我。
我已久未动笔
我已久未动笔。几个月过去了,我仿佛并不存在,在办公室和精神世界之间经历着思想和感觉的内部停滞。不幸的是,由于这种思想在沤积中发酵,甚至这样的状态也并不安宁。
我已久未动笔,甚至连我都不存在。我甚至似乎很难做梦。街道对我来说仅仅是街道。我只是带着意识去处理事务,但我不能说我没有走神:在我的意识深处,我在睡觉而不是沉思(而我通常都是在沉思),但我在工作时仍然保持着一个不同的存在体。
我已久不存在,我彻底地平静下来。没人能将我和真正的我区分开来。我只是感受到自己在呼吸,就好像我做了什么新鲜事情,或者迟些做什么事情。我开始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是清醒的。或许明天我恢复自我意识,我的生活历程也重新开始。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否会使我变得更快乐,还是不快乐。我一无所知。站在城堡的小山上,我抬起自己缺乏想象力的脑袋,看见映照在无数窗玻璃上的夕阳在熊熊燃烧,冰冷的火焰发出崇高的光芒。我至少能够感受到悲伤,能够意识到我的悲伤一闪而过——我用耳朵去倾听——突然驶过的电车声,年轻人漫不经心的说话声,以及活着的城市被遗忘的喃喃抱怨。
我已很久不再成为我自己。
倦怠
有时候,我的情感被一种几乎是突如其来的生活的极度倦怠压倒,我甚至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减轻它。自杀似乎是一种不大可靠的补救,而自然死亡——即便可以假定这种办法使人失去意识——也是远远不够的。这种倦怠让我渴望的东西,远非结束自己的生命(而这或许可能,或许不可能)所能实现,我所渴望的东西更可怕,更深刻:我从来不曾存在过,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有时候,从印度人普遍混乱的思索中,我似乎看出这种渴望的有些东西比不存在还更消极。但是,他们要么是缺乏交流他们所想的敏锐感,要么是缺乏感他们所感的敏捷度。事实上,我无法真正将我从他们那里看到的东西看清楚。更进一步说,我是第一个将这种不可救药的感觉及其难以揣测的荒谬诉诸文字的人。
我写下这种倦怠,用以治愈它们。是的,有讽刺意味的是,每一种真正深刻的忧伤(它并非来自纯粹的感觉,还混入一些智识成分),都可通过我们的写作来获得解救。若说文学没有什么用处,至少这就是它的用处,尽管只有少数人才会用到。
不幸的是,感觉比智识带给我们更多的伤痛,而同样不幸的是,肉体比感觉带给我们更多的伤痛。我称其为“不幸”,是因为人类的尊严使他们需要对立物。没有什么精神痛苦(比如爱情、嫉妒或怀旧)比未知之物更令我们痛苦,它们像剧烈地生理恐惧将我们压倒,或者说让我们变得怒气冲冲或野心勃勃。但是,没有哪种痛苦像真正的疼痛一样使人撕心裂肺的痛,比如牙痛、胃痛或分娩的阵痛(我想象如此)。
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赋予同样的智识以某种情感或知觉,将它们抬高到高过其他事物,当智识将其分析延伸至在它们之间作比较,我们又贬低它们。
我像睡觉一样写作,我的整个生活就像一张等待签字的收据。公鸡在鸡棚里等着被宰杀,而它居然啼唱着自由赞歌,只因主人提供给了它两条栖木。
雨景
每一滴雨,是我失落的人生在自然界哭泣。天空飘落绵绵细雨,转而倾盆大雨,复又绵绵细雨,转而倾盆大雨,雨中寄托着我的忧思,将整日的哀愁徒然向大地倾泻。
雨下了又下。雨声浸透我的心灵。雨如此地多……我的肌肉渗出水来,流遍我的全身。一股痛楚的寒意用冰冷的手握住我可怜的心。灰色时光变得更漫长,在时间里被拉开来;时光缓缓地流淌。雨如此地多!水沟里涌出小股急流。恼人的雨声流遍我的意识,形成排水管。
雨呻吟着,无精打采地敲打着窗玻璃。一只冰冷的手扼住我的咽喉,使我无法呼吸。在我的内心,一切都将死去,甚至包括我做梦的智慧!我无法获得身体上的舒适。我倚靠的每一个柔软的东西都用尖锐的边缘刺伤我的心灵。我看到的每一双眼睛在耗尽的白日里黑得可怕,为了死得没有痛苦而闪出慈悲的光芒。
令人鄙夷的梦
梦最令人鄙夷的地方就在于人人都拥有它。那个在送货过程中倚着街灯柱打瞌睡的送货员,在他的朦胧意识里大概在思索着什么。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所想的正是我在单调夏日的寂静办公室里来回抄写的两本分类记账本。
不存在的风景
我同情这样一些人,他们对可能之物、合理之物、易得到之物怀有梦想,而不同情那些幻想非凡、遥远的事物的人。那些有着宏伟梦想的人既是一群对自己的梦想深信不疑的疯子,又是一群快乐的人。或者说,他们只是一群空想家,他们的幻想像心灵的音乐将他们抚慰,什么意义也没有。然而,那些可能实现心愿的人,却极有可能遭遇真正的幻灭。我对不能成为罗马皇帝毫不感到失望,但我对于哪怕一次也不能和每天早上九点出现在右拐的那个街角的针线女工搭上话而感到极大的遗憾。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从一开始就阻止我们去接近这个梦想,然而,可能实现的梦想扰乱了我们的正常生活,使我们依赖于它的实现。一种梦想独立存在,而另一种梦想依照可能或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定。
这便是为什么我喜欢不存在的风景和从未见过的、辽阔而空旷的无垠大地。过去的历史时代完全是一种奇迹,因为我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不能成为他们的一份子。当我梦见不存在之物时,我睡着了;当我梦见可能存在之物时,我醒来了。
正午时分,在空寂的办公室里,我斜倚着阳台的一扇窗户,眺望着楼下的街道。我的眼睛注意到那些行人的来来往往,我散乱的思绪知道来来往往的行人映在我的眼中,但却在冥想中太过沉迷,以至于看不到他们。我的手肘费力地扶着(靠着)栏杆,我趴在手肘上昏昏欲睡,强烈地感觉到自己一无所知。带着精神的超然,我看着过客匆匆的压抑街道,写下了这些细节:二轮运货马车上堆着板条箱,仓库门前放着麻布袋,街角杂货店最远的那扇橱窗边,葡萄酒瓶闪耀的光芒,我猜想,没有人能买得起。街上匆匆走过的行人总是和片刻之前走过的行人毫无差别,那里一群浮动的人流,支离破碎的动作,变幻无常的声音,逝去的事物,仿佛从未发生过。
写下来,不是用感觉,而是用感觉里的意识……其他事物的可能性……突然,在我身后,传来一种形而上学的声音,那个勤杂工突然来了。我有种想杀死他的感觉,因为他闯入我没有思想的世界。我回过头看着他,沉默中充满憎恨,潜藏着杀气腾腾,我的心里已经听到了他要告诉我这个或那个的声音。他在房间那头冲我笑着,用很大的声音说着“下午好”。我像恨这个宇宙一样恨他……我的双眼因想象而感到酸痛。
对弥撒的回忆
雨下了数日,广袤无垠的天空重现蔚蓝。街上的水坑像乡村的池塘一样沉睡,空气中漂浮着晴朗而凉爽的喜悦,与污浊的街道形成一种对比,使冬天的沉闷空气有了春的气息。今天是礼拜天,我无事可做。今天的天气如此美好,使我甚至不想做梦。我倾尽所有的真实感觉去享受它,以致我的智力也屈从于它。我像一个自由的店员漫步街头。我想象自己已经老去,以便能够找到重返青春的喜悦。
在礼拜天,宽阔的广场呈现一派庄严气氛,俨然另一个世界。人们从圣多明我教堂的弥撒仪式中走出来,而另一场弥撒即将开始。我看着那些正在离开的人,还有那些尚未走进去的人,因为他们在等还未来到的人,观察走出来的人。
这一切都不重要。他们和尘世万物一样,只是一种蛰伏的神秘和静止状态的城墙,我像一个刚刚抵达的信使,凝视着冥想的开阔天地。
当我还是个孩子,我常常来做这个弥撒,或许那是另一个弥撒),但我想应该就是这个。出于尊重,我穿上仅有的一件最好的衣服,高兴地度过每一分钟,哪怕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我高兴的事情。我外在地活着,衣服干净而崭新。一个即将死去却一无所知的人,若是被母亲牵着手,那么他还有什么别的渴望呢?
我曾经享受这一切,但如今我才发现,我有多么享受它。我像走进一个伟大的奥秘一样走进做弥撒的人群,最终像进入一片空地一样从里面走出来。我曾经如此,如今还是如此。这是那个不再有信仰、如今已长大成人的我,我的灵魂在怀念,在哭泣——只不过这个自我是虚构的,迷茫的,痛苦的并已经死去了。
是的,倘若我想不起自己曾经是什么样的,这是多么令人难以容忍。这些陌生人群将要离开弥撒,而另一些人将来到。这些将要离开弥撒的陌生人和另一些要来做下一场的人,就像我在岸边的小屋敞开着的窗下,在缓缓流淌的河水中飘过的小船。
回忆,星期天,弥撒,曾经存在的快乐和时间停留的奇迹,而只因它们是我的回忆,将永远不会被我忘怀……正常感觉的荒谬对角线,广场四周破旧马车突然驶过的声音,嘎吱作响的车轮声在马车喧闹的寂静中响起,在这母亲般矛盾的时光里,延续到此刻,在此处,在我和我的所失之间,在我身后凝视着的那个我……
百万富翁与小职员
人爬得越高,需要放弃的也就越多。世界的巅峰除了他自己,容不下其他东西。他越完美,放弃的就越彻底;而放弃的越彻底,拥有的就越少。
我读完一篇报纸上的文章后,产生了这些想法。那篇文章讲述了一个名人——一位拥有一切的美国百万富豪——伟大而多面的人生。他得到了一切渴望得到的东西——金钱、爱情、友情、赞誉、旅行和收藏品。金钱并非能买到一切,但个人魅力使一个人能获得很多金钱,当然,还有大多数事物。
当我把报纸铺在饭店的餐桌上时,我已经在构思一篇类似的文章。文章的焦点缩小到一个公司销售代表。他或多或少算是我的熟人,此刻正像往常一样,他在后面那个角落的餐桌上吃午饭。诚然,在较小的程度上,那个百万富豪所拥有的,那个销售代表也拥有,的确,虽然更少,对他的才干来说已是足够。双方都同样成功,他们的名望没有一丝差别,此时我必定要在特定的环境下去看待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知道那个美国百万富翁的名字,然而,在里斯本的商业区,没有人不知道那个在角落里吃午饭的人的名字。
这些人在他们手臂能够得到的范围内尽可能多的去获取一切东西。他们的不同之处就在于手臂的长短,而在其他方面完全相同。我从未能够嫉妒这类人。我总是感到,美德在于这些方面:获取人的手臂范围以外的东西、活在人所处之地以外的地方、死后比生前更声名远扬、实现不可能之事、一些荒诞不经的事情、战胜世界的一切现实,就像战胜一个困难。
如果有人指出,经久不衰的快乐在人的生命停止之时将归于零,那么我首先会说我不确定是否如此,因为我对人类生存的真理无从知晓。其次,未来的名声带来的愉悦是一种现世的愉悦——而这种名声发生在未来。这是一种物质财富无法带来的、感到自豪的喜悦。这或许是一种幻觉,但不管怎么样,要比只欣悦于眼前的快乐要强得多。那个美国富豪不能去相信,他的后人将欣赏他的诗作,因为他什么也没写下来。那个销售代表无法去想象,未来的人将赞赏他的画作,因为他什么也没画下来。
然而,在这短暂的一生,我什么也不是,却能欣悦于未来的人能读起这些特别的纸页,因为我实实在在地写了下来。我能够引以为豪——就像父亲为儿子感到骄傲——我将拥有名声,至少我拥有的某些东西能够给我带来名声。当想到这里,我的地位,我从桌旁一跃而起,我那无形的、内心的宏伟高度超然越过了底特律、密歇根以及里斯本的所有商业区。
然而,我并非在有了这些反思后才开始反思。我最初思考的是关于人不得不过着渺小的生活,以便能够超越这种生活。一种反思和另一种反思不无二致,因为它们一模一样。荣誉不是一块勋章,而是一枚硬币:一面是头像,另一面是面值。更大的面值要使用纸币而非硬币,而前者的价值从来都不会太大。
像我一样卑微的人,用这些形而上学的心理学聊以自慰。
梦想
有的人在生活中心怀伟大梦想,却不能去实现。而有的人没有梦想,也同样不能去实现。
目标与现实
每一种奋斗,无论其目标是什么,在现实生活中总是要做出调整;它变成另一种奋斗,服务于另一种目标,有时候目标的实现与原定目标完全相反。唯有卑微目标,因其能被完全实现,故而值得去追求。如果我追求财富,我可以通过某种办法去得到;这个目标是卑微的,无论是个人或非个人去追求,就像所有可量化的目标,它是可以得到且可以检验的。但是,我如何才能实现为国效力,或丰富人类文化,或改善人性呢?我不确定什么才是正确的行动路线,亦不确定如何才能证明这些目标已被实现……
灵魂与上帝的区别
对于异教徒而言,完人即存在之完人;对基督教徒而言,完人即非存在之完人;而对佛教徒而言,完人即虚空。
灵魂与上帝之间的区别便是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