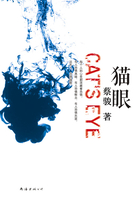“汪先生不愧智谋之士,好!”佟宝目光咄咄逼人,抚掌叹道,“权重主疑!中堂一退,就可在皇上面前明了心迹还可堵住那些说中堂揽权自重人的嘴。明珠立时便成了火炉上的人,侧目而视的众矢之的——一石三鸟,妙极!”索额图起身踱了几步,倏然回身道:“是一石五鸟!我能疼出工夫来好好侍候太子,也能仔细瞧瞧谁真的待我好!——哼!我就且让他明珠一马由着他在主子跟前折腾!”
本来显得沉闷的空气立时活跃起来,众人方有心绪去留意那桌上并不丰盛的菜馔。五个人吃着酒,叫了家里戏班子演奏助兴,直到三更半方歌歇酒住。回房安歇时,佟宝直送索额图到三门口,小声问道:“三爷,家兄信里说的事怎么办?”
索额图站在春寒料峭的风中一时没言语,半响才微叹一声道:“这个假玩意儿杀了没意思,留着有点用处,又怕玩火焚身,叫葛礼小心一点,不要直接见面来往,听着我的吩咐!”说着,见蔡代掌着灯带着几个小厮迎出来,索额图因笑道:“老佛爷下月圣诞,前些日子叫你打听明相送什么礼,你可问出来了?好歹咱们是正经国戚,别落了人后才是。”
“回爷的话,”蔡代笑道,“咱们府茶房头儿黄家的女人是明相府管库头儿张管事的姐,已是问出来了,明相送的一金一玉两把如意,一幅大理石寿比南山图——奴才寻思着老佛爷最是虔信我佛,江宁盐道献的那尊浑金观音有七百多两重,尽自抵得过了,只不过如今又多了个高相,不晓得他送什么东西……”
“罢了。”索额图说道,“高士奇那头大可不必担心,他才进上书房,官品不过郎中,再能搂钱,一时半刻就能比得上我们了?”说罢便回房安歇。
休息一日,第三天是会阅博学鸿儒科试卷的日子,索额图起了个大早,至西华门落轿递牌子进大内。因见李光地从里边出来,索额图便站了问道:“这么早就进来了?急急忙忙地到哪去呢?”李光地熟不拘礼,只拱手一揖,说道:“昨晚主上命我起草一份给施琅的诏谕,因不懂军事,在文华殿查阅史籍,直忙到天透亮儿才算交差。皇上因还要留下看看,命我回去歇息,下午再来面圣听谕。”索额图听了一怔,说道:“这会儿皇上已经临朝了?大臣们都来了没有?”
“中堂不必去乾清门,”李光地笑道,“皇上今儿在养心殿阅卷。昨个儿中堂没来,主子和高士奇、明相、熊相一起去看了畅春园,说要从虎臣兄海关上拨几百万重修起来,给老佛爷作颐养之地呢!”索额图听了心中不禁懊悔,不该贪一日悠闲,口中却道:“我这些时太累,主子特许我休假一日呢——你去了没有?”“去了的。”李光地一笑,“还有查慎行他们一干翰林,陪着主子做诗解闷儿。”二人说着,见高士奇带着两个小厮抬着一件东西过来,索额图便笑道:“我还以为我只一个人来迟了呢!你这带的什么东西,还用黄绫子盖着?”
高士奇笑道:“献给老佛爷的寿礼——中堂甭看,不过是花儿草儿的。我是个穷酸书生,可比不了您和明相。”说罢,双手捧起那盆盖着的花儿,跟着索额图来到了养心殿,李光地径自打轿回府去了。
养心殿中鸦雀无声,高士奇悄悄把花放在丹墀下,小声对索尔图笑道:“这回中堂和明相可是骗了我们,竟自歇了一日!昨个儿从畅春园回来,主子就叫我和熊相看卷子,直到半夜才回去呢!”索额图听说明珠也没有参与阅卷,心中略觉放心,只一笑,高士奇已是挑起帘子,二人一前一后进来。
康熙拿着一个名单,皱着眉头正在沉思,案头堆着三叠卷子齐整放在一边,下头熊赐履和明珠二人都端坐在木杌子上静等康熙垂问。康熙听见帘响,一转脸见是索额图和高士奇进来,便笑道:“索额图来得正好,严绳武的卷子是你收存的,是不是失落了一页?”
“回万岁的话,”索额图忙答道,“严某只写了一首诗,《璇玑玉衡赋》竟没有作,所以少了一篇儿——这事何等重大,奴才焉敢草率?”康熙看着熊赐履笑道:“怪不得你这份单子上一二三等都没有严绳武。”明珠说道:“严绳武乃是大儒,故意脱漏试题不做,实属不敬。奴才以为熊赐履将他取在等外,实在允当。”
康熙啜了一口茶,跷腿坐在炕沿上,抽出一份卷子说道:“彭孙遹这卷子是东园看的吧?这文中‘验于天者不必验于人’,恐怕说理未必周全吧?”熊赐履见康熙从他的阅卷中挑出了毛病,忙道:“主子说得虽是,但从事物本理而论,天、人原是一个理,验于天或验于人均无不可。所以彭某说的虽然偏颇,其实于大理并不悖谬。”康熙见熊赐履为自己辩护,知道他没听懂自己的意思,便又抽出一份笑道:“这也罢了。汪琬这一卷,前头写了‘有或问于予曰’,后头又有‘唯唯、否否’的话头。他指的是什么人?是朕,还是他自己?抑或朕有什么不当之处,不好直说,变了这法子来影射么?”
熊赐履想不到又碰了一枚更硬的钉子,不敢坐着回话了,忙起身一躬说道:“汪琬这人皇上深知,对圣德佩服得五体投地,焉有影射之意?赋体本来就有子虚乌有这些话,并非实有所指,伏惟主上圣鉴。”
“你不要慌张。就是影射也没干系。将来朕再问他本人,如果有话,直说就是了!”康熙格格一笑,把卷子撂过一边,“朕的愿意是夸你和高士奇。不合体例的太多了,都不取中,这回的博学鸿儒科是怎么回事?你看,朱彝尊的诗‘杏花红似火,菖叶小于钗’,谁见过杏花如火?再说菖叶又怎么会和钗扯到一起?”他一卷一卷地翻着,“……这类毛病太多了!潘束这一卷,东韵叶上出了‘宫’字;李来泰把‘逢’、‘浓’都拿来搪塞;施润章最讲究诗韵的,竟也将‘旗’字误入支韵……”
明珠对诗韵一道知之有限,屡次碰壁,知道逞能不如藏拙,因见康熙瞧自己,便笑道:“皇上看得真细!如今许多文士都不大讲究这些。近体诗本来难做,平日从容吟哦尚且拈断三根须,仓猝御试能做到这样,已奴才看,也就难为这些老先生了。”
“你哪里知道他们!”康熙冷笑道,“他们都是识穷天下的当代硕儒!岂有写不出赋、押错了诗韵的道理?”他站起身来,慢慢地踱着步子,又道:“本来他们就不想来考,所以就在考卷上用错字、押错韵。朕若按卷子黜落呢,可可儿的就把最出名的人都落了榜,天下人谁会相信是他卷子不好?只说朕不能识人!如若糊涂取中呢,鸿儒们又要暗笑朕没有实学,看不出卷上毛病儿——论其用心,他们待朕甚是刻薄的……”他沉吟着,喃喃说道,“看来不能只凭一场考试就让他们就范呀!”
明珠听了,不由愤愤地说道:“这叫不识抬举!请将这些人卷子以邸报印行各省,凡错格、违例、误韵的一概黜落不用!”索额图也道:“明珠说的有理!”熊赐履却暗自叹息,果真如此,这场博学鸿儒科取中的便差不多全是二流人物了。康熙因见高士奇不吱声,因问:“高士奇,以你之见呢?”
“奴才以为应一概取中,这是未考之前议定的。”高士奇目光幽幽地闪动着,“皇上原知道他们不肯应试,圣拉硬扯来的,有什么好心绪做诗写文章?但也有偶尔笔误的。这样一弄,大名士尽黜落孙山,与不办博学鸿儒科何异?前头千辛万苦预备多少年,岂不白费了?他们回去当然不敢骂街,但皇上却落了个不识士的名儿,也确实糟蹋了人材……所以断断不可用平常科举格局求全责备,竟是全部取足名额,便是等外的也一概授官。不愿做官的,也给个名义,算是致休……”康熙微笑着静听高士奇的宏论,说道:“你这一办法倒好,只难免他们耻笑朕不善衡文,也顾不得这许多了!”高士奇扑哧一笑道:“哪里!皇上可将每一卷荒谬之处都加了批语,发还本人拆看。这一百多人,哪个敢不心悦诚服?”
“好!”康熙精神大振,“砰”地一击案道,“王前曰趋士,士前曰趋势。朕来做个趋势之主!”
“趋势则国衰,趋士则世兴!”高士奇应口说道,“吾主此心,天下臣民之福!”
康熙呵呵大笑:“就这么定了!高士奇,你再细阅一遍,凡有乖谬之处一概用指甲划出,写得好的加朱笔双圈!——传旨:高士奇着补博学鸿儒科一等额外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