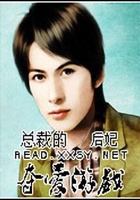回来时,见明因已抓好了药,郭大娘正摸索着袖口里为数不多的铜板。
“大娘,我今早出门时没带够钱,给你家赊了几块豆腐,今日这药钱,便相抵了吧!”明因说着,将药递给郭大娘。
郭大娘一听,掏钱的动作缓了下来,道:“自家做的几块豆腐,值不了几个钱,怎可相抵?”说着便摸出了五六个铜板放在手心点了点,皱巴巴的老脸红得厉害,自己嘀咕道:“只这几个铜板了,不知够不够……。”
明因见状,索性走出药柜子,将手里的要塞到郭大娘手里,道:“大娘,这药也是自家做的,那为何就不能相抵了?”
“可是……。”
“大娘!你家豆腐做得好,我和爹爹都喜欢的很,不如以后就这么抵过好了!”
“这怎么成啊!陆姑娘,我这样不就是占了你们便宜了!”郭大娘很是感激,只觉得不妥。
“大娘,这是两厢情愿之事,各取所需而已,怎会是占便宜?”
见郭大娘踌躇的很,陆原递给明因一张新的药方,开口道:“大娘,就别推辞了……。”还未说完,便听见门口有人在大喊着“陆大夫”,陆原止了话,疾步走上前去。
见明因也还忙着抓药,郭大娘又不好打扰,站在那里一时也不知如何。一边站着的的谢如儿多少听懂了些,走上前对郭大娘道:“大娘,就收下吧!舅舅和姐姐的一片好意,岂忍心辜负?”
郭大娘低头思索一阵,抬头看了看谢如儿,摇了摇头,回身对还在药柜中忙碌的明因道:“陆姑娘,那就谢谢你们了,你们可真是好人呐!”
明因停下手里的动作,笑道:“可别,大娘,我还想着什么时候向您讨教一下毛豆腐的做法呢!你家的毛豆腐,简直是人间极品啊!”
大娘呵呵的笑道没问题。临走还听明因交代每隔半月要来拿一次药。
看那古板固执的先生唾沫横飞了一下午的谢禾揉着脖子捏着肩膀,走过谢如儿的房间时,见她房门大敞着,便走了进去。看她桌子上摆着一盘旋着的小卷,黄澄澄的,看着象麻花,却又似乎不是。拿起一块,似是被压得扁扁的,有些酥脆,手指稍用劲便有些不受力碎散下来。轻咬一口,感受到里面绵软的夹馅儿,香甜不腻,味道刚刚好。谢禾满意地点了点头,心想着,这个表姐……哦!是表妹,这手艺,还真是天上有人间无!
谢如儿听到小梨来说谢禾来了,从里间走了出来。
谢禾一见,道:“又去剥削舅舅了?”
“不是舅舅,是姐姐……。”想着就又笑了起来,谢禾耸耸肩,很是无奈,自从知道明因比自己大之后,每次说起谢如儿都拿来取笑自己,见多了倒也习以为常不介意了。
笑了一阵,谢如儿想起早上的事,便拉着谢禾讲了一通。她倒也是后来缠着明因说,才知道那个郭大娘家中只剩下老夫妻俩,就靠着平巷的那间小豆腐坊过活,老两口就一个儿子,却在两年前清明节出城祭祖时被土匪掳走了,至今生死不知下落不明的,怪不得她去买豆腐的时候看那豆腐坊又破又旧的,只剩下个干巴巴的老头儿在那里。明因见她可怜,又知道这大娘平日里总是不好意思要人家东西,便想出了以物易物的办法。
谢如儿叹息道:“这郭家夫妇也是可怜,年暮之时竟遭遇如此窘境。”心中打算着,该帮着姐姐接济一下这对老夫妻啊!
谢禾点头,心中暗道:“这明因,温婉平和的性子,到底是心善的!”不禁默默赞许。
这日,阳光明媚,暖风湿润扑面,好容易褪下裹了一冬的棉袄子。城中的人们也似乎受了这春季暖风的鼓励,显得精神抖擞的,闹市间终年开着的店铺也似乎有了些新气象,与秃枝上冒出的嫩黄一样充满了生气。
这样的气象,怎能少得了每日都欢快如枝上鸟雀的谢如儿,自是早早的就将明因拉了出来,明因也是欢喜的很,据说今日正是樊城每月一次的会集。只是欢喜归欢喜,还是将晒了一半的金银花仔细晾晒在纱筐上才出的门。只是谢如儿催的急,便只好匆匆的出了门,连发髻都未曾仔细挽上,只随着家中挽的松髻便走了。
一连三日的会集,正是各店家将自家的好物什拿出来展示的好时机,遇上好机会,还可以好好地挣上一笔。不止城中商家,临近城村的商人也会来此摆摊,因此总能在会集上看到些平日里见不到的稀奇物件,就像谢如儿极是稀罕一个外村来的邓姓青年来卖的扇坠,都是出自他的巧手,有木制的,有石刻的,最妙的还是用核桃和各种树籽桃核儿雕刻而成的小玩意儿,雕的物什惟妙惟肖,甚得谢如儿的喜爱,每次来都要看看这个杂货郎这一月间又做了些什么精细的玩意儿来。
明因来了半月多,自然是未见过会集的盛况,一入了坊间,便东凑凑西看看,好奇得很。到了一个布帛摊子前,明因停了下来。想起前日看爹的外衫旧了些,该是时候添置一两件了。自己的衣裳倒是多了许多,一进樊城姑母就为她置办了好几套。
这家店家倒是细心,摆放得整齐的布帛上,每一匹都有裁出手绢般大小的一块,以便买家看清颜色布质。素白的手抚上一块质地轻柔的茶褐色布料,布色染得很是均匀,与爹爹平日里喜欢穿的倒也很是相符,还是满意的,便扭着头往四周寻找店家。
樊城的坊,是由官府主持开放的,只有在每月会集时开放。既说是官府开的,又是每月最大会集的聚集地,当然是设在城中最为繁华的阶段。但这坊,却并不是由四面墙围起来的,只因虽说会集时况盛大,但毕竟每月只得三日,城中最为繁华的阶段,也不可能除这三日外则尽是空巷吧!平日里那里则是些小摊小贩走街串巷时歇息摆摊的地方,三不五时的,还有些杂耍班子或是些不成班队的戏子伶人到此献技献艺,收些路费伙食费的。一旁的石桥凉亭便也就成了人们观赏歇息的好去处。今日会集,则是与平日有些不同,没了戏耍班子和七零八落的小摊小贩,各户商家都摆起了半人高的摊子,日头底下临时搭了个草棚遮遮那暖久了也有些晒的阳光。
这日阳光晴好,屋子上的青砖黛瓦,似乎也给这暖日感染了,河边桥上石缝中,点点青苔也给阳光照得甚是可爱,清风徐徐,河岸边的杨柳弯着腰垂下的新枝被吹得时而沾了河中的波光粼粼,时而甩出水滴,碎金般的落入水中又荡漾开来层层的涟漪。
可从石桥的另一端走来的男子却似乎神色匆忙得很,挺鼻凤眼上一对微蹙着的眉,脚步匆匆的,带起玄青的长袍灌了风,又扑闪着翻了开来,显得与这和熙暖阳下的轻快很是不符。
染坊里一批新布正在上色,若不仔细着点,色上得不均匀,这布的档次便得滑下好几个等级,正是忙的时候,爹得看着铺头离不开身,就想着让赵元这小子来帮忙看着点会集的摊子,他倒好,跑了个没影!刚刚家奴来报,赵与无法,只得让管事先看着点染坊,自己便急忙赶往市间坊。
赵与远远地,便见一女子正在自家的摊位前细心挑选布帛,徐徐春风扯得一袭鹅黄色精致的绣着白梅的短儒衫,连带着月牙色的垂苏软裙微微扬起,万缕青丝随意绾之,不施粉黛,却显得娇憨动人。赵与不由放慢急促的脚步,缓步而来。
正是如何都找不到店家询问的时候,谢如儿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搂了明因的腰不放,惹得明因一惊。
“你不是寻你那邓郎去了么?怎的还有心思来寻我开心?”明因一见是她,便缓下心来,笑着调侃起她来了。
谢如儿倒是理直气壮道:“这不是想着邓郎的物什精致,想带姐姐去观赏观赏么,亏我半路还折了回来,竟落得你如此,算了,我还是一心寻我邓郎去了!”谢如儿佯怒,双手抱胸,仰头嘟嘴的。
明因一见,只觉煞是可爱,点了点她高高扬起的鼻尖,笑道:“你哦!竟真是如此不拘,你这话都说的顺当,看以后还有谁敢娶你为妻!”
刚刚来会集的路上,明因便听谢如儿不停地夸奖那姓邓的郎君扇坠子做的精巧可爱,煞是惹人喜爱,明因嬉笑着道:“哦……原是邓郎啊!”偏谢如儿对于女子谨言慎行这套全是不予理会,这会子又是和明因在一起说道,她便更是百无禁忌了,便扯起自己并不算宽的袖子,佯作娇羞地回了句:“是啊!每月奴家正是只偏等邓郎呢!”
这会子明因拿来取笑她,她也欣然接受,全无闺中女子的扭捏,只和着明因呵呵地笑。
末了,拿起明因手里拿着的小块方布道:“这是要给舅舅做的衣裳?”
明因“嗯”了一声,四处又望了望,道:“只是不见店家,也不知该如何买下啊!”
正犹疑着,男子低而不沉,微带沙哑的嗓音从两人身后传来:“姑娘可是要买此布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