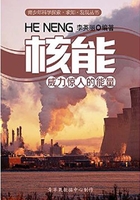丁小柔四下看看,干脆地回答:“步行街303号,swingcafé。”
走进swingcafé,丁小柔发现自己真是来对了地方。这里视野开阔,桌上摆着稀奇古怪的玩偶,墙上贴满了幼稚的留言,看来风格受众应该在25岁以下。最重要的是,店里的座位都是那种藤藤蔓蔓、摇摇晃晃的吊篮椅,设想了一下古板的杨礼文坐在支楞着花草的吊篮里打转的情景,丁小柔忍不住在心里放声大笑。
一小时后,已经消灭掉一块提拉米苏,正坐在窗前喝香芋奶茶的丁小柔看到了匆匆赶来的杨礼文。
他仍是一身正装,身上只有单调的黑灰白,推门看到满眼张扬的色彩,不禁愣了一下,却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进来。
看到丁小柔,杨礼文脸上露出一个由衷的微笑,丁小柔忽然有些后悔,怎么办,他好像真的是个好人耶……
诚如丁小柔所愿,杨礼文试了两次,才终于搞定不停摇晃旋转的吊篮椅,他强自镇定地坐直身体,样子有些滑稽。
丁小柔已是满心懊悔,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杨礼文却似乎不以为意,他的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黎珂,你现在好吗?这几年你究竟到哪儿去了?”
丁小柔微微一愣,随即明白过来,既然是从Q城医学院拿到的联络方式,应该已经知道她就是黎珂了吧,这可怎么办……她心里实在没底,只好嗫嚅着回答:“我,我真的不是黎珂……”
杨礼文似乎有些失望,稍微思考了一下,他和蔼地说道:“上次见面,你说你是黎珂的孪生妹妹,那你为什么要用黎珂的身份入职?而且据我所知,黎珂好像并没有兄弟姐妹,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能跟我说说吗?”
丁小柔调动起全部脑细胞,嘴硬地答道:“我确实是黎珂的妹妹,我叫黎琛。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我从小就被送给其他人家寄养,我们姐妹也是成年后才得知了彼此的存在。”
停顿了一下,她咬了咬嘴唇:“我跟姐姐一直偷偷书信来往,直到三年前,姐姐忽然没了音讯,我觉得情况不对,就开始到处探访寻找……”
偷眼看看杨礼文,他似乎已经信以为真,眼中竟然泛起了泪光:“是啊,三年了,我也一直在找她……”
丁小柔啜了一口奶茶,小心翼翼地问道:“那么……你跟我姐姐又是什么关系?”
杨礼文苦涩地笑了:“应该说……是师兄妹吧……”
他的语气有些落寞,丁小柔不假思索,脱口说道:“你喜欢我姐姐,是吗?”
杨礼文诚实地点点头,随后叹了口气:“可是,我却是第一个背叛她的人……”
九年前,二十八岁的杨礼文考入S城医学院,攻读肿瘤学专业的研究生。作为一名出身农家、大学毕业后曾在条件艰苦的乡镇医院工作了五年的学子,从入学第一天开始,他就决定了自己今后的去向——S城第一中心医院肿瘤研究所。
杨礼文的父亲死于肝癌。这样一种早期症状极为隐匿的疾病,这样一位操劳一生、无瑕顾及自己苦痛的老农,直到腹胀如鼓、瘦骨嶙峋,他才挣扎着来到医院,仅仅三天之后,便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彼时,杨礼文正读大二,为了多赚钱,少花钱,他已经连续两年没有回过家,寒暑假都留在学校打工。
假期里学生宿舍会全部闭锁,经过学校特批,杨礼文获准临时住在门卫房后的储物间里。得到父亲死讯那天是大年三十,他蜷缩着躺在窄小的床铺上,在欢天喜地的节日气氛里,在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哭累了昏睡,醒过来再哭,只觉天昏地暗。
在乡镇医院工作的日子,他是院里有名的“冷面一刀”,他不收患者家属的“小意思”,也不理会偶尔上门的医药代表,甚至对科主任的明示暗示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他只是拼命地工作,最长的一次连台手术,杨礼文站了整整十九个小时。
当同事们的称许变成排挤,当领导的赞扬变成打压,身心疲惫的杨礼文选择了辞职,专心准备考研。
重回校园,杨礼文无比珍惜,加倍苦读,除了上课和做实验,与大家鲜有往来,加上比大部分的同届学生都年长几岁,很快便成了曲高和寡的独行侠。
开学不久,临床学院开始实行残酷的激励制度,不论学制,不分专业,每次考试加权大排名,前一百位都有机会获得奖学金,但数目可观的特等奖学金仅有一个名额,从第二名到第十名都只是一等。
杨礼文的刻苦几乎达到了头悬梁锥刺股的程度,他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连各类冗长的表彰总结大会都请假不去,然而,不管他怎样努力,永远都只能拿到一等奖学金。
几次下来,几乎不问世事的杨礼文终于向自己的好奇心缴械,颠颠地跑到行政楼去看最新一期的奖学金榜单。
这次他是第三,第一名是“黎珂”,第二名是“靳晨星”。
久久凝望着这两个陌生的名字,杨礼文头痛地想,这个什么黎珂是男是女啊,生物化学居然考了满分……
他的疑问很快就有了答案。学期末尾,学院组织大家分批前往位于S城城郊的敬老院献爱心。与浩浩荡荡的内外科相比,学肿瘤的学生相对较少,便和同样小众的七年制本硕生编在一组,最后一批来到了敬老院。
老人们似乎已对类似的活动习以为常,他们三三两两地坐在院子里晒太阳,在大厅里看电视、打台球,或者凑成一桌下棋、打麻将,对这些朝气蓬勃的男女学生熟视无睹,表情漠然。
同学们擦的擦,扫的扫,很快干完了份内的活计,开始嘻嘻哈哈地闲聊打闹。杨礼文独自靠在墙上休息,忽然看到走廊尽头有一排安装着铁栏的屋子,他心中一紧,忍不住起身走了过去。
果然,这里住的都是些失智老人,他们有的身披床单“咿咿呀呀”地唱戏,有的没完没了地往嘴里塞东西,更多的只是或坐或卧,呆呆地、久久地向窗外张望……